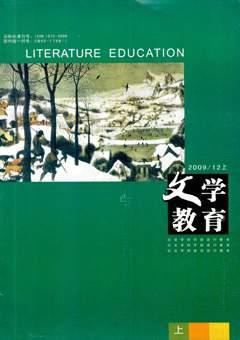西南聯大時期的沈從文
2009-04-13 05:29:20曾貞戴景敏
文學教育
2009年12期
曾 貞 戴景敏
沈從文在我心中一直是一尊神。雖然抗戰時期并不是一個適合造神的年代,而更適合造就英雄。但我一直固執地認為,這個時期也是神最有威信的時代,所以沈從文是最具備神性的作家,他在創造了自己具有神性的“湘西世界”的同時,也以一份戰士的勇氣,拉近了人與神的距離。他的《邊城》本身就是人世間最古老的神話,不管是作為文學家的沈從文還是后來作為文物家的沈從文,他一直以原始的文學技法,無需任何修飾卻任何人無法企及的修飾了人間的生活。
沈從文在西南聯大時期其實是寂寞的,但他似乎有一種天然抗拒寂寞的本領,在艱難的行路途中,沈從文總有一種精神在背后默默地支撐著他,鼓勵他向前走。他雖然不是知識分子出身,卻成了學者領域的帶頭人之一,并且成功地記錄了自己在文學天空中的投影。他在無形之中使自己成為中國新文學的代言人,宣判著人類的往事,即使是在后來,有人剝奪了他寫作的權利……
這樣的神,卻從未過著神一樣的榮耀的生活,相反地,在他并不順利的坎坷一生中,如同他行走在布滿荊棘的艱難的文學之路一樣,一生寂寞卻清醒。他仿佛被貶低到人間,混跡于社會底層的勞苦民眾中,他在現實中的身份應該是一個常常處于邊緣地帶的自由人。即使是在殘酷無情的現實生活中,即使是他在無奈之中消失在后來的文學史的視野中,這位執著的神,并沒有因此懼怕和后悔,他仍然坦然地承認自己的文學創作所追求的唯美風格與現實時代的差異。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