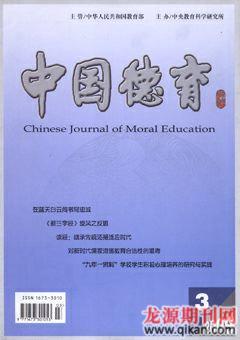“和”的含義及其對當代中國德育的啟示
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與胡錦濤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明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目標和途徑。就德育研究者而言,若想在當代中國人心中培育出既有深厚文化底蘊又能與現代文明良好對接的和諧倫理德性,就不能不準確弄清“和”的含義。因為“和諧”一詞本是將“和”與“諧”二字疊加使用的結果。據《廣雅?釋詁三》說:“和,諧也。”《說文?言部》說:“諧,詥也。從言,皆聲。”“詥”的讀音與含義有二:當其讀作“hé”時,其義為“諧”。《說文?言部》說:“詥,諧也。從言,合聲。”當其讀作“gé”時,其義為“會言”。《集韻?合韻》說:“詥,會言。”《六書統?言部》說:“詥,從言從合,合眾意也。”可見,當作“和諧、協調”解時,“和”與“諧”可以換用,正如《玉篇?言部》所說:“諧,和也。”合而言之,“和諧”一詞的含義本與“和”相通,只是古今漢語的表達習慣稍有不同而已:古漢語為突顯其用詞簡潔的特性,習慣以單個字為詞;現代漢語為配合今人的用語習慣,喜歡用兩個字或兩個字以上的合成詞。從古至今,“和”字經歷了一番演化,從中可以得出一些值得當代中國德育借鑒的東西。
一、“和”字字形與字義的演化
從字形上看,在古漢語里,“和”字有四種寫法,寫作宋體,即和、盉、龢與惒。其中,《漢語大字典》并未列出“惒”字字形的演化圖,只是作如下解釋:“惒”同“和”。《龍龕手鑒?心部》:“惒,琳師云,僻字也,今作‘和字。”《正字通?心部》:“惒,俗和字。”可見,“惒”同“和”,“惒”本是“和”的一種生僻寫法,因此,下文就不多講。在先秦時期,和、盉、龢三字是通用的,當作“協調、調和、調治、調校”等義理解時,和、盉與龢三字大體可以換用;當然,在這樣用時,三者之間也有細微區別。正如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盉》里所說:“調聲曰龢,調味曰盉。今則和行而龢、盉皆廢矣。……調味必于器中,故從皿。古器有名盉者,因其可以盉羹而名之盉也。”根據段玉裁的這一解釋,再結合相關古籍的書寫方式看,可以得出三個結論:(1)若細分,和、盉與龢三字的含義與用途有大小之分:盡管“龢”也可用于指調味,例如,《呂氏春秋?孝行》就說“熟五谷,烹六畜,龢煎調,養口之道也”,不過,在通常情況下,“龢”更常用的含義與用法只有一種,即主要用于指稱“調聲”,正所謂“調聲曰龢”;“盉”的含義與用法較之“龢”要多一些,除了可作專有名詞,專指“盉”這種古器名,也可泛指一般的調味器皿,還可用于指稱“調味”,即“調味曰盉”;“和”不但可以兼指“調聲”與“調味”,還可廣泛用于其他領域,尤其大量用于人際關系領域,并且,其地位還逐漸上升到與“同”相對的一個重要的古哲學術語,像《論語?子路》就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由此可見,“和”的含義與用途較之“盉”與“龢”二字要大、要廣。(2)和、盉與龢三字的使用時間長短有差異:從《漢語大字典》所列和、盉與龢三字的字形圖及相關解釋看,三字的起源都頗早,至少在金文里都已有這三個字的相應寫法。但是,“和”字較之“盉”與“龢”二字,不但在起源上同樣具有悠久的歷史,而且歷久彌新,延續至今仍在廣泛使用。(3)“和”字取代“盉”與“龢”二字,體現出漢字在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簡化”規律,換言之,正是由于“和”字較“盉”與“龢”二字的筆劃要少,書寫起來更方便,符合“方便實用”的一般規律,從而在與“盉”與“龢”二字的較量中最終勝出。由于上述三個原因的交互作用,隨著“和”字的興行,“盉”與“龢”二字逐漸被“和”字所取代,結果,“盉”與“龢”最終被中國人廢棄不用了。
“和”的本義有二:一是“調和味道”,簡稱“調味”或“和味”;二是“調和聲音”,簡稱“調聲”或“和聲”。中國先人對“和”的認識最初來自于飲食之和與聲音之和。當然,若細究,在“和”的這兩個本義中,“調和味道”之義較之“調和聲音”之義出現的時間可能會更早些,因為按一般常識以及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先民只有在滿足了飲食之類的生理需要之后,才會產生欣賞音樂之類的審美需要。
“和”既有調和味道或聲音、聲音相應和諧之義,由此很自然地就引申出協調、和諧、適中、和解等多種含義:“調和味道或聲音”與“聲音相應和諧”里本有“協調”與“和諧”之義,自然就能從“和”里引申出“協調”與“和諧”之義。要想將酸、甜、咸、辣等味道調配成可口的味道,就必須恰到好處地協調好各自的比例;同理,要想將五聲六律調配成美妙的音樂,也必須恰到好處地協調好五聲六律的比例,這樣,自然就能從“和”中引申出“適中”與“恰到好處”之義。一個人如能做到內心協調、身心協調、人我協調,自然就能從內心體驗到“喜悅”之情,在與他人交往時自然也就能做到“和順、平和、心平氣和、和顏悅色”“和睦、融洽”“和解、和平、結束戰爭或爭執”,于是,“和”里就又多出了這諸種引申義。無論是“調和味道”還是“調和聲音”,均意味著“要協調各方面的矛盾,使之和諧一致”,由是,從“和”里又引申出“在矛盾對立的諸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實現真正的和諧、統一”之義。可見,抽象地說,通過“和”獲得的事物,本是一種包含著差異、矛盾、互為“他”物的對立面在內的事物多樣性的統一。[1]正如《國語?鄭語》所說:“以他平他謂之和。”這意味著,和諧倫理精神的精義主要有三:(1)“天人之和”。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從正面說,要承認不同事物之間個別差異性的存在,要求人們要善于從事物的多樣性中去謀求一種和諧的統一關系,做到“天人合一”,人與自然萬物和諧共存、共同發展。從反面講,要避免以破壞自然、犧牲物種的多樣性為代價來一味滿足人的無限貪欲的諸種做法。(2)“人際之和”。在處理人與人(群)、群與群的關系時,從正面說,主張具有不同個性的人與人、人與群、群與群、民族與民族、國與國之間要彼此尊重,平等交往,養成一種具有共生取向的和諧發展的獨立人格,做到交往雙方彼此互尊、互助、互贏,從而實現人類社會的和諧共存、共同發展。從反面講,主張一個人或多個人(或群、或族、或國家)在與他人(或他群、或族、或國家)交往時,不要為了一味求同而放棄自己的個性,以至于形成一種依附性的人格。(3)“身心內外之和”。個體在處理自己的身心關系和主客我關系時,從正面說,要妥善協調自己的身與心的關系,主我與客我的關系,知、情、意、行之間的關系,做到身心和諧、心理和諧(即主、客我和諧,知、情、意、行彼此和諧),使自己的身心持久地處于舒暢的狀態。從反面講,一個人在修養身心時,要避免出現由于“身心內外失和”而導致的諸種弊病:身心一旦“失和”,個體容易產生“空有強壯身體卻心理不健康”“心理健康卻身體虛弱多病”“身心均不健康”等多種不健康狀態;主客我一旦“失和”,個體容易產生自傲心態(將“主我”想得太好,大大高于“客我”的實際發展水平)或自卑心態(將“主我”想得太差,大大低于“客我”的實際發展水平)等不健康心態;個體的知、情、意、行之間的關系一旦“失和”,就容易讓個體產生撒謊(因知行脫節)、行為粗魯(因行為缺乏理智或意志的合理調控)、義氣用事(行為完全由情緒控制、缺乏理智或意志的合理調控)、冷漠無情(因行為沒有善情的滋潤)等無禮或品行不端的行為,甚至違法亂紀的行為。
綜上所論,“和”里所蘊含的和諧倫理思想的精義至今看來仍頗為合理,與今天中國政府力倡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時代精神是相吻合的,與當今學術界風行的后現代思潮也有相通的一面。無論從積極層面還是從消極層面說,“和”都是一個很好的調節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群,群與群,民族與民族,國與國,身與心,主我與客我,知、情、意、行之間關系的準則。
二、對當代中國德育的啟示
(一)要樹立“和諧德育”的新德育理念
據《國語?鄭語》記載,西周時的史伯曾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萬事萬物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是由于各具特性的不同事情之間彼此和諧的結果,假若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是“相同”的,彼此之間沒有絲毫差異,就不會有事物的變化與發展。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本是宇宙的普遍規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先哲就運用此規律來看待世界,處理人世間的問題。前者如荀子在《天論篇》里明確提出“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的見解,以此表達其對宇宙萬物的態度;后者如孔子從待人處世的角度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著名命題,孟子從管理學角度力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主張,等等,由此使得中華民族形成了重視和諧、追求和諧的文化傳統及相應的心理與行為方式。
既然“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本是宇宙的普遍規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這就對當代中國的德育提出了新要求。因為德育本是一個由德育目標、德育內容、德育過程、德育方法、德育評價、德育環境、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等要素組成的系統,要想提高當代中國德育的實效性,就必須使德育的諸要素之間形成和諧統一的關系,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整體大于部分之和”。[2]同時,當代中國德育若要想更好地服務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就必須將其宗旨定在培育“身心和諧發展的人”上。[2]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并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只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為了獲得對別人和集體的適當關系,他必須學習去了解人們的動機、他們的幻想和疾苦。”[3] 310因此,“學校的目標始終應當是,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3]146。而所謂身心和諧發展的人,指個體的身與心(心主要包括德、智、情、意等四個方面)均得到和諧發展,從而使自己的身與心均更加健全的人。因為一個人只有自身實現了和諧發展,成為身心健全的人,才能為其后在處理人與人、人與群、人與自然的關系時實現和諧提供可能;[2]換言之,一個人若想實現家庭之和、鄰里之和、上下和睦和天下之和,前提條件之一是自己的身心要和諧。
可見,當代中國德育若想實現自身的和諧,若想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培育出大量身心和諧發展的建設者,就必須順應時勢,樹立“和諧德育”的新理念。所謂“和諧德育”的育德理念,其內涵是:人們(通常是教育者)根據當代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需要和個體(通常指受教育者)的主體需求,遵循品德形成與發展的內在規律,采取化育之類的有效手段,通過德育內外部諸要素的整體和諧互動,幫助個體實現“天人之和”“人際之和”“個體的身心內外之和”,進而促進個體逐漸生成“身心和諧發展的人格特質”,最終使個體的身心素質獲得和諧發展,從而成為一個身心健全的人。[4]一旦樹立起“和諧德育”的新理念,不但使當代中國德育能夠緊緊抓住時代發展的脈搏,從而更好地完成時代賦予自己的歷史使命;而且能夠使當代中國德育由于更加貼近人的內心要求,從而更易獲得人們的認同,消除過去常見的抵觸情緒,畢竟,從心理學角度看,任何一個心智正常的人都希望在自己的人生歷程中,于內能夠做到身心和諧發展,于外能夠做到與他人、社會和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和諧共存,共同發展。
(二)追求“真和”,去掉“偽和”
尚“和”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平衡人我關系與群我關系一貫信守的根本準則。這是由于,“中國人很早便確定了一個人的觀念,由人的觀念中分出己與群。但己與群都已包含融化在人的觀念中,因己與群全屬人,如何能融凝一切小己而完成一大群,則全賴所謂人道,即人相處之道”[5]。這樣,中國人一向重視人際交往與人際關系,幾乎將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與他人、自然的交往上,甚至中國人的宗教也多是他們人際關系的一個擴展,這導致有關人際交往和人際關系的思想在中國文化里占據重要位置。而在探討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時,由于多種機緣相互作用的結果,中國人自先秦以來就非常推崇“和”,以和為貴,以和為美,使得尚“和”成為中國人的一種“集體潛意識”。但是,稍通中國文化的人都知道這樣一個事實:在中國人的尚“和”心態里,其“和”有真偽之分。
所謂“真和”,指真正意義上的和諧人際關系。綜合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相關論述,能夠同時符合下列兩個標準的人際關系才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和諧人際關系:一是交往雙方都從心底彼此尊重并接受對方合情合理的個性特征,相互鼓勵對方發展自己的健全人格;二是做到“心和”,即交往雙方都要從心底彼此友愛對方,從心底彼此理解對方合乎道義或法律的所作所為,在此基礎上再通過民主協商對話、互容互諒或適度競爭等方式來尋求一種協調一致的關系。由此可見,“真和”精神里既包含尊重人的個性和主體意識的要義,也蘊含現代社會所推崇的平等、自由、民主的理念。
所謂“偽和”,指虛假的和諧人際關系。若細分,常見的“偽和”又可為兩個亞類:(1)“面和心不和”。交往雙方表面關系和諧,但心中彼此怨恨對方,或一方對另一方心存不滿甚或怨恨情緒。這是一種非常糟糕的人際關系,由此容易導致一些嚴重的后果:第一,它易使交往雙方或通常是處于弱勢的一方迫于有形或無形的壓力,為了維持虛假的和諧人際關系而暫時或持久地放棄自己的個性與主體意識,從而既不利于培養人們進行平等對話或民主協商的意識以及相應的素質與技巧,也不利于培養人們進行適度競爭或抗爭的意識以及相應的素質與技巧,這或許是造成一些中國人存在“逆來順受”或“聽天由命”心態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它易使交往雙方或某一方產生誤解,使雙方或某一方誤認為對方與自己實現了“和諧”,由此易使交往雙方或某一方做出錯誤的判斷與舉動。第三,它常常掩蓋了問題的實質,使問題不能得到真正的化解,結果,易招致雙方或某一方對另一方的不滿甚或怨恨情緒,從而埋下無窮的后患。現實生活里之所以會出現“面和心不和”,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五:第一,交往雙方或一方在中國傳統“尚‘和畏‘爭”與人情、面子文化的長期習染下,對“和”有一種非理性的執著與偏好,不是到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絕不撕破臉皮,明知“面和心不和”的弊病,也退而選擇之。第二,處于強勢的一方不尊重處于弱勢的一方的人格與正當權利及要求,而是利用自己的威嚴或權力,采取或顯或隱、或有意或無意的方式打壓對方,對方被迫無奈,只好“忍辱負重”,與強勢一方維持表面的和諧。第三,交往雙方或一方不能做到正視彼此之間存在的矛盾,并進而采取積極措施予以解決,而只是表面敷衍。第四,交往雙方或一方沒有真正理解和諧倫理精神的精義,誤將“面和心不和”視作“真和”。第五,交往雙方或一方雖本無意與對方進行真心交流,進而真心悅納對方,但鑒于“多個朋友多條路,多個敵人多堵墻”等做人“格言”,也不想“得罪”對方,于是采取“禮節性交往態度與方式”對待對方,而對方出于某種緣由——或同樣不想“得罪”對方、或處于不對等的劣勢、或善于做人等——也不予點破。(2)以“同”代“和”。“同”指“以水益水”[6],也就是無差別的一致之義。以“同”代“和”,就是以自我為中心,抹殺其他人的個性,從而謀求一種無差別的一致性人際關系。“以‘同代‘和”之所以是“偽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不符合“彼此尊重對方合情合理的個性”這一“真和”的實質精神。“以‘同代‘和”容易產生下述嚴重后果:它抹殺了處于弱勢群體的鮮活個性,使得一個群體內部由于缺乏不同的聲音而顯得單調,也使民主、協商、對話等溝通方式失去了生存的空間,從而極易滋生專制的管理方式;同時,容易讓被抹殺了個性的弱勢群體在心理產生積怨,進而于無形中削弱本群體的凝聚力,甚至給本群體的生存發展留下無窮后患。現實生活里之所以會出現“以‘同代‘和”,可能的原因主要有四:第一,交往雙方或一方沒有真正理解“和”與“同”的本質差異,誤將“同”視作“和”。第二,在特定場合(如抵抗侵略)或特定群體內部(像軍隊),有時“同人心”往往能產生巨大力量,正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是,一些人為了追求此種巨大合力,樂意放棄自己的個性。第三,管理者出于方便管理的需要,往往喜歡以“同”代“和”。因為群體內部一旦整齊劃一,管理者就無需考慮個體的個別差異,這樣管理起來就方便一些;反之,管理者若充分尊重與考慮群體內部不同個體的個性差異,就需運用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方式,這對管理者是一個極大挑戰,一些缺乏民主素養的管理者權衡利弊之后往往選擇以“同”代“和”。第四,受中國傳統“群體優先”思維方式的深刻影響,當群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相矛盾時,一些人自愿或被迫放棄自己的個性,便極易出現以“同”代“和”。
當代中國德育須大力宣揚“追求‘真和,去掉‘偽和”的做人理念,只有當人人都樹立起了“真和”的理念,才有助于“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才真正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立。
(三)培育新型君子人格是落實和諧倫理精神的一項重要舉措
在孔子心中,君子人格的特質有仁、義、禮、智、信、忠、恕、勇、中庸、謙虛、和而不同、文質彬彬、自強等13種。當然,上述13種人格特質的重要性是不一樣的。若借用現代人格心理學的術語,上述13種人格特質中的后9種特質只是君子人格的表面特質,前4種特質才是君子人格的根源特質。因為,第一,孔子曾說:“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可見,一個人一旦有“仁”,其內必有“勇”的素質。第二,孔子所講的“忠”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正是“仁者”的品質。第三,以謙虛謹慎、和而不同、誠信和自強的方式做人,以中庸的方式待人接物,這都體現了一個人的做人智慧,換言之,擁有做人智慧的君子也就擁有了中庸、謙虛、誠信、和而不同與自強的表面特質。第四,一個人若能做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自然既儒雅又有禮貌,能給人一種文質彬彬的良好印象。
用德育心理學的眼光看,正是由于個體通過“修身養性”的方式使自己獲得仁、義、禮、智等四種特質,從而使自己成為了“君子”。這樣,于內可以使自己恰如其分地調節身與心,從而實現“身心之和”和“主客我之和”;于外則能夠做到用“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諧”的思想來處理天人關系與人我關系。一方面,君子以“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式實現“天人之和”。“有所為”,指君子在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中,往往積極進取,善于利用自然來為自己服務,正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有所不為”,指君子在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中,又善于做到適可而止。為了使自己能與外部環境和諧相處,必會自覺地約束自己的言行,做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以使自己的言行“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另一方面,君子運用“和而不同”策略實現“人我之和”。正如孔子所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大學》所講的“三綱領八條目”表達的正是此意:“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講的是“修身工夫”,憑此而使個體具備“君子”的素養,其中極少數做到極高明處的個體就具備了“內圣”的素質。北宋邵雍在《皇極經世?觀物篇四十二》里說的“圣也者,人之至者也”“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正是君子所宜努力去做的“推己及人與物”的“外王功夫”。由此可見,具備君子人格的人最能真切體悟并身體力行和諧倫理精神。明白了這一點,就能理解何以孔子愿意花那么大的力氣去鼓吹君子人格,何以秦漢以降的中國傳統文化如此推崇君子人格,何以宋明理學家將本只是《禮記》中的一篇《大學》抬高到“四書五經”之首。
當然,君子人格不是天生的,而是通過后天教育生成的。正如楊雄在《法言?學行》里所說:“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同時,君子人格是一個有濃厚中國文化色彩且深受中國人喜愛的概念,只要稍加詮釋與轉換,就能將君子人格的精神實質理解成一種具有自尊、仁愛、寬恕、平等、民主、進取等德性,且具共生取向、身心和諧發展的健全人格,這種人格正好是和諧德育所要努力追求的。既然如此,采取有效措施培育個體的新型君子人格,就是在當代中國德育里落實和諧倫理精神的一項重要舉措。
參考文獻:
[1]方克立.關于和諧文化研究的幾點看法[J].高校理論戰線,2007,(5):4—8.
[2]金雁,楊柳.關于和諧德育的思考[J].道德與文明,2007,(1):84—87.
[3]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M].許良英,等,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4]魯潔,王逢賢.德育新論[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128—129.
[5]錢穆.民族與文化[M].香港:新亞書院,1962:6.
[6]徐元誥.國語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2002:470.
【汪鳳炎,南京師范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文化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的研究。江蘇南京,210097】
責任編輯/趙 煦
*本文系全國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教育部重點課題(項目批準號:DEA070061)的系列成果之一;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基金資助(項目批準號:07JJD88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