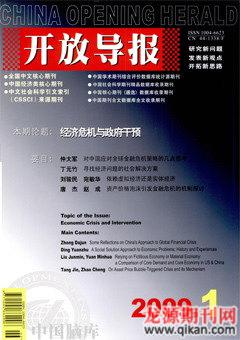調(diào)整耕地保護制度是推進土地市場化改革的關(guān)鍵
[摘要]當前中國土地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困境,源于參與土地市場交易的各個利益主體之間利益不相容,導致現(xiàn)行土地管理制度運行費用奇高,并使地方政府成為其中矛盾的焦點。要破解這種困局,必須改革現(xiàn)行的耕地保護制度。其調(diào)整的方向是要建立農(nóng)民自己保護自己耕地的機制,關(guān)鍵是提高土地農(nóng)業(yè)利用的比較收益。
[關(guān)鍵詞]土地市場化改革耕地保護制度
[中圖分類號]F3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6623(2009)01-0076-04
[作者簡介]劉憲法(1955一),河北邢臺人,綜合開發(fā)研究院(中國·深圳)主任研究員。研究領(lǐng)域:理論經(jīng)濟學、宏觀經(jīng)濟。
土地市場是土地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即以產(chǎn)權(quán)交易的方式完成土地資源的配置。中國土地制度經(jīng)過了近30年的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土地資源配置方式的市場化成分逐步增加。但是,與其它要素市場如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相比,土地市場化程度還很低,行政方式仍然是配置土地資源的主導方式。從產(chǎn)權(quán)交易的視角看中國現(xiàn)今的土地市場,我們可以將士地市場分為:農(nóng)用地流轉(zhuǎn)市場、農(nóng)地轉(zhuǎn)用市場(征地)和城市土地出讓市場。本文只分析后兩個市場。
當前中國土地市場化改革的困境
中國現(xiàn)今土地市場化程度低主要是指農(nóng)地轉(zhuǎn)用環(huán)節(jié)。本來任何一種產(chǎn)權(quán)交易,其結(jié)果必然要發(fā)生用途的轉(zhuǎn)變,否則就沒有交易的必要了。例如,把鋼材賣給汽車生產(chǎn)者,汽車生產(chǎn)者就會把鋼材變?yōu)槠囓囬T或汽車底盤。這就是說,轉(zhuǎn)用和出讓的交易本來應(yīng)該是一體的。然而,在中國的土地市場上,農(nóng)地轉(zhuǎn)用與農(nóng)地轉(zhuǎn)用后出讓是分離的,即必須先將農(nóng)村的集體土地變?yōu)閲薪ㄔO(shè)用地,再由政府將土地使用權(quán)出讓給最終的土地使用者。農(nóng)地轉(zhuǎn)用環(huán)節(jié)上政府以國家的力量強制或半強制地迫使農(nóng)民與其達成農(nóng)地轉(zhuǎn)用的交易。這就違反了市場交易的基本原則即自愿交易的原則。由于農(nóng)地轉(zhuǎn)用必須通過政府來完成,所以,政府也就成為城市土地出讓市場的獨家壟斷的供應(yīng)者。政府成為土地市場的主導者。
然而問題是這種土地產(chǎn)權(quán)交易的合約安排是否有效率,是否可持續(xù)。目前在中國土地管理中暴露出來的眾所周知的問題告訴我們,這種土地產(chǎn)權(quán)交易的合約安排的效率是較低的,也是不可持續(xù)的。這種合約安排的低效率和不可持續(xù)性,根源于這種制度的運行成本太高,而制度運行成本太高又根源于參與土地交易的各個行為主體的利益嚴重不相容。從經(jīng)濟學上講,利益相容是指參與產(chǎn)權(quán)交易各個主體互通有無、各取所需,都能在交易中得到好處。
在現(xiàn)今中國的土地市場上,參與土地交易的行為主體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農(nóng)民和用地投資商。其各自在土地市場上的行為取向是:中央政府關(guān)注耕地保護,以保障糧食安全,并保護農(nóng)民的利益,以維護社會穩(wěn)定;地方政府更為關(guān)心的是如何利用手中的土地權(quán)力發(fā)展本地經(jīng)濟,提高政府財政收入包括土地收入;農(nóng)民的訴求是失地后生活要有保障,并能最大限度地參與農(nóng)地轉(zhuǎn)用后的土地增值分配;用地投資商的利益則是通過取得土地,發(fā)展實業(yè),實現(xiàn)其收益最大化。從上述各行為主體的行為取向來看,一般來說,地方政府與用地投資商的利益是相容的,除非用地商取得土地是為了炒作,而不是為了實業(yè)投資。因此,中國目前涉及到地方政府與開發(fā)商利益關(guān)系的土地出讓市場的運作還算比較健康。利益不相容主要發(fā)生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地方政府與農(nóng)民之間。矛盾的焦點在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要實現(xiàn)其發(fā)展本地經(jīng)濟、招商引資、改善城市面貌的目的,就要增加城市建設(shè)用地,向農(nóng)民征地。因此,地方政府有內(nèi)在的擴張城市土地的沖動。中央政府為了糧食安全,同時也為了防止失地農(nóng)民太多,引起社會的不穩(wěn)定,就要采取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實行嚴格的土地計劃指標管理。在現(xiàn)實中,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土地計劃指標管理上的矛盾和沖突最為明顯。據(jù)筆者在各地的調(diào)研,在許多發(fā)達城市,土地計劃指標遠遠不能滿足其用地的需求。地方政府要采取各種手段,挖空心思向中央或省政府爭取擴大其用地指標,特別是避開中央的基本農(nóng)田保護制度。對許多地方政府來說,耕地保護制度幾乎成了“緊箍咒”。在現(xiàn)實中,農(nóng)民也不是耕地的保護者。在遠離城市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地區(qū),拋荒撂荒的土地到處可見,在城市近郊地區(qū),農(nóng)民則想方設(shè)法地將農(nóng)地變?yōu)榻ㄔO(shè)用地,搞農(nóng)民工業(yè)園,建住房。
地方政府與農(nóng)民之間的矛盾主要在征地上。在現(xiàn)行的稅制環(huán)境下,地方政府為了發(fā)展經(jīng)濟,解決建設(shè)資金不足的問題,勢必會盡可能地壓低征地補償費用。農(nóng)民以土地的“原住民”的身份優(yōu)勢,則盡量要提高征地補償費用。這使地方政府的征地難度越來越大,談判成本也越來越高。
征地難度大的根源在于土地的位置是不可切割的,也就說,某一塊土地的位置是和與此相鄰的土地所共享的,是屬于共處在一個位置上的農(nóng)民的“公共財產(chǎn)”,單獨售出或購買其中的某一塊土地是沒有什么價值的。這在經(jīng)濟學上講,這就是“毗鄰效應(yīng)”。對于土地這種具有很強“毗鄰效應(yīng)”的品種,其交易必須采取“捆綁銷售”或“捆綁購買”的方式,無法“拆零購買”。政府要征地,就得連片統(tǒng)一征,不能一戶一戶地來,否則,有一戶不同意,這筆交易就無法正常進行。在“捆綁購買”的模式下,如果土地的購買者別無選擇的話,那么,一定是以要價最高的村民為準,最高要價決定實際成交價格。這是因為,雖然每個村民的最低心理價位各不同,有高有低,但是可以使每個村民全都滿意的價格,只能是使要價最高的村民也滿意的價格。在這個可以漫天要價的市場上,理論上說其價格將趨于無窮大,價格是發(fā)散的,不存在供需均衡的價格,所以交易也就無法進行。
以上分析表明,在當今中國土地市場上已經(jīng)形成了解不開的“死結(jié)”。中央政府要保護耕地,就要強化土地計劃管制,土地管理權(quán)力越來越向中央政府集中。但是,中央政府又不能親自管理土地,必須委托給地方政府,同時也要照顧地方政府發(fā)展經(jīng)濟,改善城市建設(shè)的愿望。畢竟發(fā)展經(jīng)濟,推進城市化也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標。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勢必要根據(jù)自己本地經(jīng)濟發(fā)展情況,包括根據(jù)地方執(zhí)政者自身的意愿,盡量擴大中央政府賦予他們的土地權(quán)力,與中央政府進行土地博弈。博弈的結(jié)果往往是地方政府勝出。這是因為,有關(guān)土地的知識是典型的地方性知識,中央政府在土地信息方面處于絕對劣勢。在此形勢下,中央政府不得不進一步加大對土地的監(jiān)管力度,一方面以罷官免職相威脅,迫使地方政府就范,另一方面出臺各種土地管制措施,堵住監(jiān)管漏洞,不僅在土地數(shù)量上進行嚴格管理,甚至發(fā)展到對土地價格也要進行嚴格管控的地步。如國土資源部出臺了《全國工業(yè)用地出讓最低價標準》,要求各省要制定征地區(qū)片綜合地價等。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與征地農(nóng)民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中央政府不斷向農(nóng)民傳遞維護其土地權(quán)力的信號,有了中央政策的撐腰,征地農(nóng)民越來越強勢,要價
越來越高,地方政府為了對付這些所謂的“刁民”,不得不采取各種非正常的手段,這進一步引起征地農(nóng)民對地方政府的不滿。在征地問題上,一些地方政府已經(jīng)被扮演為“惡霸”的形象。農(nóng)民不滿,地方政府也苦不堪言。這種產(chǎn)權(quán)交易的合約安排的結(jié)果是,一方獲利必須要以侵害另一方的利益為代價,這樣的制度是不可持續(xù)的,已經(jīng)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調(diào)整耕地保護制度
是推進土地市場化改革的關(guān)鍵
從根本上說,當前中國土地市場化改革出現(xiàn)的困境,是其產(chǎn)權(quán)交易的合約安排使然,要想改變這種產(chǎn)權(quán)交易的合約安排,就要改變其外部約束條件。決定目前中國城市土地產(chǎn)權(quán)交易合約安排的最硬的外部約束條件是耕地保護制度。現(xiàn)行的耕地保護制度不調(diào)整,土地計劃管制就不可能放開,因為任何能夠推進土地市場化的制度,都會造成對現(xiàn)有耕地保護制度的沖擊。而且,目前中國的耕地保護制度是一個世界上最扭曲的制度。管轄這片地的地方政府不愿保護耕地,種地的農(nóng)民也不愿保護自己的土地,真正把耕地掛在心上念念不忘的是中央政府。這種耕地保護制度是不可能有效地運行的,而且維持其運行的成本也會奇高。耕地保護制度調(diào)整的方向是要建立農(nóng)民自己保護自己耕地的機制。
如果建立了農(nóng)民自己保護自己耕地的機制,中央政府就可以逐步放開對土地的管制,打破政府對土地市場的壟斷,農(nóng)民可以直接與土地使用者達成土地使用權(quán)轉(zhuǎn)讓的交易,而不必一定通過地方政府。在現(xiàn)階段,可以先放開政府對農(nóng)村集體建設(shè)用地的轉(zhuǎn)地和出讓的壟斷。
因為建立了農(nóng)民自己保護自己耕地的機制,農(nóng)民自己手中的土地升值了,農(nóng)民也不會隨意將農(nóng)用地轉(zhuǎn)為建設(shè)用地。假定市場結(jié)構(gòu)比較完善,農(nóng)民轉(zhuǎn)地交易的邊際收益就會趨向于與耕地的邊際收益相等。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的管理重點是土地利用規(guī)劃。以及對用地投資商的資質(zhì)、信用、土地使用方向、投資規(guī)模等進行監(jiān)管,防止用地投資商利用與農(nóng)民信息不對稱的優(yōu)勢,巧取豪奪農(nóng)民的土地。由于用地投資商在購買土地時,要與眾多的農(nóng)民打交道,市場交易費用會大幅上升,地方政府可以在促成農(nóng)民與用地投資商的交易,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發(fā)揮作用。這樣,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保護農(nóng)民利益、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利益取向完全相容。
由于是多主體供地,必然存在著競爭,并且遵循著自愿交易的原則,所以不會出現(xiàn)交易的一方對另一方利益的侵害,也不會出現(xiàn)農(nóng)民“漫天要價”的情況。因為用地投資商是有選擇的。這里地價太高,我就到別處投資。在廣東珠三角地區(qū),農(nóng)民由村集體與用地投資商私下進行土地交易的情況很普遍,據(jù)筆者觀察,并沒有出現(xiàn)不公平交易的現(xiàn)象。在土地由農(nóng)業(yè)轉(zhuǎn)為建設(shè)用地過程中,必然產(chǎn)生大量的租值,在自愿交易的前提下,農(nóng)民和用地投資商通過土地產(chǎn)權(quán)交易可以從中分享土地轉(zhuǎn)用的租值,地方政府也可以通過收取土地交易稅,得到自己應(yīng)得的一份。農(nóng)民與用地投資商及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也是完全相容的。同時,在多主體供地情況下,土地市場的競爭就可以充分地展開,土地稀缺程度以價格信號形式在市場上充分地顯示出來,價格信號引導著土地的資源配置,促進了土地的集約利用。
“天下沒有免費的晚餐”。實行這種制度可能隨之出現(xiàn)的問題是,農(nóng)地的交易主體是誰,如何形成村集體內(nèi)部收益分配的合約安排。在現(xiàn)行的農(nóng)村集體土地所有的制度下,這確實是一個難題,但這是另外的問題,這里先不討論。
最后的問題是如何建立農(nóng)民自己保護自己耕地的機制。世界上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都要保護,大熊貓要保護,因為它有價值,老鼠不保護,因為它沒有價值。如果有價值的東西沒有人愿意保護,其原因主要有二個:一是由于存在市場缺陷,市場低估了其實際價值;二是產(chǎn)權(quán)不明晰,其持有者對其可能產(chǎn)生的收益沒有穩(wěn)定的預(yù)期,使其具有公共品的性質(zhì)。在目前中國土地制度框架下,對耕地保護均存在上述兩個問題。既然耕地保護是國家的一項重要國策,這就表明,耕地已經(jīng)具有公共品的性質(zhì)。國家就要承擔其責任,并為此付出費用。現(xiàn)代產(chǎn)權(quán)理論證明,當出現(xiàn)私人價值與社會價值不一致時,對資源濫用或租值耗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一個有效率的解決途徑是提高農(nóng)民耕地利用的價值,使耕地利用的私人價值與其社會價值相等。這是建立農(nóng)民自己保護自己耕地機制的關(guān)鍵。具體地說,就是要提高土地農(nóng)業(yè)利用的比較收益。筆者建議,首先要縮小國家基本農(nóng)田的保護范圍,比如在黑龍江、吉林、內(nèi)蒙、河南、山東、湖北等若干產(chǎn)糧大省,確定特定區(qū)域,劃定“紅線”,建立國家級的基本農(nóng)田保護區(qū),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中央政府要想將18億畝耕地全部保護起來實際上是不現(xiàn)實的,縮小國家基本農(nóng)田的保護范圍后,國家可以僅對區(qū)內(nèi)的糧食實行價格補貼,把糧價抬高。國家基本農(nóng)田保護區(qū)的糧價上升必然帶動整體糧食市場的價格上升,土地農(nóng)業(yè)利用的比較收益提高了,土地也就值錢了,農(nóng)民自然就會珍惜手中土地。
如果糧價上升引起了糧食生產(chǎn)過剩,那就傳遞了一個信號,說明在土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中國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農(nóng)用土地,這時政府便可以減少對糧價的補貼,并導致市場糧價下跌,土地農(nóng)業(yè)利用的比較收益下降,農(nóng)用地轉(zhuǎn)為建設(shè)用地的速度加快,直至調(diào)整到土地農(nóng)業(yè)利用的最佳均衡點。這就是說,中國到底需要多少耕地,是18億畝,還是19億畝,還是17億畝,并不是中央政府能夠計算出來的,對耕地的真實需求只能由市場決定。最近出現(xiàn)的有關(guān)對茅于軾否認18億畝耕地保護的爭論,其問題的實質(zhì)是糧食供給是否與耕地數(shù)量存在著一一對應(yīng)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是技術(shù)經(jīng)濟關(guān)系所決定,還是社會經(jīng)濟關(guān)系所決定。中國上世紀60年代發(fā)生的“大饑荒”的歷史經(jīng)驗充分表明,引發(fā)糧食供給短缺的原因一定是糧食供需形成機制出現(xiàn)了問題,是一種社會經(jīng)濟現(xiàn)象。反對茅于軾觀點的人,其在理論上的錯誤在于,這些人誤將微觀技術(shù)層面上的耕地與糧食產(chǎn)出的技術(shù)經(jīng)濟關(guān)系,視為社會經(jīng)濟層面上的耕地與糧食供給的關(guān)系。基本的經(jīng)濟學道理告訴我們,決定產(chǎn)品供需關(guān)系的關(guān)鍵因素是價格,這對于糧食也不例外。耕地只是糧食潛在產(chǎn)出的決定因素,但不是糧食真實供給的決定因素。當然這只是在一個比較理想狀態(tài)下的分析,現(xiàn)實問題要比這復(fù)雜得多。
在中國目前大量農(nóng)村勞動力有待轉(zhuǎn)移的情況下,農(nóng)用地邊際收益要達到與建設(shè)用地邊際收益大體相等,尚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因此,要有一系列過渡性的制度安排。筆者建議對耕地保護實行分級管理的模式,除了國家直管的基本農(nóng)田保護區(qū)外,對農(nóng)業(yè)大縣可以采取省直管縣的方式,將農(nóng)業(yè)、農(nóng)地的管理職責交給省級政府。目前的市管縣的制度,實際上為城市侵蝕農(nóng)村的土地提供了制度性的條件。同時,提高農(nóng)業(yè)縣縣級政府的地位和級別,農(nóng)業(yè)大縣的級別可與市相同。對農(nóng)業(yè)大縣以糧食產(chǎn)量作為政績考核指標,其農(nóng)業(yè)補貼由省級政府負責。“三農(nóng)”問題事關(guān)社會的穩(wěn)定和農(nóng)民出路,省級政府就有動力管好其行政管轄區(qū)的農(nóng)地。省級政府可以根據(jù)本省的實際情況,制定本省的農(nóng)地管理條例,規(guī)范所轄縣級地方政府用地行為。這樣就可以通過分散管理農(nóng)地的方式,減少保護耕地的成本。而城市地區(qū)的政府對農(nóng)地管理的職責主要放在解決城市居民的“菜籃子”上,對其他土地的管制則逐步放開。除此之外,還需要研究在WTO的規(guī)則框架下,如何避免國際糧價對國內(nèi)市場的沖擊,如何克服農(nóng)產(chǎn)品市場的蛛網(wǎng)效應(yīng)等等問題。筆者將另文論述。
責任編輯張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