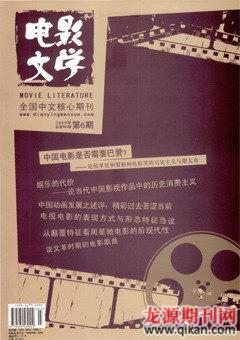不同的文化背景對人性的相同闡釋
陳 雷 趙紅軍
[摘要]作為文學(xué)大師,庫切和張愛玲雖然生活在不同的國度,植根于相異的文化土壤,但都以對人生與人性的剖析,揭示了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個(gè)體人由于受到來自社會的外在勢力以及自身內(nèi)在欲望的左右,使人生與人性在不同程度上產(chǎn)生了異化和扭曲。他們這種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對人性的相同闡釋,反映了全球化語境中東西方文化、文學(xué)的碰撞與交融。而通過相同闡述,使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文化、文學(xué)交融的特質(zhì)。
[關(guān)鍵詞]欲望;人性;異化;《恥》;后殖民主義;道德
2003年度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庫切是當(dāng)代南非的重要作家,他的小說不僅有著獨(dú)特的藝術(shù)形式,深刻的思想內(nèi)涵也格外引人注目。他不僅寫出過《等待野蠻人》等隱去了時(shí)代和地域背景的寓言式作品,也寫出了以南非的殖民地生活和各種沖突為背景的寫實(shí)性作品,《恥》就是這后一方面的代表作。這部著作是庫切近年創(chuàng)作的一部優(yōu)秀的長篇小說。小說通過對開普技術(shù)大學(xué)教授戴維·盧里的性放縱行為及其為此承受的后果的敘述,揭示了人的本性與社會道德規(guī)范的沖突。在欲望的凸顯所導(dǎo)致的父女倆的人生悲劇中反思?xì)v史與現(xiàn)時(shí),并以此為基點(diǎn)對人性中的欲望加以深刻而獨(dú)到的揭示。
在小說中庫切用簡潔的語言、令人心怵的筆調(diào)和使人震撼的情節(jié),講述了開普技術(shù)大學(xué)教授戴維·盧里為了得到性欲的滿足三番五次地“越軌”,與幾乎他所能得到手的任何一個(gè)女性有染,甚至連他的女學(xué)生梅拉妮也不放過的故事。就年齡而論,盧里比梅拉妮大上三十幾歲,按常理是不折不扣的父輩;就關(guān)系而言,他們是師生,可盧里不顧梅拉妮的反對,一次次地利用他作為一名教師的權(quán)力以及在地位、學(xué)識和經(jīng)歷上所構(gòu)成的強(qiáng)勢,對梅拉妮進(jìn)行勾引。在道義上,不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這都是不可理喻的,為社會所不允許的。所以盧里為此丟掉了教授的職位,并使自己掉到了恥辱的最低線。為了逃避恥辱,盧里躲到了女兒露茜所在的偏僻鄉(xiāng)村的小農(nóng)場,在那里他經(jīng)歷了自己的女兒露茜遭受黑人強(qiáng)暴的又一次恥辱。在小說中,庫切一而再、再而三地所提到的恥辱不過是個(gè)表層解構(gòu),它就像一個(gè)罩子覆蓋了作者所要揭示的各個(gè)層面,覆蓋了故事發(fā)展的種種矛盾和沖突,覆蓋了從殖民統(tǒng)治到其瓦解的整個(gè)過程。而在這個(gè)過程中人性中的欲望時(shí)時(shí)都在左右著各種矛盾與沖突。
根據(jù)弗洛伊德的心理哲學(xué),“人的心理結(jié)構(gòu)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個(gè)部分。‘本我包含了所有原始的遺傳的本能和欲望,宛如‘一口充滿著沸騰的激動的大鍋,其中最根本的是性欲沖動,即所謂‘性力,它為各種本能沖動、欲望提供力量,是人的整個(gè)精神活動的基礎(chǔ)和源泉。”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盧里自然也需要這樣的“源泉”。可作為一個(gè)單身漢,他是如何解決這個(gè)問題的呢?請看小說開頭的一段描述:
他覺得對自己這樣年紀(jì)五十二歲、結(jié)過婚又離了婚的男人來說,性需求的問題可算是解決得相當(dāng)不錯(cuò)了。……等著他的是索拉婭。……從年齡上說,他足以做她的父親,……他成為她的顧客已經(jīng)有一年多時(shí)間了,而且覺得她令自己心滿意足。在荒蕪一周的時(shí)間里,星期四成了一塊奢華與肉欲的綠洲。
如果說盧里同索拉婭的關(guān)系是為了解決他基本的性需求的話,那么后來他對其學(xué)生梅拉妮的勾引,則使他在這條“基本的性需求”的道路上越走越離譜:
對那女孩的回憶毫無先兆地回到了他腦海中:那對輪廓清晰的乳房,堅(jiān)實(shí)地挺立著的乳頭,平滑的小腹。欲望涌起,使他渾身不由得一陣顫抖。很明顯,不管事情發(fā)展到了什么地步,它遠(yuǎn)沒有結(jié)束。
可悲的是,盧里生活在現(xiàn)代文明之中,而不是原始的野蠻社會。在這樣的文明社會中只是一味地追求肉欲而不顧道德倫理,就會失去平衡,從而導(dǎo)致恥辱甚至犯罪。很顯然,盧里在這種沖突中打破了理性世界的道德禁忌,不顧倫理規(guī)范的約束,倒向了本能的沖動與發(fā)泄一邊。從而導(dǎo)致了他的人生悲劇。小說中盧里的心路歷程,人格表現(xiàn)錯(cuò)綜復(fù)雜,具有多層面性。從現(xiàn)代文明與道德的層面上看,他本為人師,卻放縱肉欲,再三地勾引梅拉妮,確實(shí)可恥。從人的本性、也就是“本我”層面上看,52歲的他孤零零只身一人,無以聊慰,最后不得不同一個(gè)五短身材、體形肥胖,一臉黑麻子,剪著個(gè)平頭,腦袋似乎就垛在肩膀上的女人有染,以解決“本我”的沖動,確實(shí)可憐。從理性世界與非理性的原欲沖突層面上看,由于他在道德上的失控,以致給他人帶來傷害,而失去立身之地,不得不躲在女兒偏僻的小農(nóng)場;在那里明知女兒遭強(qiáng)暴卻又無能為力,無法保護(hù)處于弱勢的女兒,確實(shí)可悲。然而透過這可恥、可憐以及可悲的父女倆的個(gè)人命運(yùn),我們看到的所有的這一切都與人的欲望和“那段錯(cuò)誤的歷史”有關(guān)。
《恥》的深刻就在于庫切不是簡單地把問題放在欲望的層面上進(jìn)行處理,而是從欲望的凸顯中尋到了矛盾和沖突的根基所在,從實(shí)實(shí)在在的發(fā)生中抽象出了人生的哲理,悲劇的根源。小說中“對人性分析是以人為本的,它不受任何既定的框子所左右,明晰、深刻,仿佛是一把無形的刀子,將人性一層一層地剝離開來,讀者看到的是最深層的人性的肌理。”而欲望是傷害人性肌理的最大禍根。如果說盧里為之付出代價(jià)的原因是肉欲的凸顯的話,那么殖民者對南非的侵入便是一種強(qiáng)烈的占有欲。作者把殖民者由于欲望的凸顯所造成的悲劇放在現(xiàn)代文明與歷史擴(kuò)張的大背景中,使作品有了內(nèi)涵與外延的雙重延伸,在內(nèi)涵上,盧里被裹挾在現(xiàn)代文明的束縛與人的最本質(zhì)的東西——“本我”彰顯的矛盾中,這種矛盾釀成了盧里的人生悲劇。而其內(nèi)涵的真正意義所探討的不僅僅是主人公的個(gè)人悲劇,他是現(xiàn)代人的悲劇之所在,盧里不過是其中的一個(gè)代表、一個(gè)符號。庫切筆下的欲望是在殖民主義以及后殖民主義的歷史大背景中凸顯的,反過來作為利欲熏心的人在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掙扎中被深深地打上了歷史的印記。
如果說庫切是把人性與欲望放在殖民者對非洲大陸進(jìn)行瘋狂侵略的歷史層面加以揭示的話,那么張愛玲對此所做的剖析則是來自于生活在東方中國的平民百姓中形形色色的個(gè)體。在欲望的驅(qū)使下,她筆下的一個(gè)個(gè)小人物在互相殘害的同時(shí)也殘害著自己,玷污自身的心靈。張愛玲以人的內(nèi)心世界特別是女性的內(nèi)心世界為切入點(diǎn),撕開了人性中沉重的一角,那便是欲望。張愛玲在對人性的探索中,憑借她筆下一張張凡夫俗子的面孔,揭露出人性深處的陰暗、自私、虛偽和孤獨(dú)。他們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傾軋下,人性變得恐怖不堪,靈魂變得陰暗,丑陋無比。在她的作品中,欲念對人的異化展示得最為徹底的就是《金鎖記》中她所精心刻畫的曹七巧。在物欲的驅(qū)使下,曹七巧這個(gè)小家碧玉,為了高攀名門望族,甘愿嫁給一個(gè)殘廢男子,為了以正室的身份獲得她那一份財(cái)產(chǎn),她不得不委曲求全,將心底里的那份情欲壓抑下去。結(jié)果當(dāng)情欲變相地借金錢顯形時(shí),她的人性扭曲了。她慢慢地蛻變成另外一個(gè)七巧。作者并沒有在性格這個(gè)層面上對人物進(jìn)行過多刻畫,而是把筆墨轉(zhuǎn)移到精神,轉(zhuǎn)移到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在曹七巧的心中,由于欲望的左右,她施展各種“法術(shù)”,人物性格的多極變化也在這法術(shù)施展的過程中不斷地得到展示。張愛玲的另一篇小說《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對物欲的追求雖不像曹七巧那樣強(qiáng)烈、那樣執(zhí)著、那樣直截了當(dāng),但這位“破落戶”的離婚女兒,在被窮酸兄嫂的冷嘲熱諷攆出娘家后,跟一個(gè)飽經(jīng)世故,精明情場的老留學(xué)生范柳原談戀愛,互相之間的真真假假和吸引、挑逗以及頗費(fèi)心機(jī)的攻守之戰(zhàn),都無時(shí)無刻不透露出白流蘇的欲望,那便是為自己找一個(gè)經(jīng)濟(jì)上的依靠。
在張愛玲的作品中,不論是曹七巧、白流蘇還是葛薇龍,不論她們的結(jié)局怎樣,命運(yùn)如何,她們都是欲望的俘虜,金錢的奴隸。中國文學(xué)“不能以風(fēng)土人情取悅外國讀者,也不能以政治上的反對派吸引外國讀者,這樣的時(shí)代已經(jīng)過去了,中國作家必須寫出真正的中國人”。自從魯迅在尼采的影響下塑造了阿Q這種典型的小人物之后,形形色色的平民百姓便在中國作家的筆下勾勒出來了。以“惡俗不堪”而著稱的張愛玲,用她的筆去探究一個(gè)個(gè)凡夫俗子的心理世界,挖掘著他們意識的底層,從而觸摸到了罪惡的根源——欲望。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你、我、他,誰都無法回避同欲望之間的糾葛。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各自都在施展著自以為是的拙劣伎倆。讀張愛玲的小說讓我們品嘗的就是這人生的百味。她用這人生的百味,揭示了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所關(guān)注卻又解不開的欲望之謎。
綜上所述,分別生活在東西方的這兩位文學(xué)大師——庫切和張愛玲在揭露社會、展現(xiàn)人生、剖析人性時(shí)雖然切入點(diǎn)不同:一位將人性中的欲望放在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大潮進(jìn)行拷問,另一位則從人性的內(nèi)在本質(zhì)入手,但他們的目標(biāo)卻是一致的,就是對人的歷史、人的本質(zhì)、人的命運(yùn)、人的處境、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及人與社會的關(guān)系進(jìn)行思考、揭示與批判。不同的地域,相異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各異的語言。是什么使他們的目標(biāo)如此一致呢?這便是全球化語境中東西方文化、文學(xué)的碰撞與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