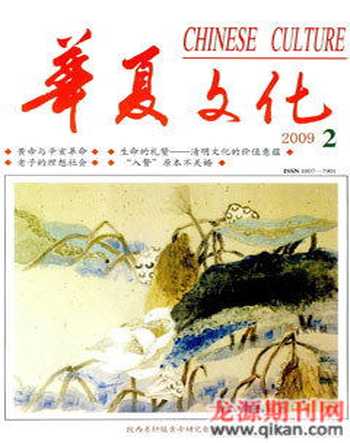“入贅”原本不關婚
羅獻中
提起“入贅”,人們并不陌生,都知道它是舊時民間的一種特殊的婚姻方式,即“人贅婚”,俗語叫“倒插門”,是指男子到與之訂婚的女方家結婚并成為女方的家庭成員。可是,很多人卻不知道,“入贅”原本與婚姻并無關系;“入贅”一詞當初也并非婚姻方面的用語。
“入贅”原本是指什么呢?與什么有關呢?要揭開“入贅”的“本來面目”,關鍵是需要索解“贅”字的本義。“贅”字是個會意字,從敖、從貝。其中,“敖”字在小篆中從出、從放;“貝”當初是一種貨幣名稱,“貝”字后來在文字中就成為錢財的象征(漢字中大凡以“貝”字作為部首的字,一般都與財物、價值、貿易等經濟方面的事物或活動有關,如財、貨、販、貸、貿、貴、賤、購、賠、贖、賒、資、貧、貪,等等)。關于“贅”字的本義,東漢著名文字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中云:“贅,以物質錢,從敖貝。敖者猶放貝,當復取之也。”就是說,“贅”字的本義是“以貝(錢財)放出,然后再收回”,即“抵押”或“放貸”之意。在實際運用上,又側重于“抵押”這個意義。從“抵押”之意來說,“贅”字就相當于“質”和“典”,即以某物質錢、以某物典當等,如《金史·百官志》:“民間質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五、七分即五、七成)
當初,人們是以財物作為抵押的。但事物是發展的,抵押也是如此。“抵押”發展到后來,抵押品的范圍擴大了,把人納入了其中,也以人作為抵押品。人被作為抵押品,就叫“贅子”,相當于“人質”。比如《漢書-嚴助傳》中記載:“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相應地,“入贅”的意思就是為了借貸而做贅子、做人質。從某種意義上說,“贅子”類似于“質子”。只不過“贅子”存在于民間,是經濟活動的產物;而“質子”則存在于國家之間,是政治和外交活動的產物。上古時期,兩國交往,各派世子或宗室子弟留居對方作為保證,叫“質”或“質子”。如《左傳·隱公三年》:“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戰國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質于秦。”
在民間,人作為抵押品,與財物作為抵押品一樣,如果逾期不能被出押方(借貸者)贖回,也要被收押方(高利貸者)“據為己有”(沒收)。收押方就要將“贅子”作為奴婢使用。“贅子”就由抵押品變成奴婢,失去人身自由。三國時期經學家如淳說:“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贅子”的含義經歷過兩次變化。當“贅子”由起初的抵押品變成主家(收押方)的奴婢時,就改變了它最初的意義。這是“贅子”變化的第一階段。當“贅子”被主家看中,被主家“以女匹之”,成為主家的女婿時,其意義就進入了變化的第二階段,從經濟領域進入了婚姻領域。此時,“贅子”就搖身一變,變成了“贅婿”;“入贅”的內涵也逐漸與經濟脫鉤,而開始與婚姻產生聯系。不過,由“贅子”變成的“贅婿”,其社會地位極低,近于奴婢,是備受世俗歧視的。這種情況出現于秦代及其以前。所以清代著名學者錢大昕在《潛研堂文集·讀史問答》中說:“(秦時)贅子猶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贖者,去奴婢僅一間耳。秦人子壯出贅,謂其父子不相顧,惟利是嗜,捐棄骨肉,降為奴婢而不恥也。其贅而不贖,主家以女匹之,則謂之贅婿,故當時賤之。”
演進到后來,“入贅”就演變成了一種特殊的婚姻方式,即男子就婚于女家。此時,“贅婿”不再是由主家的奴婢轉變成的,而是先到女方家成婚、繼而留在岳家的“上門婿”。這樣,“入贅”一詞也變成了婚姻形態方面的專門“術語”,其含義也由當初的“作抵押”變成了“作上門女婿”。“入贅”的原因、目的和性質與先前迥乎不同。當然,“贅婿”當初多是因家貧而無聘財,才以身為質而“倒插門”的。正如《漢書·賈誼傳》所說:“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這種現象主要存在于秦漢時期,當時“贅婿”的社會地位仍然很低,為人輕視,甚至被列為七“科謫”(犯罪或遭貶者)之一。后來,隨著社會的發展,“贅婿”的社會地位也在不斷提高,其人格也逐漸受到尊重。
由上可知,“入贅”原本與婚姻并無關系,而與經濟活動緊密相關,其本義是指作抵押(甚至繼而作奴婢)。它后來之所以成為一種特殊的婚姻方式,就是由先前的這種無奈和屈辱之舉發展而來的。正因為如此,“入贅”之婚和“贅婿”在當初才普遍受到世俗的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