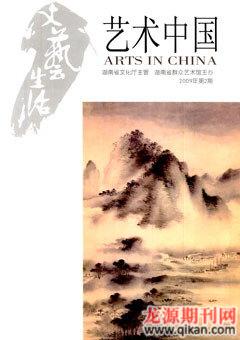白砥:慢動作的實驗
沈必晟
白砥的書法創作,并不是我欣賞的類型。我當然沒有絲毫貶低他的意思,而是出于個人的偏好,很奇怪的認為。他的那種走走停停、欲言又止、初看上去憨憨笨笨、細究又有巧思的創作,在我而言,更像設計、剪紙。都是刻意安排下的產物,如果說和書法能扯上關系,可能是緣于他的工具還是傳統的毛筆宣紙吧。
書法的最終定義一直在爭論不休當中,這是個很復雜的問題,我當然解釋不清。但要而言之,有關書法的概念至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漢字及其字象,一是一次性書寫。前一個不涉主題暫且不談,后一個則不得不有所發明。書法作為有別于其他門類的藝術、技術,還是其他的什么也好,它在工具上的獨特性,劃定了它的界限。古人說:“惟筆軟則奇怪生焉”,說明工具在書寫過程中的作用,也事涉書之“藝”或“道”。尤其是其不可重復、不可增刪、不可渲染的書寫性,加重了書法一次性完成的特質。懷素和尚的“忽然絕叫三兩聲,滿壁縱橫千萬言”,張旭的“揮毫落紙如云煙”。米襄陽的“八面出風”、“風墻陣馬”等等,都可以被古今文人戲劇化的記敘傳唱,正說明了這種一次性書寫時的瘋巔狀態是被歷代中國人擊節稱賞、吟詠再三的。而歷史上,也從來無爭議地將草書作為書法的最高境界。從“技”的方面理解,書法之難就在于在疾速行筆的過程中,一次性再現萬千氣象。也就是說,既要快筆直書,又要在這個轉瞬即逝的過程中照顧字形、墨法、章法、行氣等等諸因素,照此理論,行筆愈快,技術難度自然愈高。草書作為書法中的最高境界,單從技術動作上考慮,自然是行書、楷書等其他書體不可同日而語的。這似乎就表明了,書法的書寫性特征的凸現,是最令人回味、最叫人癡迷、最使人瘋狂,也是現實狀態中最難以捕捉的地方。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將“書寫性”評為傳統經典書法中最為核心的模式,或者說,是傳統書法中最具智慧匠心的地方。
我知道白先生在書寫時的速度是不太快的,和其他書家相比較,他的原作在墨色上的變化與追求,也并不是太強烈。他的慢,應該是在將心力放在字形的變化與筆力的伸張上。
字形的變化是需要的,它是衍生風格的載體。在實際的書法創作中,這種字形的產生,或者說該種成熟風格的凸現,不談形而上的審美情趣。純粹從操作層面去做考究,實際上是后天習練與自身書寫的生理特點相結合所致。古人在這個問題上說“心手相應”,我揣想,
“心”應該是指思想的參與,想法和手上的功夫互為表里,互為補充,或者說手能精確表達思想,那當然是愜意的事情,但落實到純操作的層面,要將“思”能起于無形,在“能”字上做足功夫,以書之于有形,書寫的生理特點和極限就是亟需注意和加以重視的地方。這種書寫的生理特點和極限,就是以漢字及其字象為界限,它也是傳統書法與現代派書法爭論的焦點。即便如此,以白先生的書法創作還是以漢字及其字象為限論,至少是不太激進的。從這個角度理論之,張瑞圖的特點就是運筆的左右擺動,懷素是從左上角到右下角的逆時針劃圈。褚遂良的典型運筆是“s”型筆畫,黃庭堅則是大劃“八”字,左右搖蕩。應該說,對書寫的生理特點和極限的掌控也是促成書家肯定其書寫方式,加快其書寫行為的重要因素。
在這一點上,白砥的創作確實是在強化一些特征。放慢了書寫的速度,筆力自然會渾厚些,但同時也會使通篇字感覺木訥笨拙,特別是在空間分割上尤會顯得了無生趣。白先生會加上一些慢動作狀態下的草書形態,這些草書形態的單字可以幫助打破呆滯的單字外廓空間,整幅書作更顯靈動;草書形態以外的單字,也做了手術,要么上下錯位,要么左右拉扯,還有在擠壓狀態下顯“高”、“矮”、“胖”、“瘦”的單字,都會隨著作品的具體樣式做相應的調整,并在此基礎上輔以碑味濃烈的方筆,整合全部作品。
毫無疑問,白先生的書法作品,在單字外廓上的變化是顯得最為劇烈的,單字與單字之間重合的面也是最小的,這是他書法的一大特征。有人因此斷定他的線條之間,因照顧外廓的變化,少牽絲。多含蓄,甚至于上升到哲學的角度,說他“含而不露”,玩足了武當的內家功夫。這種評價,我沒法置評。我只是舉一個最為大眾熟悉的現象,實際上也是幾年前我在小文《關于書法的空間情調》中論及的地方:行草書大多都有牽絲的現象,但楷書沒有。規范的唐楷,是極盡規范動作之能事。尤其是顏楷,必欲有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欲上先下、欲下先上之動作,單獨看這些動作,撇當然是欲左先右,橫當然是欲右先左,豎當然是欲下先上,挑也當然是欲上先下,沒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但書法是在規定的時間里,做連綿不斷之動作,試將上述的書寫規范作連續的考究,就會恍然大悟。舉“三”字作例,第一橫的欲右先左,在筆畫收尾的時候又隱含一個回轉的動作,而下一個橫畫起始又是欲右先左,單獨看這兩橫,可能機械而無聯系。但作連續不絕方面看,這兩個動作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可以這樣理解,如果顏楷將這個動作分解形成了萬世必遵崇的法度,在具體的筆畫中刻意加以體現,那么行草書實際上就是在空中完成了這個動作軌跡。如果這個大膽的猜想成立的話,那么就完全可以拿去解釋牽絲一類的現象。也就是說,牽絲是在空中動作及紙時留下的痕跡,楷書的這類動作,實際上是行草書牽絲類動作規范后的遺存。這頗有點類似猴子與人的關系,猴子有尾巴,人從猴子變來,雖然尾巴蕩然不存,但仍有尾骨的遺留。
白先生慢動作狀態下的書法單字之間,確實是少牽絲的。但既要保證線條的質感,又要持續作稍有行氣的表達,剛才對顏楷的剖析,放在白先生身上,似乎也顯得貼切自然,并沒有什么不妥。只是那種因慢而生的所謂的“含蓄”,或形而上得利害的什么“含而不露”等等,我都覺得實在是有貼錯標簽的嫌疑,大有“你不說我還有點明白,你越說我卻糊涂”的意味在。
書法家在書寫過程中的揮寫、揮運之樂。看來是沒有辦法在白先生的創作過程中去得到痛快淋漓的體現了。當然,白先生會說他自個兒覺得有味道、過癮,“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這是他的體會閥值。你的閥值高,那是你的事。
白先生的辦法,一句話,就是將傳統書法資源作純視覺上的造型,謀求在視覺形態上的新變。這或多或少暗合了當代書法孜孜以求完全形式上突破的思潮。平心而論,這個探索不是沒有意義的行為。以書法作形式上的實驗,是當今書壇在西方抽象畫發展影響下所做出的反應。而西方抽象畫,實際上在上個世紀里,是有得于更多東方書法的地方,你可以去看看馬蒂斯、畢加索等大師的徒手畫,這個結論基本上是不證自明的。畢加索與張大千在晤面時,更直率地表達,他假如在中國,肯定是一位書法家。我想,畢加索對中國書法的認真,一定是囿于書法在一次性書寫揮運中所顯示出來的無窮魅力和哲學意味。這都說明書法在西方抽象派大師心中的地位。世紀末的反方向影響,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學術上的互相交流與對話,但把突破傳統書法、并繼續創造有中國氣派的書法的焦點放在這個形式至上的地方,實在是令人擔憂,愿智者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