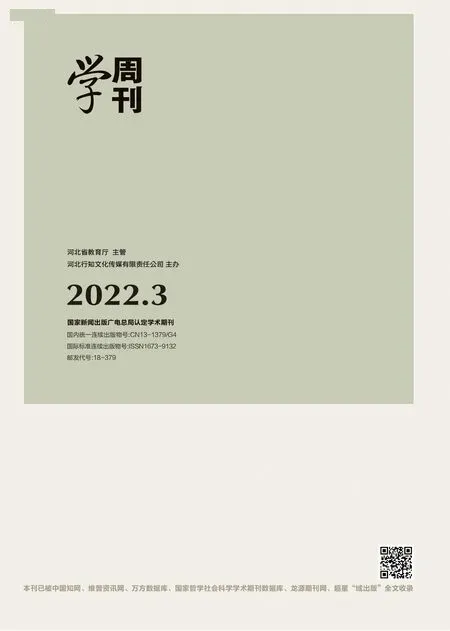激活源頭水,下筆方有神
廖立新
從專家學者到普通中學教師,從高考閱卷場到中學語文課堂,越來越多的人士在感嘆高考考場作文的程式化、空心化、趨同化。
事實正是如此:隨著高考關注的高度社會化、招生競爭的日漸白熱化、復習備考的極端功利化,考生考場作文正在并將繼續丟失個性和靈魂,極富創意和靈性的寫作活動也正在并將繼續蛻變為對所謂滿分、高分作文千篇一律地簡單克隆和拷貝,一場社會成本最為高昂的選拔性考試正在并將繼續發揮其巨大的模板復制功能為我們生產著一大批缺乏思想感情、毫無主見和創意、甘愿放棄話語權的“優等生”。
我們無權也不必徒勞地埋怨、指責師生的短視、社會的刻薄、學界的呆板僵化、家長和教育行政部門的勢利、書商和出版部門的惟利是圖,只要體制上的根源不消除,這種局面和趨勢就很難改變。
然而,作為教育和教學活動的直接責任人和具體實施者,廣大中學語文教師卻不能不本著對國家民族負責、對考生家長負責、對自己良心負責的精神,抵制誘惑,抗拒壓制,無私無畏的姿態,捍衛思想者的尊嚴,捍衛寫作者的話語權,還寫作以本色。
既然我們都承認文學是人學,都承認生活和心靈是寫作的源泉,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從源頭人手去激發學生的寫作熱情和表達欲望?
一、撐一支長篙漫溯
歷史是逝去的今天,今天是未來的歷史,那么未來呢,會是過去和現在的復制嗎?滾滾奔流的江水喚醒了孔子的時間意識和歷史滄桑感,于是由衷喟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于是就有了“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緊迫感和使命感。皎皎明月,亙古如新,江山依舊,人事已非。“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的感嘆與感悟又何嘗不是千萬文人墨客的感嘆與感悟?“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在歷史的長河里,茫茫的宇宙間,個體的生命固然渺小,固然短暫,可是你懷疑過人類血脈的綿延不絕么?你懷疑過人類對真理的永恒追求,對未知世界的不懈探索么?
且不說這些宏闊的宇宙意識、歷史意識,即便是在極微觀的現象與事實的層面,就有多少值得我們人類去觀察、感受、思考、質疑、推究的東西啊!許學生一支長篙吧,這長篙就叫做探索精神。憑這支長篙,撐起一葉智慧之舟,向著宇宙的更深處,向著歷史的更深處漫溯。那就劃過改革開放的二十年,耳邊唱響《春天的故事》;那就劃過瘋狂、荒謬的十年文革,去傾聽一位老人真誠的懺悔;那就劃過硝煙,劃過烽火,劃過漫漫征程,劃過百年屈辱,劃過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奮斗追求,“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那就劃過鄭和的船隊,劃過鑒真的風帆,劃過玄奘的行囊,劃過茶馬古道,劃過絲綢之路,去探尋不同民族、不同國家文化與經濟的共存共榮之道……
二、第三只眼看世界
社會生活為我們提供了太多的寫作素材,我始終不明白:為什么高考命題專家總是擺脫不了“回避熱點、焦點”的魔咒?為什么中學語文教師離開了教輔資料、備考書就不知道給學生出什么作文題?為什么廣大考生總是不厭其煩把有限的幾個古人折騰了一回又一回?是誰蒙蔽了智者的雙眼?是誰奪走了思想者的長劍?
“超女”火爆,看到了拇指經濟的瘋狂和草根民主的頑強;湯圓滯銷,看到了傳統文化的危機和家庭情感的疏落;城管副隊長被殺,看到了城管工作思路的癥結和城市功能文化定位的狹隘;23歲的年輕生命終結于23元,看到了正義本能缺失的可悲與可怕。
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學生說:我思想,我才能成長。
三、我的生活我做主
三點一線,是有些單調,有些乏味;書山題海,是有些枯燥,有些沉悶。但是,年輕的生命注定是禁錮不住的,驛動的心靈終究是要放飛的。你可留意過同桌之間的竊竊私語?你可定格過走廊上的凝神遠眺?你可關注過茵茵草地上漫步的身影?你可領略過運動場上的吶喊聲威?更何況,他們也有父母兄弟,也有生別死離!生活饋贈我們些什么,也照樣會饋贈些他們什么。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朱熹說得好,豐富的生活體驗、廣泛的社會實踐是創作的不竭源泉。如果學生還是被生活的洪流裹挾著前行的不自覺者,教師有責任教他們成為自己生活的主宰者;假如學生親歷了生活卻缺少體驗和感悟,教師更有責任去培育他們心靈的觸角。寫自己,寫生活,永遠是作文訓練的法寶。
四、心靈需要一面鏡子
外宇宙廣袤無垠,內宇宙同樣廣闊無邊。法國大作家雨果說過:世界上最寬廣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廣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廣闊的是人的心靈。也有人說:心是花園,思想為種,既可繁花似錦,又能雜草叢生。可是,我們很多時候偏偏忽略了這個最廣闊、最豐富的世界,忘記了給這花園撒播下美好的思想的種子。以至于心靈的天空日漸萎縮,心靈的花園日漸荒蕪,心靈的世界日漸晦暗。
作為語文教師,當務之急是給學生的心靈一面鏡子。有了這面鏡子,他們才照得見自己的心靈,才懂得內窺自省,才懂得自我觀照,才恍然驚覺原來自己的感情是如此豐富細膩,自己的心理是如此斑斕多姿。這面鏡子或許就是一種心靈的敏感性和感受力,或者是一種“第三者”意識,無論怎樣理解,共同點是都需要訓練和修為。那么,從寫作指導開始,命題盡量直接抵近學生的心靈,把聯想和想象引向心靈的深處,技法上著力于虛實結合和虛實轉換,間或引入意識流手法,甚至于以魔幻現實主義的挪移嫁接功夫實現時空的超秩序組合與建構。
回到人本身,回到生活本身,為著滿足人的發展的需要,這才是新課程的宗旨和要義。寫作教學和高考作文考查也必須回歸正道,而不是漸行漸遠,更不能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