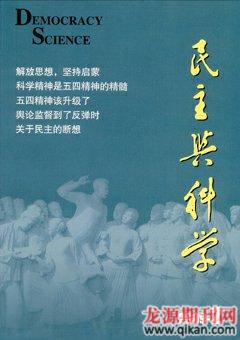五四精神該升級了
李 俠
今年恰逢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90周年,筆者前些年每當到這個時節總要寫一點文字以示紀念。于今這種書寫的感覺越發艱難了,說到“五四”,我們能否說點具有新意的東西呢?這是一個很令人尷尬的問題。坦率地說,我至今都很佩服“五四”時期的那些先賢大哲們。在民智未開的年月里,他們用先知般的預言為我們開啟了一個時代的序幕,并以遠見卓識的思想為我們的這個長期積貧積弱的國家開出了一劑震古爍今的處方——科學與民主,由此也確定了中國在現代史上的基本走向。
如果說五四運動為我們開出的藥方是一種二元結構,即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希望由此實現我們國家的富強與進步,那么,從歷時性角度來說,在那個時代,這個二元結構相對于當時的中國文化環境來說是相當超前的,因為當時我們基本上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也只有少量現代意義上的科學,這也更突現出“五四”先哲們的深邃的歷史眼光,今天來看這份答卷可以給及格的分數。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五四運動,我們今天的生活會是什么樣子?那么90年后的今天,這個處方對于當下的中國是否還適用?這是一個嚴肅的、也是迫切需要反思的問題。我們今天的社會環境與“五四”時代發生了天壤之別,因此,如果仍然采用90年前的藥方,對于當下的中國來說,我們的思想根本沒有多少實質性的進步,而且這劑藥方對于已經發生變異的中國語境來說,藥效已經遠不如當初那么有效了,為此,筆者去年曾嘗試提出“新五四”精神的處方應該是三元結構,而不是二元結構。困難的問題是,這個藥方的第三個元素應該是什么?2008年筆者曾給出的第三個元素是伊先生(創新),如今想來,有些不妥,畢竟創新是一個復合元素,而不是單純的原子元素,換言之,創新不是最基本的元素,它是可以分解為其他元素的。而“五四”提出的兩個元素基本上都是原子元素,筆者認為,“新五四”精神的三元結構應該是科學、民主與真理。這三元結構分別對應著如下事實:科學對應著外部世界,民主對應著人類社會的秩序,而真理則指涉在世界中存在的個體的內在信仰。依筆者管見,“五四”的處方之所以在90年的歷史發展中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關鍵在于它缺少了對在世存在的人的信仰的關注,它只關注了外部世界和社會的秩序。對于外部世界我們已經基本取得了預期的成功,而對于社會秩序,坦率地說,我們并沒有成功,直到今天,我們仍是如履薄冰般地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從這個判語中,可以推斷出,我們對民主還很陌生,因此也就談不上民主在90年中取得多少實質性的進展。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在老“五四”處方里缺少了一個必要的維度,即作為社會構成部分的個體的心理意向的規定,在中國悠久的實用主義文化背景中,我們缺少一種宗教的氛圍,因此替代宗教作為永恒追求之物的只能是真理。正是因為構成社會的眾多個體缺少把真理作為永恒之理念,所以,民主的進程也就無法推進。這就是“五四”啟蒙運動不徹底的地方,不過我們不能以此苛求我們的先哲,畢竟,他們已經天才般地為我們指明了前進的路線圖,我們應該也要有所作為。為了印證筆者關于“五四”精神的三元結構,下面分別談談科學與民主在當下遭遇的困境,就可以更好地說明改變“五四”二元精神結構在當下的重要意義了。
精英陰影下的民主悖論
科學界是一個嚴格按照社會學分層理論運行的社會亞群體,群體分布的形狀類似于金字塔形,位于科學共同體頂層的就是科學界的精英,中間層則是眾多的各類專業人員,底層的則是科學共同體的各類初級人員。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說法,分層有利于共同體的秩序與效率,前提條件是這個分層是可以正常流動的。而民主按照最通俗的說法就是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權利,它包括羅爾斯意義上的作為公平的正義原則,其指涉了兩個條件,即公平原則與差異原則,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而科學領域的特點在于,只有少數人具有杰出的才智,因此他就具有更大的發言權和決定權。在科學界是不考慮差異原則的,由于科學場域的這個特點,民主的前提條件在這里失效了(僅考慮作為公平的正義原則)。科學界盛行的規則是“贏者通吃”,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馬太效應”的根源所在。如果一個社會經歷過一個比較完善的市民社會階段,那么,科學作為一種建制,它與政治、經濟處于相對獨立與疏遠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科學場域按照自身的規律單純發展,即便有馬太效應現象存在,只要上下層之間存在健康的對流關系,那么科學作為單純處理自然界事物的一個獨立建制仍然可以有效地促進社會的整體發展。這種對流關系是科學場域內的一種特殊民主形式,而市民社會的存在提供了自律作為一種維持秩序的常規力量是可以發揮一定作用的。如果沒有經過這個階段,就無法形成有效的民主的秩序機制,導致自律作用形同虛設。這里的根源在于如果一個社會沒有經歷過成熟的市民社會發展階段,科學場域內的活動與政治、經濟的聯系必然緊密,那么科學作為應對外在世界的工具就完全有可能處于一種被操縱的異化狀態,最后形成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所謂的各種社會資本的交易與兌換(主要是政治資本、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按照一定比率的兌換),這就是他所謂的社會煉金術。現在中國的現狀就是科學場域與政治、經濟等場域沒有明顯的邊界距離,甚至可以說科學場域完全依附于其他力量場域,導致科學場域內民主的實質缺席。按照美國社會學家C·米爾斯的觀點:現代社會的頂層日益一體化,并常常進行著看似隨意的合作。中間階級是一種漂浮不定的僵持、平衡的力量,中間層并沒有將底層與頂層聯系起來。社會的底層在政治上一盤散沙,甚至作為一種消極的現實,越來越沒有權力。這種狀況科教界內的人士不會感到陌生。科學精英日益蛻化為科學的符號,從而具有了知識即權力的可以隨意轉換的秘密武器,在政治資本、經濟資本之間進行著公開的利益兌換。目前科學界充斥的各類精英代言人的角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科學共同體中的中下層感到普遍的無望甚至絕望,從而產生整體的結構感的喪失。坦率地說,公眾對于當下中國科學界認同感的日漸喪失的根源就在這里。對于整個社會來講最大的危害在于,自“五四”以來被奉為啟蒙寶典的二元精神結構被消解了,這就是本文提出的老“五四”精神結構與當下社會情境出現了結構性不匹配現象。
真理:捍衛民主與科學的最后一個支點
90年前,我們還處于前工業化時代,那個年代也正是科學與民主浪潮在全球快速興起的時代,整個社會的發展被構想為一種線性進步圖景,二元結構完全滿足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五四”的先哲們把這樣一些先進理念引進落后與封閉的中國,即便對二者之間的關系并沒有完全搞清楚,也是可以理解的,這個方案在今天看來也是非常有歷史遠見的。而90年后,我們快速地越過了工業化時代,正在邁向后工業化時代,整個社會的發展日益呈現為一種非線性發展模式,那么老“五四”的二元理念結構顯然已經無法適應當下時代的腳步。時代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人的觀念的變化上,世界還是那個世界,社會還是那個社會,因此,科學與民主針對的基本對象沒有變化,因此,二者仍是需要保留的要素,問題是此時的社會構成的內涵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主要是由于構成社會的個體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就需要一個新因素來應對變化了的個體觀念,否則民主與科學觀念將無法逃避被異化的命運,從而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而這個元素就是真理。關于民主的異化這里暫且不談,而科學的異化可以表現為很多形式,僅從認識論角度來看,就存在江曉原教授指出的科學的三大誤導:首先,科學等于正確;其次,科學技術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第三,科學是至高無上的知識體系(《文匯報》,2009-2-26)這個總結性的概括非常全面,前些年盛行的科學主義思潮就是這種異化的最好體現。之所以會出現這些誤導,是因為在民主失去了應有的制約作用后,科學精英們在失控的市場經濟面前,憑借對科學的修辭策略的獨家壟斷,毫無遮攔地開始淪落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導向。由此,我們看到了科學開始日益演變為資源與權力的奴仆,科學界的失范現象大多與此有關。早在2000多年前,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就曾說過:贏得榮譽就應盡到自己的責任。可惜,今天還有多少科學精英還記得這句箴言呢?這也就是科學哲學家杰里·拉維茨所謂的“后常規科學”時代(Post-Normal Science),這個階段的最大特點就是“事實是不確定的,價值在爭議中,賭注是巨大的,決策是緊迫的。”(蔡汀·沙達,《庫恩與科學戰》,2005),面對如此復雜的局面,科學日益分化為四類:以次充好的科學、企業化的科學、魯莽的科學和骯臟的科學。這些情況的一些端倪我們多少都有些經歷,并且其中有些品質還有快速增長的趨勢。如何應對這種復雜的局面?除了繼續完善民主之外,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全社會推進把真理作為個體追求的一種永恒理念。我們之所以關注真理,是因為真理的本質與人的自由有關。個體為了捍衛自己的自由就需要有一種民主的制度安排,否則自由是無法實現的,基于自身的自由考慮,他會真正自發地追求民主。同理,為了自身的自由他需要物質保證,而科學則是提供物質保證的最好的工具。因此,只有當個體把真理作為自己的信念時,才能主動地推進科學與民主的發展。同時,只有真理才能從根源處捍衛民主,否則民主永遠是沒有根基的,另外,真理,再次把科學拉向求真的軌道,使之擺脫被任意擺布的地位。也許最為重要的是,真理作為一種烏托邦,在喚起美與善的同時,并為我們當下的艱難前行提供了一種超越的可能性以及面對困難的勇氣。
基于以上考慮,老“五四”的二元結構之所以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是因為那時預設的信念基礎是實用主義的,而實用主義不需要永恒信念的支撐,沒有信念支撐的“五四”精神是無法保證必然通達目的的,因此,“五四”精神應該升級了!
(作者單位:中南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