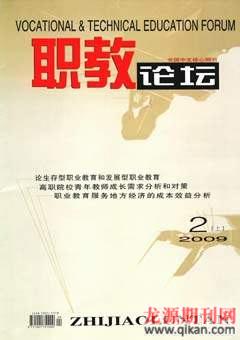從“金融危機”看職業教育的“以就業為導向”
莊西真
大洋彼岸的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影響不斷深化,其影響已經從局部發展到全球,從發達國家傳導到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從金融領域擴展到實體經濟,其涉及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沖擊強度之大超出預料。
中國自然也不能幸免,畢竟出口在我國經濟中已經占了很大比重,“萬惡”的資本主義突然不需要我們的產品了,好不容易博得了個世界制造中心的我們難免迷茫、失意和彷徨。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媒體上不斷傳出企業經營困難,中小企業停產或半停產、甚至破產倒閉的壞消息,一些大企業也出現較大虧損,由此導致大量失業,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增速下降,就業進入“嚴冬”季節。農民工提前返鄉增多,農業部根據固定觀察點最近對10個省市的數據調查,得出農民工提前回流量占農民工總量的6.5%。因此,如果以6%的回流量估計,全國1.3億外出農民工中已有780萬人提前返鄉。(《21世紀經濟報道》2008,12,18)
受到沖擊的不僅是農民工,大學生的就業也面臨寒潮,2008年中國高校畢業生為559萬人,為歷年之最。2001年以來,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維持在70%左右,如果以這個比例計算,意味著2008年還有約168萬大學生沒有就業,實際上大學生的就業率達不到70%。今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將達到610萬人,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大學生們的就業形勢將更加嚴峻,很多學校和專家建議大學生放下身段、降低要求,將薪酬一降再降以求就業。
其實,即使沒有經濟危機,中國的就業形勢也不容樂觀,只是經濟危機更加讓不樂觀的就業形勢“雪上加霜”罷了。中國經濟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帶來了眾多的工作崗位,2002至2006年,我國每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在900萬人左右,2007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上升到最高的1200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也保持在4%-4.3%,應該說過去幾年的就業形勢還是比較不錯的。但是和中國經濟10%的增長率相比,我國的就業增速遠遠落后于GDP增長,一旦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就業的問題就立刻浮出水面。我國如果要保證每年1000多萬人的新增就業,GDP應該至少保持在8%以上(這也就是決策層和有關專家說的保八的原因)。但是經濟增長了未必就意味著就業也增長了,經濟學上的奧肯法則說,一個國家的失業率與經濟增長率成反比,這個法則不適合中國,從就業彈性(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帶動就業呈現一定比例的正向增長)來看,從1980至1990年,我國的GDP保持9.5%的增長,就業人口年增長率為4.3%,就業彈性為0.453。從1991至2000年,我國GDP保持10%的增長,就業彈性下降至0.11,而從2001年至今,就業彈性下降到不足0.1。
以上不憚瑣屑敘說金融危機導致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和重化工業等資源密集型工業畸形發展,進而影響就業減少的情況,無非就是說“就業難”。按說美國金融危機與中國職業教育之間沒有直接關系,但是金融危機影響我國的實體經濟,甚至影響就業,那就與我國職業教育發生了關系,而且關系還很緊密,因為中國的職業教育一直提倡“以就業為導向”。根據有關方面對職業教育的定位(中等職業教育是在九年義務教育的基礎上培養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高等職業教育是在高中階段的基礎上培養數以千萬計的高技能專門人才);也根據歷年來對職業教育畢業生就業情況的調查,職業教育與實體經濟密切相關,這種相關主要表現在職業教育的學生就業集中在機械制造、紡織服裝、模具玩具、電子電器、家具、通信設備等實體經濟行業(這些行業也是大多數農民工就業的行業)。現在這些行業不同程度的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普遍壓縮生產、裁減員工、艱苦支撐,職業教育自然受到影響,多年來我們一直引以自豪的中等職業學校百分之九十幾的就業率(2005年95.35%,2006年95.6%,2007年96.10%。暫且不管這個就業率的真偽)看來遇到麻煩了。我們說“以就業為導向”,前提是有業,也就是說就業機會在那里等著,然后職業教育采取相應措施,使人們很快抓住機會。現在是無業可就,根本沒有就業機會,沒有職業“以就業為導向”就失去了坐標和方向。有人可能會說,無業可以創業,創業需要資金、市場、制度環境等條件,這么多大學生(還有博士、碩士)都不能創業,對于職業學校的學生來說談何容易。看來我們要認真反思我們關于職業教育的一些觀念、做法,如果金融危機能夠促使我們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又符合職業教育內在規律的發展職業教育的路徑,那可真是“壞事變好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