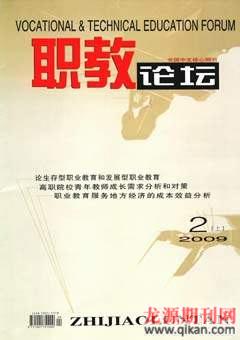德國女性的就業與職業培訓
陳 瑩
摘要:女性是一支不可忽略的勞動力資源。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德國女性從事職業工作的比率持續上升。女性就業狀況是否合理,直接影響到經濟的發展。文章對德國女性就業現狀、影響就業因素以及促進就業措施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德國女性就業;現狀;影響因素;措施
作者簡介:陳瑩(1979-),女,浙江桐鄉人,上海師范大學機電學院講師,主要研究德國職業教育。
中圖分類號:G71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7518(2009)04-0056-03
一、引言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德國女性從事職業工作的比率持續上升。傳統的家庭模式,即男性負責工作賺錢,女性負責照顧家庭,也就是所謂的“一人養一家”的模式,逐漸遭到消解。隨著女性參與工作賺錢,男性也更多參與照顧家庭。傳統的性別角色界限逐漸變得模糊起來。
那么,促使越來越多的女性踏上職場的動力何在?
首先,女性就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其伴隨而來的經濟收入。勞動力市場的惡化使得男性難以獨立支撐養家的重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勞動力市場不穩定,失業率居高不下。“一人養一家”的傳統模式需要承擔極大的風險和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女性踏上職場,可以緩解由丈夫一人養家所隱含的失業風險。
其次,德國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過低的出生率導致社會老齡化現象嚴重。老齡化帶來一個直接的后果,即勞動力不足。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經濟無法舍棄女性這支龐大的勞動力大軍。
再次,社會價值取向多元化,女性價值觀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的女性期望在職場上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或者說,盡管女性家庭觀念依舊濃厚,希望在家庭之外能夠擁有一份職業的女性不在少數。
最后,女性就業也有客觀條件作為保障。隨著社會結構的轉型,隨著服務業的興起,女性就業有了更廣闊的天地。另外,隨著兩性平等運動的深入,女性有了和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權。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成為女性就業的重要促進因素。
二、德國女性就業現狀
(一)兩性傳統社會分工
在2006年進行的一個調查顯示,對于男性在外工作、女性在家照顧孩子的模式,新聯邦州18歲以上的人口中,有20%持贊成的態度,在老聯邦州更是高達53%。另外,老聯邦州有60%的人認為工作和家庭是無法兼顧的,女性如果參加工作,家庭生活勢必受到影響,新聯邦州持這一觀點的有25%。[1]
這一“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的社會分工觀念,不僅阻礙了女性踏上職場,也直接造成了女性就業面的狹窄。這在教育領域已有明顯的體現。
在高等教育領域,女性所學的專業主要集中在語言、文化、社會學等專業。而男性則集中在技術和工程專業。[2]在職業教育領域,超過60%的女性集中在28%的職業中。[3]
(二)女性就業質量較低
首先,很多職業女性從事的是“簡單工作”。 所謂的簡單工作,主要指的是職業資質有待提高的工作。在德國,簡單工作的比例有23.2%。從事簡單工作的就業人口中,女性比例高達80%。以女性為主的簡單工作領域包括零售業、旅館清潔、孩子和老人護理等。[4]這些工作社會承認度低,工資較低,且升遷前景黯淡。它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德國31%的職業女性,其工資水平處于低工資水平線之下(低工資指的是工資收入低于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二);而收入位于低工資水平線以下的職業男性只占10%。[5]
其次,德國大部分女性從事的是部分時間工作。只有少部分女性從事全天候的工作。在占據女性總數59.6%的職業女性中,有44.3%從事部分時間工作。[6]根據世界經合組織OECD的統計,德國從事部分時間工作的女性,和荷蘭、英國一道,遠遠高于歐洲其它國家平均水平。[7]部分時間工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女性就業,然而部分時間工作往往缺乏職業升遷前景,阻礙了女性在事業上的進一步發展。
再次,即使在全天候工作中,也就是女性較高收入群體中,女性收入也只占男性收入的78%。工資待遇方面,兩性差距較大。[8]
三、決定女性就業的因素
(一)女性教育程度
在德國,職業女性教育程度呈現兩極分化的特點。教育程度越高,女性越容易踏上職場。反之,教育程度越低,女性越容易扮演家庭婦女的角色。[9]
兩性平等運動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部爭取兩性受教育權利的歷史。兩性平等運動的核心就是爭取兩性受教育權利的平等。換言之,教育程度是決定女性參與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決定性因素。
就教育而言,在德國,相對于學位文憑,職業能力更主要靠職業教育獲得。也就是說,擁有較高的職業資質,便意味著擁有良好的就業前景。同時,職業資質較差的勞動力,不得不面臨日益惡化的就業環境。最近二十年就業情況證實了這一點。[10]
一方面,德國女性受到的教育水平較高。在30歲以下的人群中,獲得專科高等學校文憑和高等學校文憑的,女性占據大部分。也就是說,30歲以下的人群中,女性所受的教育水平高于男性。[11]這也是越來越多的德國女性踏上職場的重要促進因素。
另一方面,按照聯邦統計局的2006年的統計數據,在參加職業培訓的學員中,女性比例只有40%。[12]這直接影響了女性就業的數量和質量。
(二)社會家庭政策
女性的事業成功與否牽扯到諸多的因素,包括社會因素和家庭因素等。
在10歲至25歲的群體中,女性花在學習上的時間要比男性多;而在25歲至30歲這一階段,情況正好相反,因為這一階段,正是成立家庭的時期和撫育幼小孩子的時期,女性需要為家庭作出極大的犧牲。[13]家庭成了影響女性事業成功的一大障礙。
在德國,育兒時間的長短和育兒津貼的額度對于女性就業影響較大。自從1986年規定發放育兒津貼以來,關于津貼發放的規定有過多次更改。到2007年,規定育兒期限的上限為3年,育兒津貼發放期限為2年。如果家庭年收入在3萬歐元以下,育兒津貼發放額度為家庭工資凈收入的67%。[14]育兒津貼福利制度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女性就業的積極性。
德國三歲以下的孩子,很少有育兒機構代為看管。在2005年和2006年,在老聯邦州僅有少于10%的孩子得到育兒機構的照顧。[15]這一比例相對于國際上的情況而言,是相當低的。直到小孩滿三歲后,才可獲得育兒機構半天的看管。這一現實情況直接限制了年輕母親在生育后重返職場。
德國的稅收政策規定,稅收標準可以按照夫妻收入較低的一方來執行。這樣,為了減輕納稅負擔,丈夫收入較高的家庭,妻子極有可能放棄工作。[16]
對于擁有較低職業資質的女性來說,還能享受失業救濟和其它社會救濟。尤其是2005年開始實施的《失業救濟法II》,更加強了這方面的保障。
總之,女性就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會家庭經濟政策的影響較大。德國完善的福利制度,挫傷了女性踏上職場的積極性。德國育兒機構等社會設施的普遍缺乏,在客觀上阻礙了女性參與職業工作。
四、提高女性就業率和就業質量的措施
(一)提高女性職業能力
1.作為女性主要活動領域的家庭生活,是培養女性職業能力的重要途徑。
2000年9月6日歐盟在布魯塞爾舉行的主題研討會討論了培養職業資質的重要途徑:家庭生活。這次大會討論基于這樣的共識: 通過非正式學習途徑所獲得的能力也應當獲得承認。所謂正規的學習領域有: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教育、職業教育、繼續教育等;非正規的學習領域有:家庭生活、朋友交際、黨派生活、社團活動、工作過程、興趣愛好領域等。[17]
在德國,人們一般把能力分成四種類型:人格能力、社會能力、方法能力和專業能力。前三種能力俗稱“軟能力”,又叫關鍵能力。除了專業能力以外,這三種能力都可以通過非正規途徑獲得。家庭生活作為人最主要的生活內容,理所當然成為獲得能力的最重要的非正規途徑。
大會建議在招聘和晉升的時候考慮到這些通過非正規途徑獲得的能力資質,并且對于這些能力資質的考核和評估作了研究。其中包括31個能力項,參考5個等級標準,通過自我評估的方式或者他人評估的方式作出評判。31個能力項涉及到的主要方面有:樹立生活目標、具有貫徹力、在困境中作出正確判斷、勇于承擔后果、合理安排時間、保持良好的健康狀況、能與他人共同生活等。
這種能力測試方法獲得了參與者的好評。在這個能力測試的模式中,家庭和職業的關系由消極對立轉向合作互補。這種能力測試方式,有助于女性發揮自己的才能,在職場上走得更遠。
2.學習軟件的使用,是培養女性職業能力的有效手段。
相對于傳統培訓方式而言,電腦支持下的人機對話環境為學習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培訓途徑。在人機對話的學習環境中,學習者可以靈活地安排培訓時間和地點。一般來說,學習組織方式分成兩種。一種是學習者自愿進行的,學習時間安排在工作時間之外;另一種是企業安排的,一部分培訓內容安排在工作時間之內。無論是哪一種學習組織方式,都為學習者提供了傳統培訓方式無法給予的便利。
學習軟件分為兩種。一種是專門針對企業開發的軟件,開發成本較高,一般來說只有大公司能夠負擔得起。另一種是投放市場上的針對面較廣的學習軟件,學習者需要判斷哪些適用于自己所在的企業以及自己的工作崗位。選擇合適的學習軟件,能有效地促進女性職業能力的提高。
對于職業能力較弱的女性而言,很難滿足由于企業結構的變化引起的職業能力新要求。女性通過學習軟件的學習,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彌補職業能力的缺陷,從而參與并融入到企業網絡化的組織結構中,適應企業組織結構扁平化管理模式的改變。
因此,女性職業教育和培訓應當積極利用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優勢。女性應當充分利用學習軟件進行學習,習得和擴展專業能力。這一點,在企業繼續教育領域中尤為重要。
(二)轉變社會觀念
首先要轉變社會觀念,拓寬女性就業范圍。
實踐證明,舉辦“女孩未來日”等社會活動能獲得良好的效果。
在女孩未來日這一天,女孩子們可以深入各個技術企業和部門以及高校和研究中心等,她們可以去辦公室、實驗室、車間、編輯室等,通過親眼觀察實際的場景,通過和專業人士對話,來獲得對于職業的初步印象。在這個過程中,她們也可以建立和企業的聯系,這對她們未來的發展顯然是不無裨益。另外,通過這一活動,公眾和經濟界的目光開始聚焦于年輕一代的女性,并挖掘這一人力資源的寶藏。事實證明,參與這一活動的企業,在招聘的趨勢中,女性的比例有明顯的提高。這一活動受到多方支持,影響深遠。
如何讓女性在男性壟斷的行業里,得到切實可行的培訓,從而開拓就業領域?人們尤其需要實施具體可行的方案,為引進女性勞動力提供切實保障。在這方面,較多研究聚焦于IT行業。IT行業作為新興的技術產業,一開始便為男性所壟斷。研究機構為了在IT行業引進女性資源,在理論方面進行了深入調查,從關于IT行業培訓信息的獲得、培訓師傅的指導、學習方面的困難、學習方面的期望、擇業動機等,基于性別差異進行了實證研究。
其次要轉變社會觀念,提高女性就業質量。女性所從事的所謂的“簡單工作”,實際上并不簡單。比如服務業中與人打交道的工作,雖被稱為簡單工作,卻有著較高的能力要求,尤其是對人格能力、社會能力等關鍵能力的要求較高。因此,對于女性所從事的所謂的“簡單工作”,有必要提高其社會聲望,提高其工資待遇等。
(三)制定政策法規
提高女性就業率和就業質量,需要政策法規的保障。在這方面,德國做得較好。
首先,德國在2005年頒布的《職業教育法》第一次規定可以有條件縮短女性職業教育時間。由于很多女性身兼照顧家庭的重任,女性職業培訓要求更多的靈活性。《職業教育法》第八條明確規定,如果女性需要照顧孩子或者有需要特殊護理的家人,可以縮短培訓時間。這樣,對女性而言,家庭和教育可以更好地結合起來。
其次,德國是第一個把部分時間工作制寫進法律的國家。女性在無法全天候工作的情況下,半日制等形式的“部分時間工作”也不失為一種補償性的選擇。為女性提供足夠的部分時間工作,能夠有效提高女性就業率。
但由于德國是一個高福利的國家,注重對弱勢群體的保護。生育假、稅收政策等在維護女性利益的同時,也讓女性對于福利政策形成了過度的依賴。女性踏上職場的積極性減弱了。
另外,在德國,托兒所、幼兒園等社會設施的缺乏,形成女性就業的一大障礙。這一情況的改善,有賴于相關政策法規的出臺。
總之,制定政策法規應當把握好這個“度”,既保障女性生育的利益,又能促進女性就業,同時能解決女性的后顧之憂。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女性就業率和就業質量,促進經濟的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1]ALLBUS 1982-2004,Eurobarometer 65.1 (Frühjahr 2006).In: Angelika Scheuer und Joerg Dittmann: Berufstaetigkeit von Müttern bleibt kontrovers. 07.2007.
[2]Statistisches Bundesamt: Statistik der Studenten, Deutschland 2007. URL:https://www.genesis.destatis.de/genesis/on-line/logon.
[3]Granato, Mona; Schittenhelm, Karin: Wege in eine berufliche Ausbildung:Berufsorientierung, Strategien und Chancen junger Frauen an der ersten Schwelle.01.08.2003. URL:http://www.sowi-online.de/reader/berufsorientierung/granato-schittenhelm.htm.
[4]Institut Arbeit und Qualifikation (IAQ), Universit t Duisburg-Essen: Frauen in Einfachen“ Ttigkeiten.General Direktion. Interne Politikbereiche der Union.Studie PE 378.298. 05.2007.
[5]同4.
[6]Eurostat online Datenbank. 2005. In: 同4.
[7]Michaela Kreyenfeld,Dirk Konietzka,Esther Geisler und Sebastian Bohm: Gibt es eine zunehmende bildungsspezifische Polarisierung der Erwerbsmuster von Frauen Analysen auf Basis der Mikrozensen 1976-2004.Max-Planck-Institut für demografische Forschung. 03.2007.
[8]同4.
[9]Lauterbach 1994; Klein und Braun 1995;Kurz 1998;Drobnic 2000.In:同7.
[10]Solga,H.(2002):Ausbildungslosigkeit “als soziales Stigma in Bildungsgesellschaften. Ein soziologischer Erkl rungsbeitrag für die wachsenden Arbeitsmarktprobleme von gering qualifizierten Personen. Ko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 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54: 476-505. In: 同7.
[11]Gender-Datenreport 2005.S.97.In:Angela Venth:Gender-Kontraste: Das Lernen von Frauen und Mannern.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Erwachsenenbildung.03.2007 URL: http://www.die-bonn.de/doks/venth0701.pdf.
[12]Statistisches Bundesamt: Frauen in Deutschland 2006. Wiesbaden. 2006.
[13]Statistisches Bundesamt: Alltag in Deutschland. Forum der Bundesstatistik, Bd. 43. Wiesbaden. 2004.
[14]同7.
[15]Bundesministerium für Familie,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 (BMFSFJ): Kindertagesbetreuung für Kinder unter drei Jahre. Berlin. 2006.
[16]Sainsbury, D: Taxation,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nd employment. In: Sainsbury, D. (Hrsg.): Gender and Welfare State Regim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S185-209.
[17]Bundesministerium für Familie,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 Familienkompetenzen als Potenzial einer innovativen Personalentwicklung. Berlin/Bonn.07.2002.
本文系全國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課題教育部青年專項“‘大職教觀視野中的職業教育制度變革研究”(課題編號:EJA06022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