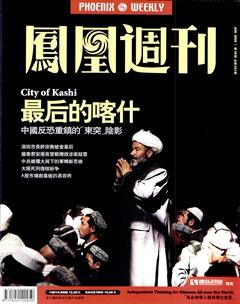記憶之戰
崔衛平
影片《南京!南京!》的討論,同時引發的是一場“記憶之戰”。這部影片貌似“青年導演”的“實驗”之作,在基本的敘事脈絡方面,卻完全沒有超出官方意識形態的框架。而很可能,民間卻有著另外一部關于這段歷史的記憶之書,盡管它是如此零落和不完整。兩種記憶之間的差異和懸殊其實一直存在,在某個特別的時刻就會爆發出來。
回想起來,第一次有人同我談起南京大屠殺居然是一個日本青年,真是諷刺得很。那是在70年代末,作為77級中文系學生我們被要求與留學生同住,以培養他們的語言環境。留學生們時常舉行聚會,—次在吵死人的巨大音響當中,一位日本留學生將我拉到墻角,用他不熟練的漢語嚴肅地對我說:他本來以為到了南京,南京人民會對他揮舞拳頭,將他打死,但是什么也沒有發生。他一邊說一邊做著揮拳的手勢。那時候來中國的,一般都是左派青年。
他的這番沒頭沒腦的話,才使得我格外關注1980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35周年時,報刊雜志上開始出現的那些圖片和報道。此時我所感到的震撼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這件事情本身,另一個是,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我不知道在我熟悉的街道上,兩個日本軍人曾經進行過殺人比賽。從廣播里我經常聽說,日本有人始終想要歪曲篡改該國教科書中有關侵華內容,但是我們自己的教科書上為什么沒有南京大屠殺這么重要的歷史事實呢?
我們關于那場戰爭的了解,居然主要來自電影:《小兵張嘎》、《雞毛信》、《地道戰》、《地雷戰》、《趙一曼》、《八女投江》,《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回民支隊》,《狼牙山五壯士》以及《永不消失的電波》、《野火春風斗古城》等。現在看來,所有這些影片存在的普遍問題是——不管日本侵略軍所作所為如何,最終他們都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顯出其魑魅魍魎、不堪一擊的原形,而另一方面,在與日本鬼子的斗爭中,革命人民都表現出高昂的革命斗志,他們的品格在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之后,變得又崇高又偉大。
因此,我們從電影中所了解的那個苦難時代,卻是一首首人民戰爭的勝利之歌與贊美詩,是一場場英雄主義的壯歌和凱旋,是正義必然戰勝邪惡的節烈之聲。他們當中即使有人犧牲了但是他們的鮮血只是染紅了戰斗的旗幟,使得這旗幟更加神采奕奕和迎風飄揚。尤其是像《地道戰》、《地雷戰》這樣的影片,最終造成的竟然是一種勝利狂歡、普天同慶的氣氛。難怪看了這樣影片的年輕學生,他們變得并不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相反更多地感到生不逢時,覺得自己錯過了一個真正輝煌的、大展宏圖的年代。
事實就是這樣被篡改了,歷史就是這樣被顛倒了。戰爭所帶來的巨大災難和破壞被掩蓋尤其是對普通民眾的深深傷害很少被提及和表現。那些瞬間被奪走生命的人們呢?那些在奔跑中被當胸擊倒的人們呢?那些頭皮粘著泥土不愿意合上眼睛的人們呢?那些在自家胡同口被追殺槍擊的人們呢?那些還沒有來得及享受生命的年輕人和孩童呢?那些被進行中的軍車碾過頭顱和壓成傷殘的人們呢?那些在血泊中呻吟吃力地望著夜空的人們呢?那些被火光映照的一張張無力、憤怒、悲愴的面孔呢?他們心中的被欺騙,被蹂躪、被拋棄的復雜感情昵?
這—切從未記載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當中。那些永遠沉埋在地底下的人們,是再也不會開口的失敗者,輸得一干二凈,他們的悲哀、痛苦,也必須隨著他們的身軀一道離開這個世界。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不知道他們的家庭住址、家中人口,兄弟姐妹如何,老人如何,孩子如何。而他們如果得到再度記起,除非能夠用于產生某種既定的意義,被引向一個需要的目標,用于某種宣傳。否則,他們就永遠被抹殺。“歷史”喜歡站在得勝者一邊,崇尚歡天喜地的慶典和節日。
逝者苦,生者也難。不僅是那些痛不欲生的母親和妻子們,包括所有從那個時刻生還的人們。經歷過大屠殺那樣一種災難之后,當看到同胞在身邊、在大街上倒下,這個人眼中的世界發生坍塌,他原來堅信不疑的世界秩序發生崩潰,他心中善惡是非的天平開始傾斜,這個世界上哪里還讓他覺得是安全,可靠和感到踏實的?他還能信任什么,從什么地方開始重新撿起自己生命的意義?當外部世界遭受蹂躪時,他的內心和他的人性也在遭遇從未有過的危機與災難!從今之后,他如何去做?按照什么原則或者理想?還是僅僅依據本能和欲望?事情真的像電影里所表現的那樣,在經歷了巨大災難之后,人們只會越發堅定和堅強,而不是越發虛無和犬儒?
如果戰爭與災難所帶來的只是弘揚人性,那么它們就是一件需要加以贊美的東西了,從摧殘與破壞中只能產生人性的升華,那么它們就是不可多得的美德催化劑了。這從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的記憶,是一個經過美化的謊言。在這一點上,影片《南京!南京!》的做法與從前如出一轍。幾個為人們記住的面孔無一不是崇高赴義的陸健雄(劉燁扮演)、姜老師(高圓圓扮演),包括妓女小江(江一燕扮演)。歷史上記載當年難民營里的妓女為什么舉起手來愿意去日本軍營,是因為她們在難民營里始終受到其他婦女鄙夷不屑的眼光,因而她們挺身而出,是為了在那些瞧不起她們的人那里挽回尊嚴這樣的出發點有些類似德國影片《朗讀者》中,主人公漢娜寧愿坐牢也不愿意當眾承認自己不認字。這樣做有其特殊的個人原因,而不是影片中虛構出來的是為了難民營過冬的糧食,衣物。人為地拔高這些女人,乃至將一些普通婦女也放在舉手的行列當中,便弄得強奸不是強奸,而是一項造就美德和貞女之舉了。
注意這些人都是普通人,陸健雄也只是下級軍官。對于普通人們,這部影片采取的策略是讓他們抵抗,在碰到危險時“我上,我上”,而不具有其他選項。從這一點來看,去年地震時中學老師范美忠先生的發難,不是沒有道理的,盡管筆者當時也批評了他。在我們的語境中,主導意識形態始終是鼓勵人們作犧牲的,而哪些人正在身處危險,哪些人能夠被犧牲掉呢?就是平民。在當年大屠殺的南京,當官的、有錢的都跑掉了,能夠用作犧牲的是那些跑不掉的普通人,拿出生命來作殊死抵抗與他們從來沒有關系。《南京!南京!》只是再度重復了這個犧牲的神話,在這方面它絕不敢觸碰禁區。
如果說這部影片有什么“突破”的話,那就是讓日本兵與漢奸重歸人性,讓他們身上的人性蘇醒。給他們提供人性演變的過程。也就是說,與以往影片不一樣的是,不僅人民勝利了同樣侵略軍與幫兇也找到了人性的力量,得到了自我救贖。結果皆大歡喜,沒有人需要為戰爭,屠殺及其帶來的創傷負責,沒有一方是在承擔、承受戰爭的重負。這個放棄追究責任的立場其實并不新鮮,只是從前不能表述得這樣赤裸裸。
那些有權者、有錢人,他們從戰爭當中所受的損失是十分有限的,如果有什么損失也是很快得到恢復的,弄不好還有從這場戰爭中獲益匪淺的,正好從這場戰爭中獲得發展壯大,這些人肯定不需要去太多考慮戰爭的責任和負面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外來侵略軍的責任與本國當權者(及后來的各種歷史書寫者)的責任是連在一起的。后者越是不能在強權者面前保護人民,他們便是越要抹去或減輕侵略軍的暴行,除非對他們的宣傳有用。當我與海峽對岸的學者提到《南京!南京!》時,對方也會用“抗戰”來表達那個年代,我驚呼這種說法怎么跟我老爸一個樣!在“抗戰”這個提法當中,包含了一個自我表述的立場,即表明自己是抗日的,強調自身在戰爭中的主體位置,而不說是“日軍侵華”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使用某個稱呼看似小事其實非常重要。戰后很長時間之內,在公共語言中,人們仍然沿用當年納粹所稱呼的“最終解決”來指那件事情,直到1978年,一部在美國熱播的電視連續劇叫做《大屠殺》,人們才普遍采用了“大屠殺”這個提法。
實際上在1937年入侵南京的日本軍隊中,根本找不出這樣一個叫做角川的士兵!那么這樣的虛構是為了什么?在今天意味著什么?是什么樣的途徑,才能釋放出這樣荒腔走板的“想象力”,肯定不是朝向亡靈的那個方向,不是任何倫理和道德的要求,而是某種現實利益,那就是——該部影片想要走日本市場,想要取得日本人的票房陸川將這個又表述成“用電影去教育日本的年輕一代”,這也未免太自作多情了吧,就像影片中角川靈魂的得救,一定需要中國人來操心嗎?所謂“日本兵的人性”,這真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立場與理解。
如今“人性”這個詞用得太濫了。當騷擾鄧玉嬌的那些淫官們前往雄風賓館夢幻娛樂城的時候,心中想著的肯定是自己的“人性”要求,當那些貪官們將國家與人民的財產中飽私囊的時候,他們所響應的也是自己內部“人性”的呼聲“人性”是這些竊賊與荒淫無恥者的最后一件外衣,是他們企圖替自己的罪惡華麗轉身的最后一件法寶,他們除此而外沒有別的能夠替自己遮羞的東西了。這就是這部影片所折射出來的中國當下的國情和語境——以往“左”的那一套(對人民群眾的要求)依然存在,同時又添加了給予當道者網開一面的“右”的說辭。
關于大屠殺的慘景,影片主要表現的是被強奸的場景與叫喊。這真是一個不錯的“賣點”,一個吸引眼球的絕佳理由。從這樣的表現中,人們關于南京大屠殺能夠建立起來的知識和印象是什么呢?可以說,影片的制作者竊取了南京大屠殺這個公共的記憶資源,把它拉向一個更深的深淵。這樣一部想方設法替侵略軍脫罪,給巨大災難與不幸抹上人性彩虹的影片,對于大屠殺的亡靈們來說,是“二次屠殺”,令他們“二度死亡”(威塞爾語,此人為猶太作家,因堅持記憶獲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
南京大屠殺中遇難者的人名是再也找不回來了。70年來,沒有一個官方企圖做過尋找名字這件事情。但至少,在民間,肯定有著另外一部關于南京大屠殺,關于日軍侵華歷史的記憶。它也許像一段漆黑的墻面,上面沒有幾個字;也許這墻壁已經剝落不堪,飄灑著燃燒的灰燼,但是某些歷史會通過我們民族的某些集體無意識,通過我們身體中的密碼,通過我們的心靈和感情,在同胞之間和上下代之間,頑強地繼承和傳遞下來。
顯然,在有關歷史記憶方面,來自民間的表述與來自官方的表述,其間的分歧和沖突,還有其他許多。近60年來的歷史,許多次運動(或者民間應該發明另外一些詞匯來稱呼它們)帶來的無數災難,官方有官方的定論和結論,民間也會有民間自己的記憶和故事。近期人們愿意用“大饑荒”,來稱呼所謂“三年自然災難”,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