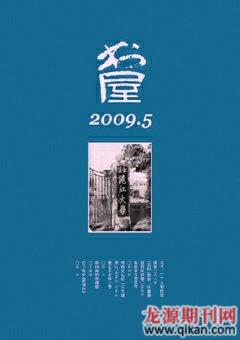我生長在鐵一號
顧 土
鐵一號,就是北京鐵獅子胡同一號,現在已經稱為張自忠路三號了。鐵獅子胡同在我記事時早就蕩然無存,后來的張自忠路也被一改再改,時而成了工農兵東大街,時而成了地安門東大街,時而又成了東四十條的延伸,最后終于修了一條寬敞無比的平安大街,將張自忠路化為其中的一部分。
鐵獅子胡同一號曾經是清朝的親王府,清末,府內建筑被拆除,重新建造了兩組磚木結構的歐洲古典式灰樓,海軍部和陸軍部設在其中。1912年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時,總統府和國務院就在這里;靳云鵬任國務總理時,也曾作為總理府;1924年段祺瑞當了臨時執政,這里成為執政府;后來這里也做過北平衛戍區司令部,也曾是二十九軍駐北平軍部及冀察政務委員會辦公所在地;1937年變為岡村寧次的日本華北駐屯軍總司令部,東院則是日本特務機關興亞院;1945年后這里是十一戰區長官司令部和國民黨北平警備司令部。1949年以后至今,中國人民大學將此地作為校舍的一部分。
鐵一號的大門是中式建筑,坐北朝南,為一座面闊五間的懸山頂木結構建筑,上鋪灰瓦。隔著馬路,大門對面,還有一道大影壁十分惹眼,但在我小的時候卻被公共廁所和包子鋪所遮蓋。大門左右各臥有一排玲瓏的小石獅,而門樓兩旁端坐的則是兩頭大石獅,威嚴中略顯慈祥。大門下曾經橫有一道長長的門檻,讓童年時的我必須把一條腿拼命抬起來才足以跨過,門檻現在已不知去向。
鐵一號大院百年來發生過許多事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一八”慘案了。其實,這座大院長久沒人注意,外人只知道是個單位所在地,或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清史研究所”,直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門口東側立起一塊石碑,上書“‘三·一八慘案發生地”,才令路人開始琢磨“三·一八”慘案。上世紀九十年代,大門東側墻上又出現了“段祺瑞執政府”字樣,原來這里已經被列為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的某一天,我忽然發現文物保護單位又升格為全國,而且叫做“清海軍部、陸軍部舊址”,大院因文物長期被居民占據,導致隱患環生,也不斷遭到通報批評。鐵一號這一老建筑群,由單位駐地發展到革命教育基地,再到市級文物,最終成為全國重點文物,可以看出社會對歷史建筑的認識過程。
我生在鐵一號,長在鐵一號,讀小學以前只知道這里有我的家,讀中學時知道魯迅紀念的劉和珍等人倒在大門前,讀大學以后才終于清楚了這里的歷史地位,天天經過大門時,當然也非常想知道“三·一八”慘案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事件。
一
讀中學那會兒,課本沒什么可讀的內容,但收有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我們都能背誦下來。正因為有了魯迅的這篇文字,我們記住了“三·一八”慘案,也記住了劉和珍的名字。就像我們當時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的那點有限知識大多來自毛選注釋那樣。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于這些傳說,竟至于頗為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于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群君的。而且又證明著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大約因為魯迅這一段寫得特別有感情,所以,這一段同學們也背誦得特別有激情。根據課本的注釋和老師的講解,從此我也一直認為“三·一八”慘案的罪魁禍首是段祺瑞,而且知道段是那時北洋軍閥反動政府的頭子。其實,直至1979年版的《辭海》依然如此解釋:
1926年3月12日,馮玉祥所部國民軍與奉系軍閥作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軍艦掩護奉軍軍艦駛進天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經守軍擊退。日本竟聯合英、美等八國于16日向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府提出撤除國防設備等無理要求。時稱“大沽口事件”。3月18日,北京群眾五千余人在李大釗等人領導下,在天安門集會抗議,會后游行請愿,要求拒絕八國通牒。段祺瑞竟下令衛隊開槍,群眾死四十七人,傷一百五十多人。這起慘案激起全國人民極大憤怒。
1989年版的《辭海》只字未改,原封照搬,只有1999年版的《辭海》以新的文字顯現出些許不同:
1926年段祺瑞執政府屠殺人民群眾造成的慘案。3月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張作霖的奉軍交戰期間,12日日本軍艦進逼天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陣地,被國民軍擊退。16日日本聯合英、美等八國援引《辛丑條約》,向段祺瑞執政府發出要求撤除大沽口防務的最后通牒。“大沽口事件”發生后,18日北京群眾萬余人在李大釗等領導下在天安門集會,要求“駁牒”、“逐使”。會后群眾舉行游行請愿,在執政府門前遭段祺瑞衛隊的屠殺,死四十余人,傷一百余人。
1999年版《辭海》的“三·一八”慘案的辭條最耐人尋味的是,“軍閥”這樣的形容沒有了,不再提“段祺瑞竟下令衛隊開槍”,而加上了“援引《辛丑條約》”一句,但卻將“掩護奉軍軍艦”抹去;另外,集會的“五千多人”變成了“萬余人”,死傷的具體人數與以前相比,反倒更加模糊了。
關于“三·一八”慘案的發生過程,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文史資料選輯》上曾經有過一番爭論,均為政府與學生雙方的直接當事人,針鋒相對,其時間跨度居然達二十年。
1960年3月內部發行的《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發表《“三·一八”慘案親歷記》,作者楚溪春,1926年,他曾任執政府衛隊旅上校參謀長,是保衛鐵一號執政府與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的負責軍官。楚溪春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出來后先在直系的第二十師任中校主任參謀,1924年二次直奉戰爭中直軍敗北,所在部隊也被編散,1925年1月他成了京衛軍第一旅也就是執政府衛隊旅的參謀長。執政府倒臺后,他又參加晉軍,以后一直沒有脫離軍界、政界,最高的職務曾是河北省政府主席,應該算是民國政壇上的一個人物,所以隨傅作義易幟后可以當上政務院參事、全國政協委員。他于1959年8月寫下的親歷記是這樣回憶的:“三·一八”慘案之前半個月,已經有過幾次學生反對外國的游行,因有北京警衛司令鹿鍾麟派遣的大刀隊隨行,均未出事。慘案前一天,衛隊接到上級命令,說次日學生要到天安門開會,會后去段宅請愿,守衛官兵必須嚴加戒備,但要萬般忍耐,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以免發生意外。由于鹿鍾麟已率隊去天津與奉軍作戰,所以大刀隊不能再度隨行。3月18日當天下午,楚溪春親自到段宅布置戒備,而執政府由衛隊旅少校參謀王子江負責,布置時特意要求前幾排官兵不準扎皮帶,中幾排可扎皮帶但不許拿武器,后幾排準許攜帶武器。等到慘案發生后,楚才得到消息,立即趕到執政府,命令士兵回營房集合。此時北京警衛司令部代司令李鳴鐘也已到達,神色慌張地對楚說:“打死這些學生,叫我怎么辦?”當他們前往吉兆胡同段宅見到段祺瑞時,段已經知道此事,先是大聲喝問李能否維持北京的治安,然后對楚說,他不但不懲罰官兵,還會獎賞他們,因為這是一群土匪學生。過了幾日,司法部、高等法院、陸軍部聯合處理這一慘案,要衛隊旅前去對質,楚打算讓王子江出席作證,但王十分害怕,不愿出頭。楚聽一個上尉軍械員介紹,當學生向執政府擁擠時,學生拿著帶鐵頭的木棒打士兵的頭部,罵士兵是“衛隊狗”、“軍閥走狗”,士兵被迫后撤。就在學生即將沖進執政府大門時,王子江命令士兵開槍,但其意是朝天放空槍嚇跑學生,不料守衛士兵真的平射起來,慘案于是造成。衛隊旅為了掩蓋真相,顛倒是非,假造出一些學生準備縱火和握有槍支的“罪證”,當局當然偏袒衛隊旅,案子不了了之。
楚溪春的意思很明顯,就是說這一慘案是一次偶然發生的事件,只是事后段祺瑞和當時的政府做得比較無恥。身在“三·一八”慘案現場另一方的李世軍也寫了一篇反駁文字《“三·一八”慘案紀實》,認為事情并不如楚溪春所說的那樣,這不是什么偶然發生的意外不幸事件,而是“段祺瑞及其幫兇蓄意策劃的一場血腥大屠殺”。也許“文革”的原因,他寫于1963年11月的文章竟然遲至1979年9月《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六輯才見天日。李世軍又是什么人呢?他1922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1923年加入國民黨,曾長期負責國民黨在北京的學生運動,發動組織了一系列反對北洋執政當局的活動,1924年還在天津接受孫中山的接見。1927年后,他一直活躍于政壇,位至監察委員,1949年完成轉身,曾任民革中央委員、江蘇省政協副主席、國務院參事。據他回憶,早在“大沽口事件”之前段祺瑞就已經準備向愛國青年學生開刀了,依據是段曾在《甲寅》發表過一篇充滿殺機的文章,并公布了“整飭學風令”。段政府的國務總理賈德耀也曾致電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要他對“受赤化之毒”的學生“嚴加管束”。張之江則致電段,說:“學風日下……請執政設法抑制。”段復電稱:“維持秩序,轉移風化,亦為地方軍警之責。”1926年3月初,北京空氣緊張,布滿密探,12日紀念孫中山逝世周年紀念大會時,“段的緹騎”四出,大有一觸即發之勢。16日,各校學生向天安門進發,在校門口即遭武裝警察毆打,重傷者四十余人。16日當晚,北京學生聯合會召開緊急會議,參加的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北京執行部、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等三十余人,會議決定18日舉行第二次請愿游行。17日這一天,“段祺瑞的狗腿子”四下散布恐怖氣氛,聲稱如果再游行,一定要用武力制止。李世軍父親的朋友也告訴李:“段老總這幾天火氣很大,表示決心要殺一些赤化搗亂分子。”18日天安門前舉行了群眾大會,會后學生加工人約兩千余人來到執政府門前請愿,門前早已密集全副武裝、殺氣騰騰的軍隊。學生代表要求會見段祺瑞,過了半個小時,一個軍官出來兇狠狠地說,執政有病休息,不在這里,你們趕快走開吧。隨后,大屠殺的信號響了,軍隊立即行動。就在楚、李文章之間的1963年9月,曹祥華在《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期上還發表過一篇對楚溪春文章的訂正,實際上這不是訂正,而是駁斥。他當時是北京平民大學的學生,中共黨員。他根據親身經歷也認為,這是“段祺瑞蓄意屠殺群眾”,學生完全是被動挨打。
關于“三·一八”慘案的回憶還有很多,有親歷有聽聞,自慘案發生后就已經陸續開始,楚和李的意見基本代表了兩種主要看法。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楚與李可謂敵對的雙方,一屬于政府一屬于學生,一個是北洋執政當局的軍人,一個是國民黨學運的工作者;以后他們又長期處于一個旗幟下,而且位居顯要;1949年后,他們也一并轉型,成為新時代的“民主人士”,地位差不太多。可是,關于“三·一八”慘案的看法卻依舊對立,從行為敵對的雙方到觀點對峙的雙方,整整延續了半個多世紀。遺憾的是,雙方始終沒有正面對質,李的反駁文章面世時,楚早已離世十三年。結果也像“三·一八”慘案那樣,許多事情,包括游行人數、死傷人數、是預謀還是偶然、段祺瑞在其中的作用等等,似乎從來都沒有說清楚道明白。
二
“三·一八”慘案是北洋執政當局統治時期的重要事件,相比較民國前期的各種慘案而言,更具歷史價值。因為這一事件涉及當時的中外關系、國際利益、黨派地位、勢力消長、人物評價,也影響了后來的歷史走向、政治格局。
廓清“三·一八”慘案的歷史迷霧,首先要將歷史回放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后的北京政治舞臺。當時馮玉祥班師倒直,使第二次直奉戰爭以直軍失敗告終,從此形成了馮玉祥和張作霖合作的局面。可是,兩派勢力都不可能獨攬乾坤,只得成立“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推舉曾長期實際掌握北洋政權的段祺瑞出山,當了個“臨時執政”。表面是“凡立法、行政、海陸軍權,均集于執政一人之身”,事實上,段在1920年直皖戰爭后就已經失去了軍事實力,身邊只有章士釗、許士英、王揖唐、曾毓雋、梁鴻志等謀臣策士,根本無權,靠周旋于張、馮勢力之間,均衡、調和、騎墻來維持自己。在段的周圍,以吳光新為首的“國舅派”主張倚張抑馮,而以段宏業為首的“太子派”則相反。《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一輯刊登過一篇段府老仆役王楚卿的回憶,介紹了不少段祺瑞的真實情況,他就說:“執政的風光只表現在出門的時候凈凈街而已。所以連他的舅老爺吳光新都看出苗頭來了,借著到日本觀操的名義,一去不復返了。”過去在黎元洪、徐世昌等人當總統時,段是實權派,如今,他自己也親身嘗到了黎、徐的滋味。
馮、張之間原本是利用關系,直系一倒,他們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地盤、財政、人事和對外關系、思想傾向方面都處于對立狀態,經常鬧得不可開交。張還認為馮的倒戈是他花錢買來的,根本瞧不起馮及國民軍。馮、張勉強聯合僅一年,由于馮暗中支持反奉的孫傳芳,策動奉系將領郭松齡反戈倒奉,打敗占據直隸且親奉的李景林部并趁機攻克天津,使雙方沖突完全公開化。1926年2月,張作霖聯合東山再起的吳佩孚,拉入山西督軍閻錫山,共同對付國民軍,3月間向京、津等地的國民軍開戰。導致“三·一八”慘案的“大沽口事件”,正是奉軍與國民軍相互進攻而引出的中外交涉事端。而馮玉祥及其國民軍與段祺瑞的關系也日見緊張,因為國民軍一向認為段偏向于張,另外,由于段與張在反對“赤化”、反對蘇聯、對待孫中山北上、對待南方革命勢力、對日關系等方面均有一致之處,也加深了馮玉祥與段的矛盾。1925年底,本來無權的段執政更成傀儡,北京實際是國民軍的天下,馮玉祥雖已下野,但依然是國民軍的實際領袖。也因為如此,馮玉祥及其國民軍可以在段的眼皮底下處決段多年的至交和心腹徐樹錚,還扣押了段的親信曾毓雋等,而且正有意推倒段的執政府。“三·一八”慘案前后,可以說,段祺瑞已處于風雨飄搖的時刻。
段盡管是個擺設,但他是北洋元老,多年掌握大權,門生、舊部遍及各地,其中包括馮玉祥及其部下,所以大家表面上還得給他十足的面子,而他遇人遇事又倚老賣老,依然無所顧忌,直言不諱,常常忘了自己現實的情形,還端著最高統治者的架子。他認為張作霖出身胡子,馮玉祥曾經是部下,于是,對他們二人常常函電交責。北京警衛司令鹿鍾麟見他時,他當著眾人的面照樣可以得意洋洋地說:“這是我從前的兵。”其實鹿的心里根本沒拿他當回事,后來包圍執政府準備捉拿段祺瑞的恰恰正是鹿鍾麟。段的這些言行,很容易給人造成他就是主政者的印象。
“三·一八”慘案發生時,北京實際的主政者是誰呢?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賈德耀可以算其一。別看他與段是同鄉,又曾是段的學生,但據賈德耀后代的回憶,他與馮玉祥的關系更好,交情深厚不說,在驅逐遜帝出宮、迎接孫中山北上等問題上也與馮相一致,對段及其僚屬也多有不滿。他的組閣,既是段的邀請,也是馮、鹿等人的擁戴。實際控制北京軍權、警權、治安權的,應該說是鹿鍾麟,此人是馮手下一員大將,始終緊跟馮玉祥,曾代替馮指揮國民軍作戰。其繼任李鳴鐘,也多年跟隨馮,是馮的主要助手。李世軍文中提到的代馮遙控北京的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更是馮的左膀右臂。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當時有一紙宣言說得很明白:“北京現狀,完全在馮系軍人控制之下,段祺瑞是馮氏的傀儡,賈內閣是馮氏的輿臺,故馮玉祥及馮氏軍人對北京治安應負絕對的責任。”
北京明明實際掌握在國民軍手中,但為什么支持國民軍的天津行動、反對八國對國民軍最后通牒的游行人群還要不斷向北京政府游行請愿呢?這是因為:第一,游行也是向各國駐華使館示威,3月18日最初的大會選在了天安門,這里距離東交民巷最近。第二,示威組織者并不知道執政當局,包括國民軍將要采取什么對策,想以此聲援甚至逼迫國民軍;另外,馮玉祥此時還是“五原誓師”前的馮玉祥,也是沒有完成革命轉型的馮玉祥,表面上,段祺瑞與國民軍還都屬于臨時執政府,抗議的人群當然不可能也沒有心思將他們明顯分出彼此。第三,段祺瑞長期在人們的心目中親日反蘇,而且在馮、張聯合中偏向奉系,被人懷疑有可能是奉系倒馮的內應,所以特意要到段的辦公地點和住宅前發出憤怒的吼聲。
“三·一八”慘案的直接起因是“大沽口事件”,所以,澄清這一事件是廓清“三·一八”慘案的前提。1926年3月初,奉軍軍艦進攻馮玉祥國民軍所占領的天津大沽口;9日,國民軍在大沽口水道布置水雷,通知一切商船不得進入;次日,英、美、法、意、日等國照會北京執政府抗議,認為違反了《辛丑條約》。隨后,鹿鍾麟趕緊作出解釋,并提出外輪入口的具體辦法。11日晚,日本駐津總領事提出次日上午將有一艘驅逐艦入口,要求免檢放行,雙方約定時間為上午十點。12日,中方認為日本艦只入港時間不對,艦數也不符,可日方卻強行闖關,炮臺守軍放槍警告,日艦立即用機關槍還擊,守軍負傷。16日下午,日、英、美、法、意等八國公使在荷蘭使館聚會,決定為維護《辛丑條約》共同向北京政府發出最后通牒。通牒提出五項要求:天津航道停止所有戰斗行為、排除水雷及一切障礙物、恢復所有航路標志、對外國船舶不加任何干涉、停止對外船的一切檢查,并要求在四十八小時內兌現,至遲不得超過3月18日正午,否則將“采取所認為必要之手段”。這一通牒當日下午四時被送到外交部,北京執政府外交委員會隨即召開會議,認為通牒內容已經超越《辛丑條約》,違背條約精神。而且航道能否恢復交通,關鍵在于奉軍是否進攻天津。會議決定起草復文,由外交部派員送達荷蘭使館,并轉達相關國公使,此時已是3月17日。同時,國民軍守軍卻派代表赴日本總領事館,轉達鹿鍾麟口信,承認“大沽口事件”純系中國方面的誤會,希望日方諒解。下午四時,炮臺張團長又訪英艦艦長,表示國民軍將撤去一切障礙;傍晚,張團長又訪意艦艦長,表示對各國提出要求可以照辦,只要奉軍放棄進攻。各國領事對答復相當滿意,而奉軍方面也承認了通牒的五項條件。不過,這些言行并不屬于北京當局,因為北京的外交委員會和外交部還在開會繼續討論對策呢。
“大沽口事件”的處理結果和政府對策尚未公布,北京的游行示威卻何以愈演愈烈呢?對列強的積怨積怒,此原因之一;催動當局采取強硬措施,也是原因之一;但還有更深層的政治動因寓于其中。閱讀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的《三·一八運動資料》、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的《三·一八慘案資料匯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的《馮玉祥與國民軍》,以及近些年出版的有關馮玉祥與蘇聯關系的著述,即可看出其中的端倪。
“三·一八”慘案,可以說是兩股政治勢力對抗的結果。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與張作霖、段祺瑞等勢力共商國是的可能性不復存在,在奉系、直系的壓迫下,馮玉祥日益“左”傾,于是,處于上升時期的國民黨連續發動學生、工人等群眾運動反對北洋各系,支持南方的革命勢力,為北伐做輿論準備。這也就是為什么早在“大沽口事件”之前北京的游行已經一浪高過一浪的原因。過去我們一向沒有在意國民黨早期發動群眾運動的歷史,實際上,國民黨在北伐勝利、統一中國之前,其群眾運動的發動能量也很大,為宣傳國民黨政治主張、推動北伐成功,貢獻不小。尤其1924年國民黨一大國共合作以后,大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群眾運動更是如虎添翼。李大釗創建了北京等地的國民黨黨部,領導了北京的學生運動、工人運動,但他的公開身份卻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據親歷“三·一八”慘案的董壽平回憶,由于共產黨已經加入了國民黨,所以,包括學生在內的多數人眼里都是國共不分,認為兩黨都是革命,都是親蘇,都是激進。許多人還認為國民黨分左右兩派,左派就是共產黨。張作霖、段祺瑞、吳佩孚等北洋各系攻擊的“赤化”、“共產公妻”等,也是國共不分,甚至將國民軍都算在里面。3月18日前后的各類游行請愿集會,應該說,是由中國國民黨主導的,有共產黨和各社會社團參與組織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北京執行部、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等發起的運動。中共北方區委本身就和這些國民黨組織機構交織一體,其領導人李大釗等人或同屬或兼職,既可分開并列,也可相融不分,有的時候一起開會,有些時候中共自己單獨秘密討論。因為國民黨名氣大,翠花胡同八號國民黨北京市黨部也是活動頻繁,共產黨又是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參與,因而當時多數人將這些人都視為國民黨。“三·一八”慘案前后各類群眾運動組織者位列第一的名字叫徐謙,他也是事后被通緝的第一人,此人的頭銜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國民黨統治全國以后,曾隆重舉行了“三·一八”慘案的紀念活動,為死難者公葬,在北平的幾處地方建立紀念碑,足見其對“三·一八”慘案的重視。只是后來到了我們這一代了解“三·一八”慘案的時候,意識形態主導一切,再加上一看李大釗是主要組織者,國民黨的作用反倒不提了。“三·一八”慘案前后公開出現的組織名稱比較多的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北京執行部、中國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國家主義青年團、孫文主義學會、北京總工會、北京學生總會、學生敢死隊、北京反帝大聯盟、反對帝國主義先鋒隊、留日歸國團、四川代表團、廣東外交代表團、北京國民外交代表團、民生周刊社、三民主義宣傳會、工界聯合會、北大學生會、法大學生會等等。
“三·一八”慘案也是中外關系、國際關系導致的結果,是外國勢力在中國角逐的后果。當時,南方的國民黨、共產黨在蘇聯的支持下,日益壯大;北方的馮玉祥正在向左靠攏,對蘇聯社會主義頗感興趣,非但接受了蘇聯的資助,還在醞釀赴蘇考察。國民黨、共產黨組織的,帶有蘇聯、共產國際為背景的北京游行示威請愿,從一開始就是對親蘇的國民黨、共產黨的聲援,對馮玉祥、國民軍的催促,其最終目的是讓段政府垮臺,其最好的結果是讓馮玉祥上臺,并與南方的革命力量聯手。當然,得益的正是蘇聯。在北京當局尚未對八國通牒作出最后反應時,游行就已經喊出“打倒段祺瑞政府”這樣的口號,可見,解決“大沽口事件”并非最終目的。國民軍中的蘇聯軍事顧問維·馬·普里馬科夫說的一段話耐人尋味:“3月18日,發生了鎮壓學生的行動。學生們舉行游行示威,要求把政權轉交給國民黨,隊伍到達總統府時,總統的衛隊向學生開了槍。”其實,早在二次直奉戰事剛結束時,蘇聯就對結局非常不滿:原本馮玉祥意欲由孫中山北上主持大局,不料,段祺瑞、張作霖并不買賬,而且馮玉祥最終居然還同意請段出來主持。于是,推倒段執政,催促馮玉祥,就成了此后各類游行的一個潛在訴求,而“打倒北洋軍閥”、“打倒段祺瑞”也幾乎成為游行的家常口號。“三·一八”慘案后,普里馬科夫見到李鳴鐘時曾經質問:“你可以解除總統衛隊的武裝,剝奪總統的權力!”當他們認為李不足以擔當此任時,就勸導馮玉祥用鹿鍾麟替換,并且,蘇聯顧問也始終在和李大釗、李石曾等人交換意見,等到鹿鍾麟終于回京取代李鳴鐘時,果然就包圍了段祺瑞的執政府,目的終于達到。
三
“三·一八”慘案究竟系誰主使,就目前所有證據看,與段祺瑞等北京執政當局的上層人物確實無關,即使李世軍、曹祥華的文章也無法具體指證就是段之所為。其實,段當時已經岌岌可危,就算事先他真有此意,北京警衛部隊也未必聽命于他。“三·一八”慘案發生后還不到一個月,段就倉皇出逃,從此下野,永遠退出了政治舞臺。何況,當時段也確實不在執政府內,而是在自己的住宅中養尊處優,不明現場實際情形,當場下令也不大可能,多年來幾乎所有的回憶都承認他事后才知此事。段祺瑞的生活習慣也很有意思,不妨一敘。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很少變化,極其規律。早晨起來吃過早飯,先在書房看公事,然后上衙門處理公務,中午回家吃飯,但從不和家人坐在一起,而是在內客廳單開一桌。午飯后,他在內客廳里間睡午覺,大約兩三點鐘起來,多數時間是在下圍棋,還有高手相陪。下棋以外有詩會,自己作詩,邀同好品賞。晚飯一般都有客人在座,飯后鋪起牌桌,打上八圈或十二圈。這樣的人以此方式掌握國家大政,也算一絕。不過,正是由于他的這種特殊習慣,中午以后都呆在吉兆胡同住宅內,所以恰巧躲過了慘案發生的時刻,那時他正午休,得知慘案時正在下棋。
面對奉系、直系和閻錫山的聯合進攻,面對八國的最后通牒,北京執政當局的其他關鍵人物當時也是前途未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還能在位置上坐多久,北京的未來究竟是何人的天下。賈德耀剛剛當上總理,屁股尚未坐穩;鹿鍾麟正在忙于指揮天津的國民軍加強守備,并在各國之間為“大沽口事件”周旋;李鳴鐘對學生游行一向比較寬容。從當時的內閣和北京警衛司令部在“三·一八”慘案前兩天的工作情形看,他們對待游行示威浪潮基本是不知所措,有時派兵保護,維持秩序;有時派員前往溝通,在沖突后又道歉慰問;對示威群眾的強烈要求,多半無以應對,得過且過,并無確鑿證據表明他們中的某一人企圖大開殺戒。3月17日,游行請愿隊伍曾派代表分別前往執政府和外交部。到執政府的代表與具體護衛的士兵忽然沖突,數人受傷,最后終于見到國務院秘書長,對方答應轉達代表意見,并懲治責任士兵。去外交部的代表不但見到外交部相關人員,還在夜半將已經睡下的賈德耀喚醒,在賈宅會見了這位賈總理,直至次日清晨才離去,賈總理幾乎答應了代表的所有要求。這樣的狀況也表明他們并無蓄意傷害游行隊伍的理由。
然而,慘案還是發生了。其原因不能不從古往今來所有示威抗議的游行說起。
只要不是官方發動的游行,當示威抗議出現時,都會出動衛戍部隊、治安警察以至后來的防暴警察,維持社會秩序,守衛政府機構和各國使領館,給人一種如臨大敵的感覺。當示威游行隊伍與警衛隊伍對峙時,情緒往往也會變得高度亢奮,失控在所難免,直至出現暴力、流血事件。所以,僅一百多年來,各國因此導致的慘案就不計其數。有的確是主政者蓄意所為,有的是具體指揮軍官的妄為,有的是處于高度緊張的士兵或警察的誤為,有的則是游行人群首先使用暴力而為,還有很多根本就難以說清具體的起因。隨著民主與法治的確立,也隨著對付游行示威方法的日趨成熟,流血事件,尤其是死傷事件日益減少。一方面,是對游行的法制界定、暴力非暴力的明確;一方面是對治安部隊防范時的規范化管理,如不準攜帶槍支或是不準攜帶子彈,提高防范工具的無致命傷害性能等。另外,事件之后的獨立調查、相關法律處罰、有關責任人的處理,也不斷完善,使對峙雙方都不敢肆意妄為,除了別有用心外,都極力將自己控制在一個底線以上。可惜,1926年的北京距離這樣的法治規范環境何啻萬里!
1926年3月18日的北京各警衛部隊由于幾天來的游行示威,已經處于高度戒備狀態,情緒極其緊張,楚溪春等人的回憶即可說明。1926年3月18日的游行人群也是異常激憤,因為兩天來的游行已勢不可擋,再加上前一天學生的流血負傷、組織者的不斷推動鼓舞、各界人士的強力支持,致使3月18日從天安門過來的游行人群的情緒格外高漲。凡是參與過游行的人都知道,游行的心理是:社會越關注、影響越大、參與人數越多,也就會越激動,最后難以自控,更難理性地看待對方。這在李世軍、董壽平等親歷者的回憶中也十分明顯。執政府警衛部隊有槍有彈有刀,這是明確的事實;游行群眾拿著什么,說法不一。董壽平說李大釗的確鼓動過大家拿棍拿棒,但也有人說沒見過,這已難以說明白,不過,一大堆旗桿足以被人視作武器了。于是,沖突開始。有人說,是游行隊伍先向執政府沖擊,也有人說他們只是在那里擁擠,還有人說學生正坐在那里休息。這恐怕是個永遠無法辨別的史實,只能說人群已經到達了執政府門口。面對人群,衛隊當然要阻攔,結果,槍擊發生了。究竟誰下令開槍?具體負責的軍官下令,恐怕應該是一個定論。有人說就是楚溪春(據說楚還是一部電視劇《亮劍》里一位楚姓主人公的原型,不知真假),也有人說是王子江,另外還有別的說法,但都是死無對證。死亡人數,各方說法基本一致,因為死人很容易驗明,但傷者人數從來就不統一,因為什么叫受傷并沒有界定標準,有人去了醫院,有人回家包扎,有人湊合湊合就過去了。1905年俄國發生的著名“流血星期日”,其死傷人數,特別是受傷人數,百年來也是說法不一,甚至相距甚遠。至于說參加3月18日集會和請愿的人數說法更是多種,連《辭海》也前后不一致。什么是參加?來了一段又走了算不算?圍觀跟著喊的算不算?估計也只能永久存疑了。
二十世紀各國的慘案無數,如果不是執政當局公然屠戮,僅僅是因為游行期間與軍警對峙而發生的血案,其主要判斷標準不在于誰先動手,這樣的問題任誰也說不清,關鍵在于善后措施。平心而論,“三·一八”慘案的事后處理相對其他慘案來說,做得還不差。
無論楚溪春還是李世軍、曹祥華的文章,都閉口不提“三·一八”慘案的善后,只是說段祺瑞執政府顛倒黑白,掩蓋證據,反誣游行隊伍,通緝游行組織者。這也許囿于他們寫文章時的社會環境,不便苛責。事實是,當時全國幾近一片憤怒聲討,北京幾乎所有輿論都嚴詞譴責,知識界、教育界也紛紛口誅筆伐,各種規模的悼念活動和聲討活動相繼舉行,而這一切,都沒有受到任何阻礙,可謂大張旗鼓。一直是個擺設的國會卻在這時特意召開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學生的“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政府還頒布了對死難者家屬的“撫恤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國務院閣員因此“總辭職”,也就是說一屆內閣政府由此而倒臺。因為一起慘案,導致了這一連串后果,在百年中外慘案史中也算難得。盡管北京當局過后也發布通緝令,并指責游行策劃者的所為,但都屬于表面文章,依照段祺瑞的說法,屬于“維持政府威信”,與前面所做各項相比,算是次要的。至于段執政,一些回憶文章說他聞訊后頓足長嘆:“一世清名,毀于一旦!”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后又宣布自己終身食素,以示懺悔。段執政心里究竟如何想法,我們無從揣測;果真當眾下跪,也算不易;而他的食素,卻并不起自“三·一八”慘案,而是1920年直皖戰事之后在天津做寓公時就已經吃齋念佛了。一個茹素信佛的人,假若真是下令屠殺,那真可謂人面獸心。
當時的京師地方檢察廳4月3日還有一封致陸軍部的公函也不能不提,看見這樣的公函,你不得不想,那時的司法居然還有如此獨立性。其中所述,基本傾向游行隊伍,最后稱:“總之,學生人等少不更事,平日言行有輕躁失檢之處,然此次集會請愿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擊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惟事關軍人犯罪,依據陸軍審判條例第一條及陸軍刑事條例第一條應歸軍事審判機關審理,除國務總理賈德耀等,被訴命令殺人部分,仍由本廳另案辦理外,相應抄錄本案全卷三宗,連同尸身照相、死傷人名清單暨衛隊旅原送各物證,一并移送貴部,請即查明行兇人犯,依法審判,以肅法紀。”
“三·一八”慘案之后,中國政局迅速發生轉變。段祺瑞很快被國民軍攆走。有文章稱慘案讓段執政的合法性喪失殆盡,其實,沒有慘案,他也照樣會被國民軍趕下臺,因為蘇聯不喜歡他,南方革命勢力不喜歡他,國民軍也從沒有認為段會有利于他們。慘案倒是動搖了國民軍在北京的統治基礎,不久便由天津、北京潰退,張作霖這個堅決的反蘇反共反革命派反倒入主京城。于是,具有蘇聯和共產國際背景的李大釗,這個曾經組織“三·一八”大游行的中共黨員被害,蘇聯大使館遭搜查,張作霖與蘇聯徹底決裂。于是,馮玉祥很快就加入國民黨,隨后赴莫斯科,以后又有了五原誓師,與北伐軍遙相呼應。于是,代替國民軍的奉軍在北京的政治態度令北伐軍全面進攻,迫使奉軍退走關外,張作霖命喪黃泉,北洋各系統治最后煙消云散。
這就是我心中的“三·一八”慘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