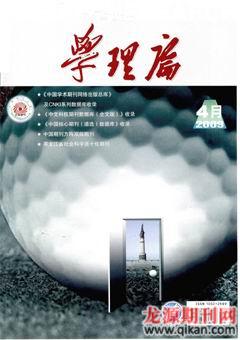論死刑的執行方式
唐貴平
摘要:死刑是人類社會早已存在的現象。各個民族、各個國家歷史上都有相同或不同的死刑執行方式。但總的說來,世界各國的死刑執行的方式從殘忍、血腥逐步邁向文明、人性化。本文通過對死刑執行方式進行回顧,從法哲學和倫理思想角度對其存在進行闡述,并對死刑執行方式的發展趨勢做了簡要說明。
關鍵詞:死刑;執行方式
中圖分類號:D924.12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2589(2009)08—0074—02
一、死刑執行方式
1.用動物致死,即用動物來致罪犯死亡。參與致死的動物很多,例如狗、牛、駱駝、野豬、山羊、猛禽、烏鴉、蜥蜴、昆蟲、嚙齒動物、毒蛇或大蟒蛇;還有用大象踩死,或讓大象用鼻子把人多次拋起摔死;還有用馬拖死等。還有就是用各種猛獸。用猛獸將人咬死在古羅馬非常盛行,此類猛獸包括獅子、老虎、豹子、熊、鬣狗、狼等。這種刑罰在歐洲一直延續到5世紀。中國古代用動物致死的除了五馬分尸外,其他的方式只有模糊的記載,例如使用毒蛇,只見于商代。
2.窒息致死。主要如絞刑、扼殺、溺刑、活埋、吊刑、十字架刑等,使罪犯不能呼吸而死亡。絞刑是最常見的死刑刑罰之一,見于世界各國和各個歷史時期,在許多國家絞刑至今是合法的,薩達姆就是被絞死的。扼殺也就是勒死,與絞刑不同,扼殺使用的是外力,絞刑使用的是犯人自身的重力。在歐洲的某些國家,扼殺發展成絞殺,并一直存在到20世紀70年代。扼殺在中國也長期存在,但不是死刑的合法手段。溺刑就是淹死,地中海地區很早就采用這種刑罰。古羅馬的溺刑經常在犯人身上綁上重物,或將犯人裝在袋子里,扔進水中;某些歐洲國家直到20世紀依然采用溺刑。中國古代的溺刑在南北朝以后就不再采用。活埋,最常見的就是用土埋掉。有人說羅馬的歷史就是從活埋開始的,活埋在法國、德國等地后來有所發展。在中國秦朝,“坑儒”就是例證,以后歷朝,活埋不再是法律手段,只是私刑。
3.刀斧砍殺。主要有斬首、凌遲、割喉、肢解等,斬首就是砍頭,在中國,斬首多用于平民,因為中國人不喜歡死無完尸。而歐洲的貴族認為,不死在刀劍下是可恥的,其尚武好斗在死刑上都得以表現。凌遲就是小塊地切掉身體的一部分,直到死亡。凌遲這種方式很可能是從古埃及的活體解剖發展出來的。在地中海地區,凌遲在公元前就出現了。在中國一般認為是在元代出現的。英國關于這一刑罰的法律直到19世紀還保留著。與砍頭不同的是,割喉之后,頭顱和身軀沒有分離,它是古羅馬特有的刑罰,甚至被稱為“羅馬刑”,割喉在中國較少,不見于正史和法律。活剝,這種刑罰在亞洲、歐洲都有。印度的做法是用小火在身體表面烤,然后再剝。古希臘、古羅馬也有這個刑罰。在中國活剝不是法律規定的刑罰。肢解與凌遲不同,肢解是大塊剁掉,凌遲是小塊切下。這種刑罰存在于世界各地。中國古代還有腰斬刑罰。鋸刑與肢解有點類似,區別主要在于工具。這種刑罰最早出現于地中海周圍,后來傳到了希臘、羅馬。《圣經》中就有鋸刑的記載,在中國歷史上則沒見到這種刑罰的記載。
4.毒死。毒藥致死,這種方式也產生于地中海地區,古希臘著名思想家蘇格拉底就死于這種刑罰。這種致死方式后來也被人經常使用,但大多都是司法外的致死手段。中國古代也有使用毒藥的,但沒有成為正式的法律。現代的注射刑就屬于此種,只是技術更先進。毒氣是現代化學技術提供的殺人手段,當今世界只有美國還使用。
5.貫穿軀體致死。貫穿刑就是用長形利器貫穿人體。希臘、羅馬人的貫穿刑用標槍較多。此類貫穿刑在19世紀中期依然被歐洲國家采用。箭刑,這種刑罰比較簡單,用弓箭射死,在中國和世界各地都有。槍刑,火槍出現之后,這種死刑在歐洲就開始出現了,有人認為它是古代“箭刑”的延伸。由于最初的火槍比較昂貴,因此早期的槍刑只適用于有身份的特殊人,其中包括士兵。槍刑是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采用的死刑方法,有的國家除了槍刑之外,還同時保留其它方法。
6.其他方法致死。如碎身刑,就是將人的身體不規則地粉碎,常見的方法是用一個大輪盤,將人綁在輪盤上轉動,旁邊或地上有釘子、刀子之類的東西。在古羅馬,碎身刑有時也叫“耙刑”。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碎身刑的方法,但是時間較早,商代以后就不見記載。磔刑使用的是自然力將人進行肢解刑,肢解使用的是人力。古希臘、古羅馬的磔刑有時采用樹,將兩棵樹彎曲到合攏的狀態,先固定住,然后將犯人的手腳分別綁在兩棵樹上,再松開兩棵樹的繩子,樹干自行彈開的力量造成犯人身體的肢解。磔刑在中世紀被歐洲很多國家采用,使用的工具大多是馬匹。歐洲直到18世紀才取消了這一刑罰。中國在宋朝以后便不再采用磔刑。
二、影響死刑執行方式的法哲學與倫理思想
1.因果“報應”、“同態復仇”觀。人類社會之初,基于因果關系的理解,人們有了樸素的“報應”觀。從《漢謨拉比法典》對傷害他人眼睛、折斷他人骨頭、擊落他人牙齒的自由民分別處以傷害其眼、折斷其骨、擊落其齒的規定,到《摩奴法典》的“最低種姓的人以駭人聽聞的壞話,辱罵再生族,應割斷其舌”之條款,無不打上了同態復仇的烙印。古時的腰斬、五馬分尸、凌遲、斬首、絞刑等殘酷的死刑執行方式,更是承載著世人“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報應觀念。然而,社會的文明進步并沒有徹底消除人們的報應刑罰觀,從某種程度說,現代法治的文明并不是表現在徹底舍棄報應刑罰,而是體現于刑罰執行的人道追求上。
2.國民刑罰思想因素。國民刑罰思想是指國家民眾對刑罰包括其目的、價值、功能等在內的評價。國民刑罰思想是在歷史運動中形成又不斷地夾雜著傳統與風俗更新。古代“以血還血”同態復仇時代,國民中占統治地位的刑罰思想是執行死刑的方式同態與其所犯的罪。后來,雖然同態復仇在逐漸被舍棄,但占統治地位的刑罰思想還是認為執行死刑方式帶來的痛苦程度應相當于他們所犯下的罪,這種思想即使到了今天對少數人也有影響。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占統治地位的刑罰思想是執行死刑已是對死刑犯最大懲罰,實現了懲罰犯罪、預防犯罪的目的,達到了懲治犯罪人,威懾潛在犯罪人,教育普通公民的效果,因此在執行死刑時不應額外增加死刑犯的痛苦。
3.人道主義、人權觀念。人道與人權這兩個概念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密不可分。它們成為近代文明強有力的推動者,也是各國廢除死刑最重要的原因和思想基礎。當年貝卡利亞首倡廢除死刑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死刑不人道,他說“如果我要證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我就首先為人道打贏官司”。人道主義和人權觀念促成了世界將近一半的國家廢除死刑,那么它們對死刑的執行方式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當然地成為影響保留死刑的國家選擇死刑執行方式最主要的原因。從死刑執行方式的歷史沿革來看,隨著人道主義、人權觀念的傳播和影響,死刑執行方式有了較大的變化,一些減少受刑人痛苦程度的方式出現,還有多個國家嘗試注射刑,執行方式是最能體現刑罰懲罰性和人道性的,這種以盡可能減少受刑人痛苦的執行方式的發展趨勢明顯體現了行刑人道化。
三、死刑執行方式發展的趨勢
死刑是一種悠久而又最嚴厲的刑罰,它剝奪的是人的生命權。自意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利亞在其《論犯罪與刑罰》中首次倡導廢除死刑以來,人們對死刑的功能及價值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隨著報應刑觀念的革除及現代刑罰觀的確立,刑罰人道主義及刑罰輕緩化思想的深入人心,人們對死刑重新進行了價值評價。
剝奪人的生命權的方式是有多樣的,但死刑執行方式在一定時期是穩定的,但從長遠來看它是向著更符合社會需要發展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奉行刑罰“重刑化”,崇尚報復和威懾,這決定了死刑執行方式必然是殘酷、野蠻的,以制造痛苦為目的,故迎合它的便是炮烙、凌遲等酷刑。這些殘酷的行刑方式確實將死刑的威懾力提升了一個高度,這一時期的死刑可怕的不是死刑本身而是死刑的執行方式。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時代,人道主義、人權觀念深入人心,人們對生命的價值以極大的珍重,人們對死刑的畏懼已定格。對死刑犯而言,生命被合法剝奪就預示著其已經為自己的所有犯罪行為付出了代價。雖然傳統的等害報復論曾主張,刑罰應以與犯罪在損害形態上相等同為必要,但自古以來刑罰在懲處犯罪方面就具有“天然缺陷”:犯罪的損害形態是無限的,而創制刑罰的資源卻是有限的,如一個殺了10人的死刑犯,他只能以自己生命的一次終結作為代價,我們不能對其執行10次死刑,或者是通過更為殘忍的方式剝奪其生命。倘若死刑在執行方式上打上報應觀的烙印,那將與殺人犯罪無異,都是對生命倫理的破壞。因為按照犯罪行為的不同來選擇執行死刑的方式,或許實現了對不同犯罪接近等害的懲罰,但并不利于理性和正義的恢復。因為死刑的目的僅僅在于合法的結束罪犯生命,而不在于以何種痛苦的方式去結束,法律之“善”正是體現在這種結束方式的人道化,是“法律之下殺人”與“法律之外殺人”的根本區別。
在死刑的執行方式上分“三六九等”,是對生命基本倫理的蔑視。死刑的執行只在于剝奪殺人者的生命,而不能追求以痛苦的方式去剝奪。無論其行為有多么罪惡,在面臨國家安排的合法死亡時,用終結生命的殘忍去實現刑罰的報應性功能,甚至講求對犯罪的震懾效應,都是不人道的。如果采用令死刑犯十分痛苦的行刑方式實際上是在社會樹立了一種惡的榜樣,不利于防止犯罪實現刑罰功能,相反采用人道的執行方式有利于國民仁慈善良的人性,使國民強烈憎惡犯罪,有利于防止死刑,從而對發揮刑罰的功能,實現刑罰的目的具有積極的意義。特別是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起,一些還保留死刑的國家都試圖選擇人道、文明、科學簡便的執行方式。
綜上,死刑的執行方式是死刑制度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內容,每個時代都有其特點,死刑執行方式又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死刑執行方式在實現刑罰功能的同時,要尊重人權,倡導文明執法精神,為我國最后廢除死刑奠定基礎。廢除死刑已成為世界性的趨勢,死刑的廢止是人類文明的必然結果。
參考文獻:
[1]王順安.刑事執行法學[M].北京:群眾出版社,2001.
[2]胡云騰.存與廢死刑基本理論研究[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0.
[3]李云龍,沈德詠.死刑制度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
[4]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5]曾憲義主編.中國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6]何勤華.外國法制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責任編輯/彭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