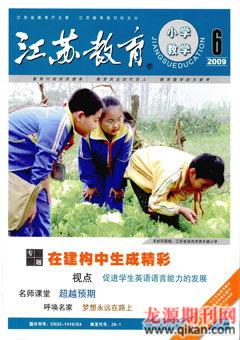慢慢走的風景
曹春華
隨著江蘇省“千校萬師支援農村教育工程”啟動和實施,2007年的秋天,我離開了生活和工作了十年有余的蘇中小鎮,來到了蘇北的一所農村小學,開始了為期半年的語文教學工作。在充分感覺到農村小學語文課堂的質樸和純真的同時,更感覺到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絕大多數的語文課,教學內容幾近等同于教材的內容,而教學的流程,僅限于文本文字表面的窄帶滑行,普遍缺乏基于文本細讀基礎上,文本意蘊的深刻發掘和重點字、詞、句、段的有效點撥。
于是,我嘗試著帶領著孩子們,放慢腳步,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出發,悄悄地走進語文這座美麗的大觀園,沿著文本細讀的思路。最大可能地引領孩子們管窺語文的應有魅力,同時也最大可能地喚醒孩子們本該具備的對語言的那份敏感。于是,便有了這一路的風景。
一、在熟悉的地方看到陌生的風景
俗話說:熟悉的地方沒有風景。或許。是因為過分的“熟悉”,作為文本之眼的課題,在人們一遍又一遍地“路過”之后,也便成了“熟悉的風景”,他們甚至確信,這短短的幾個字,一眼便能望穿,毫無“小題”大作的必要。于是,孩子們對文字的敏感,便從接觸文本伊始便被無情地削弱了。
蘇教版第十一冊的《把我的心臟帶回祖國》是我向全校語文教師公開教學的第一篇課文。我讓孩子們睜大眼睛。看我在黑板上一筆一畫地寫下“心臟”這個詞。之所以如此鄭重,是因為我要在學生的潛意識里“灌輸”“一字未宜忽”的文本細讀態度。兩個學生讀得只能算作正確。于是我說:“心臟”,可不是隨隨便便讀的,你們知道,心臟對于一個人,意味著什么?孩子們仿佛“開竅”了許多,紛紛指出了這個器官于人的重要性。我進而補充:所以,人們把心臟當作自己靈魂的所在。雖然大腦才是思維的器官,但,人們總是習慣于把自己的一切情感看成是心臟的功能,被稱為“心理”。比如,我們中國的許多表示情感的字,都是——我手指著“心”字,故意拖長了聲音,此時孩子們恍然大悟:豎心旁。我讓幾個還沒有這個“發現”的同學試著舉例。那么,我們讀這個詞還能這么輕描淡寫嗎?怎么讀?孩子們躍躍欲試。
我讓孩子們看我把課題補充完整,然后設疑導讀:把誰的心臟帶回祖國(指導突出“我”)?把“我”的什么帶回祖國(指導突出“心臟”)?把“我”的心臟帶回哪兒(指導突出“祖國”)?然后,我讓孩子們帶著自己的理解,齊讀課題。這樣,我讓孩子們“語語悟其神”的初衷終于告成了。在此基礎上,讓學生二次質疑課題,并讓學生帶著這些較為深層的問題,開始與文本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曾經聽肖川先生介紹:一位海外的中國詩人說,每當他看到“碧海、滄桑、江湖”這些漢語獨有的詞匯時,都會莫名的激動,甚至落淚。我們語文課的首要目的,不就是要培養學生對祖國語言的那份敏感嗎?不就是要不僅僅讓學生“理解”文字的字面義,更“細讀”出文字背后更加豐富的隱含義,讓學生從文字當中品味出應有的溫度嗎?“錘打”課題的預設方案就是要讓學生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閱讀”,讓學生養成從文題開始涵泳的習慣。其實,我何曾“錘打”,“令人驚訝的東西就在你身邊”,這陌生而深邃的風景,最終還是學生自己發現的。我做的。只不過放慢了腳步而已。
二、在簡略的地方看到豐賄的風景
課文文本的簡略、留白,不僅讓文本符合了美的尺度,更給閱讀者留存馳騁想象和二次創造的空間。
《把我的心臟帶回祖國》便有大量的留白。比如,在肖邦離開祖國的那個清晨,作者描寫的華沙美景只有一句:1830年11月的一天,維斯瓦河上彌漫著薄薄的霧靄。誠然,“彌漫”一詞盡得風流,然而,作為一個天才的藝術家,在他與祖國生離死別的時刻,他應該多么想多看一眼這多情的土地,多么想把祖國的山山水水、花草鳥獸看個夠!
師:這是深秋的一個清晨。馬鞭在晨霧中清脆地響起,馬車駛出了。馬兒啊,你慢些走,讓我多看一眼這土地吧!
師:透過這薄薄的霧靄。肖邦看到,河岸邊——
生:楊柳依依。
生:小草上露珠晶瑩。
生:鮮花盛開。
師:你看到了,肖邦的眼睛——
生:睜得老大老大。
生:充滿了眷戀。
生:充滿了淚水。
師(疑惑地):為什么?
生:因為。現在這美好的祖國已經不是波蘭的了,有十分之九的領土都落到了沙皇俄國的手里了。
師:是啊,“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為什么在肖邦的眼里,祖國這么美啊!
生(齊):他熱愛自己的祖國!
“一切景語皆情語。”景色的美,緣自肖邦的愛。那是寫在肖邦的眼神里,也彌漫在肖邦的神思里的。學生這樣豐富的想象和感受,不僅為下文贈別的學習鋪墊了情感基調,更讓學生在腦海中開始建立起一個豐滿而立體的肖邦形象。
孫紹振教授在《名作細讀》中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語文課堂上重復的都是學生一望而知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語文教學的效率怎么不會低下,學生對閱讀的興趣和熱情又怎么能維持?閱讀指導的價值便在于教師有價值的指導。對學生而言,“一望而知”的是文本文字構成的表象,而“一無所知”的則是文本間的“空白”。閱讀中缺少了設身處地的想象,個體生命的體驗,閱讀便失去了生命。
三、在平淡的地方看到馥郁的風景
《牛郎織女》,這是一個古老的故事,可以說家喻戶曉,但民間故事成為語文的教學文本,我們便絕不能僅僅把它看成一個神奇的故事。
我將教學的基本思路定為“走進故事。走近人物”,教學立意確定為:建立“(牛郎)無限相信愛的力量”和“(織女)不懈追求心靈的自由”的人文高度。具體的教學設想為:通過引導學生走進文本,設身處地體會人物的境遇,深入把握牛郎和織女等人物的性格,深切關懷人物命運,學會走進人物內心的深度閱讀方法。
為了讓這個故事活起來,在第一課時,我運用在文本細讀中常用的“分析”方法,抓住文中的兩個“最”字,并分三個層次進行鋪陳:一是放大選擇“最好的草地”和“最干凈的溪水”的過程;二是聚焦此時牛郎腹內饑身上寒的狀態;三是放眼這不是偶爾為之,而是“每天”如此。另外,為了讓牛郎的形象在孩子們的眼前豐滿起來,我采用角色假想的方法,讓學生作牛郎的代言人,讓牛郎“心眼好”的選擇成為學生自己的選擇,讓“無限相信愛的力量”成為學生自己的發現。
經常能觀摩到故事類課文的教學,大家的主要精力總放在情節的梳理和人物性格的提煉上。而一節課下來,人物的形象卻那么單薄,教學也缺少了一種因故事本身而產生的動人的力量。劉勰《文心雕龍》有云:“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也就是說,“文”與“質”本是一體,在教學中我們便遇到了把誰放在首位的問題。“文本中的語言是沉默著的。”故事類課文的教學目的,恐怕求索“質”的微言大義倒是其次,而在
于引領學生走進構成這個故事的“文”,在貌似平淡的文字里,觸摸到異常的溫度,從而情動于衷,而對“質”的求索也在此過程中水到渠成。換句話說,語文的教學,我們首先要做的不是“抽象概括”,而是“鋪陳演繹”。在細節的生長中,課堂變得豐富醇厚,彌漫著馥郁的芬芳。
從理論上說,一篇課文文本的意蘊是無法窮盡的,就像那無垠的藍天,但“重視體會作家的原意不應該離開文本,而是必須從文本出發,同時重視詞句的客觀意義。”(王先霈《文學文本細讀講演錄》)人們盡可以憑借著閱讀的前見和自己的想象,憑借著文本,便能無限地逼近文本,無限地懷想文本的天空。閱讀教學的過程,就是讓孩子在閱讀實踐中逐步掌握打開閱讀之門的這把帶有明顯個性色彩的鑰匙,讓自己的視閾從模糊逐步走向清晰,從粗糙逐步走向細膩,從而“在主動積極的思維和情感活動中,加深理解和體驗,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獲得思想啟迪,享受審美樂趣”(《語文課課程標準》),從而積累起無比美妙的閱讀經驗。
老舍的散文名篇《草原》是蘇教版教材選進的一篇“新”課文,課文情景交融,充滿詩情畫意,但這種帶著作家強烈個性色彩的文章,對語文教學來說,卻是個挑戰。如何突破難點,將學生帶進那一望無垠的草原。分享老舍先生那獨特的體驗呢?如果我在自己的家鄉,或許給學生放上一段錄像,展現幾幅圖片,便能解決問題,但這兒的教室沒有電腦,更沒有“班班通”的上網環境,怎么辦呢?我相信身在農村的孩子,經常會見到無垠的田野,只要喚起孩子們相似的“前見”經驗,適時引導孩子們展開豐富的想象,是可以深入理解和感受這些文字的。
師:那“只用綠色渲染,不用墨線勾勒的中國畫那樣”是一種什么感覺?
生:無窮無盡的綠色,鋪天蓋地,都像要跑出去了。
生:那么明亮的綠色,一直鋪向遠方,整個綠色草原上都裝不了了。
師:是啊,那綠色向周圍擴散、滲透、流動。請你們輕聲再讀“輕輕流入云際”這句話,看看這“翠色欲流,輕輕流入云際”是一幅怎樣的畫面。
生:此時此刻,草原和天空像是融合在一起,到處是那樣的鮮亮、充滿生機。
生:我覺得這草原就像綠色的波浪一樣連綿起伏,涌向遠方,消失在天際。
師:真是碧草與藍天一色呀。老師也想讀一讀!(教師范讀)
師:是呀,這哪里是綠色在流動,這分明是生命的泉水在流淌。(指板書)難怪老舍先生說“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我們讀書就要這樣去讀,不僅要讀懂文字表面的意思。還要用心去感悟、用情去體驗、用想象去補充,讀出文字背后蘊含著的意思。
學生對文本難點的突破是應該站立在教師文本細讀的“肩膀”上的。他們理當分享前人(教師)業已積累起來的閱讀經驗。否則他們對文本作品的閱讀永遠是“第一次”。我們無法估量閱讀過程中一個個難點對學生閱讀能力提升的作用。這些閱讀的難點,便如“藍空天末,搖搖欲墜的孤星”,仿佛近在眼前,卻遙不可及,仿佛一眼便能洞穿,卻撲朔迷離,或許你可以選擇繞開,以一種不求甚解的姿態選擇逃避,但,當你直面這些難點,進而竭盡所能突破以至超越,那不意味著一個階段性的勝利?一個個小小的坡度才積累起閱讀階段性的高度,當你攀登上這個高度時,那種“舉頭紅日近。回首白云低”的風景是何等美妙。
語文課程標準確定了小學階段課外閱讀不少于百萬字的課程目標,這無論對農村教師還是農村孩子來說都是極大的挑戰。要讓孩子駛上閱讀的快車道,課堂教學責元旁貸,對課文中一個個難點的超越,便組成了學生閱讀能力成長路程上的一個個“關鍵幀”。這些“藍空天末的孤星”在孩子眼中一次又一次地從模糊到清晰的過程中,我們是不是能凝神諦聽到孩子閱讀生命欣然拔節的美妙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