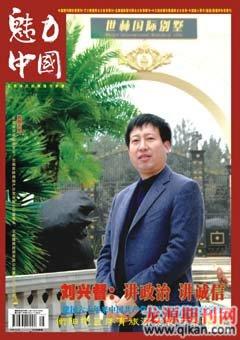淺析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原因
楊社論 李冰克
中圖分類號:D068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1673-0992(2009)05-019-04
摘要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英國面對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擴(kuò)張的咄咄逼人攻勢,采取了姑息、縱容、妥協(xié)退讓的綏靖政策。這與英國經(jīng)濟(jì)實(shí)力的衰退、和平主義思潮的影響以及傳統(tǒng)外交政策的影響是密不可分的。
關(guān)鍵詞:靖政策;經(jīng)濟(jì)勢力;和平主義思潮 ;均勢政策
“綏靖”(Appeasement),就其本義來說,有“講和、調(diào)解”、“安撫、平息斗爭”以及“用滿足要求的辦法來息事寧人”。在外交史中,“綏靖政策”(Appeasement Policy)專指“對侵略者姑息、遷就,用犧牲他國利益以至本國領(lǐng)土、主權(quán)等利益,乞求和平的政策”。20世紀(jì)30年代面對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擴(kuò)張,英國無論是麥克唐納政府(1931-1935)、鮑爾溫政府(1935-1937),還是張伯倫政府(1937-1940)均采取了綏靖政策。那么,一個(gè)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緣何會采取這樣姑息、縱容、妥協(xié)退讓的綏靖政策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試從“經(jīng)濟(jì)軍事實(shí)力、社會心理(和平主義思潮)及傳統(tǒng)外交政策”三方面來對英國綏靖政策的出臺進(jìn)行剖析。
一、經(jīng)濟(jì)軍事因素:
英國雖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勝國,但其力量受到了相當(dāng)大程度的削弱:戰(zhàn)爭中,英國軍費(fèi)開支逾100億英鎊,國民財(cái)富損失1/3,商船損失70%,出口貿(mào)易減少了一半;戰(zhàn)后國內(nèi)債務(wù)近80億英鎊,由戰(zhàn)前世界最大的債權(quán)國變成了債務(wù)國,欠美國47億美元,世界金融中心也由倫敦轉(zhuǎn)移到美國紐約。
戰(zhàn)后英國經(jīng)濟(jì)增長緩慢,而1929-1933年世界范圍的經(jīng)濟(jì)危機(jī)又使尚未恢復(fù)的英國遭受到沉重的打擊,英國的經(jīng)濟(jì)下降到最低點(diǎn)。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縮減,英國成了世界各國傾銷剩余糧食的市場;本已嚴(yán)重的失業(yè)狀況進(jìn)一步惡化,失業(yè)人數(shù)成倍增長;對外貿(mào)易進(jìn)一步萎縮,貿(mào)易入超逐年增加,國際收支惡化;社會危機(jī)加深。 經(jīng)濟(jì)實(shí)力的衰退,導(dǎo)致了軍費(fèi)的嚴(yán)重不足。1933-1938年,英國軍費(fèi)開支為12億英鎊,同期德國為28.6億英鎊,蘇聯(lián)為28.08億英鎊,日本為12.6億英鎊。1934-1938年間,英國軍費(fèi)開支增長率為25%,同期德國的增長率為47%,前蘇聯(lián)為37%,日本為45%。
經(jīng)濟(jì)的衰退和勢力范圍的日益瓦解加劇了英國國內(nèi)的政治動蕩,統(tǒng)治集團(tuán)內(nèi)部爭吵不休,內(nèi)閣更迭猶如走馬燈。從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七年,英國五次更換首相。
上述情況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由于英國損失慘重,加之深受經(jīng)濟(jì)危機(jī)的影響,使英國在數(shù)個(gè)世紀(jì)內(nèi)建立起來的霸權(quán)地位受到了威脅,英國實(shí)力嚴(yán)重衰退。而實(shí)力是主權(quán)國家外交政策的基礎(chǔ)和保證。國力的虛弱、戰(zhàn)備的松弛使英國在外交活動中無力采取強(qiáng)硬的態(tài)度,只有對法西斯國家妥協(xié),才能保衛(wèi)自己的國土安全和維護(hù)既得利益。因此,實(shí)力的衰退是英國推出綏靖政策的根本原因。張伯倫稱自己的對法西斯國家推行的戰(zhàn)略是“絞盡腦汁找到的一種災(zāi)難臨頭時(shí)避免災(zāi)難的辦法”,對此,英國史學(xué)家基思·米德爾馬斯評論道:“1938年張伯倫政府所規(guī)定的綏靖政策,通常被視作英國虛弱之極的標(biāo)志,是英國困難處境的一種必然結(jié)果”。
二、和平主義思潮的影響:
20世紀(jì)30年代一戰(zhàn)可怕的陰影還沒有在人們頭腦中消失,德意法西斯的戰(zhàn)爭氣味就已穿過英吉利海峽彌漫到了英倫三島,心有余悸的英國人特別害怕再發(fā)生一次世界大戰(zhàn),再加上經(jīng)濟(jì)危機(jī)所帶來的失業(yè)和恐慌,使英、法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流行一種強(qiáng)烈的和平主義思想。尤其是勞動人民要求和平,希望能在寧靜的環(huán)境中生活。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國內(nèi)的和平主義運(yùn)動有了很大發(fā)展。各種和平社團(tuán)都認(rèn)為,英國應(yīng)“為爭取和平而冒險(xiǎn)”,“大不列顛不應(yīng)忽視任何一個(gè)促進(jìn)和平的機(jī)會”。即使在英國海軍喪失了海上霸權(quán)后,國內(nèi)的輿論還一致要求進(jìn)一步縮減其已經(jīng)縮減過的武裝力量。他們希望通過國際仲裁辦法的推廣,通過國際聯(lián)盟的活動來實(shí)現(xiàn)世界和平。當(dāng)時(shí)“沒有一個(gè)人否認(rèn)英國人不惜以裁減軍備以至危及國防的程度來樹立一個(gè)好榜樣”。和平主義運(yùn)動的初步興起就為綏靖政策的產(chǎn)生提供了強(qiáng)有力的輿論和社會環(huán)境。
1935年,納粹德國重整軍備,公開走上擴(kuò)軍備戰(zhàn)的道路,歐洲的戰(zhàn)爭威脅日益長,而英國的和平主義運(yùn)動法也達(dá)到了高潮。1934年11月,英國39個(gè)和平團(tuán)體提出全面裁軍和廢除航空部隊(duì)的主張,還要求用非軍事性和經(jīng)濟(jì)制裁的方法來阻止戰(zhàn)爭爆發(fā)。“和平民意測驗(yàn)”的結(jié)果表明,大多數(shù)英國人都反對戰(zhàn)爭,希望通過加強(qiáng)國聯(lián)、經(jīng)濟(jì)制裁等方法維護(hù)和平。在民眾和輿論的壓力下,英國各派領(lǐng)導(dǎo)人紛紛以和平擁護(hù)者的形象出現(xiàn)。這也就影響了政府的外交政策。美國國際政治學(xué)家杰里爾?A?羅賽蒂通過輿論對外交的分析,認(rèn)為“從許多問題來看,功能公眾輿論對決策過程幾乎沒有什么迅速和直接的影響,如果有也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從另一些問題來看,特別是極為突出的問題,公眾輿論對政府中的決策人,包括總統(tǒng)和國會議員,都有著迅速而直接的影響”。1935年7月,帝國國防委員會在一份報(bào)告中說:“應(yīng)該抓住一切機(jī)會盡可能長久地避免戰(zhàn)爭風(fēng)險(xiǎn)。和平主義運(yùn)動的一步步發(fā)展使得英國上下急切盼望能保住英聯(lián)邦的既得利益,從而在全球內(nèi)奉行一條維持現(xiàn)狀、避戰(zhàn)求和的外交路線。綏靖政策的產(chǎn)生在英國非張伯倫政府的偶然為之,《慕尼黑協(xié)定》實(shí)質(zhì)上簽下的是千萬英國民眾的姓名!正如英國史學(xué)家梅德利科特所說的“對于絕大多數(shù)的英國人來說,維護(hù)和平主義意味著避免任何導(dǎo)致戰(zhàn)爭的政策”。
事實(shí)證明,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撕毀慕尼黑協(xié)定,吞并整個(gè)捷克斯洛伐克以后,英國人民幡然醒悟,和平主義江河日下,避戰(zhàn)求和的綏靖政策也隨之付諸東流。可以說,在一定條件下,和平主義為綏靖準(zhǔn)備了某種思想基礎(chǔ),和平主義所造成的軍備不足又為綏靖提供了某種物質(zhì)基礎(chǔ),而深受和平主義愚弄的群眾則構(gòu)成了綏靖的某種社會基礎(chǔ)和心理基礎(chǔ)。這就是三十年代強(qiáng)大的和平主義思潮對二戰(zhàn)前夕英國外交政策的影響。
三、傳統(tǒng)外交政策的影響:
綏靖政策主要是作為一種外交政策而出現(xiàn)在英國政府的決策中的,而這一決策又是與英國傳統(tǒng)的外交政策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說是英國傳統(tǒng)外交政策延續(xù)的結(jié)果。
英國外交的重心一向在歐洲,運(yùn)用均勢政策使各大國始終處于力量均衡或近于均衡的狀態(tài)。作為一個(gè)世界大國,“勢力均衡”的舊傳統(tǒng)和“光榮孤立”的影子使英國始終定位在充當(dāng)歐洲的制衡者和仲裁人。一戰(zhàn)后,歐洲與世界格局發(fā)生了重大改變。德國戰(zhàn)敗,它對英國及歐洲大陸的威脅解除;而掌握著歐洲一流陸軍的法國則一時(shí)成為歐洲大陸上的唯一強(qiáng)國,法國是現(xiàn)在唯一有可能對英國造成麻煩的國家。因此,此時(shí)英國軍是政策的特征表現(xiàn)為“扶德抑法”。而戰(zhàn)后新生的社會主義前蘇聯(lián)的崛起更使英國感到,要保持歐洲大陸勢力的平衡并相互制約,就必須采取一種“扶弱抑強(qiáng)”的新的歐陸均勢政策。于是,英國選擇了徹底戰(zhàn)敗的德國作為扶助的對象,在戰(zhàn)后一系列關(guān)于德國問題的處理上,英國總是傾向于德國。
但是任何一種外交政策地實(shí)施,都必須以強(qiáng)大的實(shí)力為后盾,英國經(jīng)濟(jì)軍事實(shí)力的衰退和國際地位的降低使其無力保證均勢政策的實(shí)施。因而,面對德、意法西斯的威脅只能妥協(xié)退讓,進(jìn)而綏靖。另一方面,由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的根本對抗,面對俄國十月革命后世界各地掀起的反對殖民統(tǒng)治的民族解放運(yùn)動帶給西方列強(qiáng)統(tǒng)治體系和殖民地的巨大沖擊,西方列強(qiáng)都非常仇視新生的前蘇聯(lián),對共產(chǎn)主義威脅惶恐不安,千方百計(jì)地削弱前蘇聯(lián)和限制共產(chǎn)主義的影響。鑒于德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日益反蘇的傾向,英國等西方國家為阻止前蘇聯(lián)的影響,把德國當(dāng)作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屏障。如果把法西斯這股禍水引向前蘇聯(lián),使蘇德之間發(fā)生沖突,彼此在戰(zhàn)爭中兩敗俱傷,那么英國的霸權(quán)和利益就能安然無恙,歐洲均勢將得到更大程度的鞏固。綏靖政策也因此被更加廣泛的應(yīng)用——“扶德抑法”、“禍水東引”。在德國法西斯大步緊逼的情況下喪失聯(lián)合前蘇聯(lián)、法國齊力對付法西斯德國肆虐的大好時(shí)機(jī),導(dǎo)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過早爆發(fā)。
綜上所述,筆者認(rèn)為,導(dǎo)致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原因是實(shí)力的衰弱、深層的社會心理以及傳統(tǒng)的外交政策的影響。三種因素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終使英國扛起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綏靖主義的白旗,首相張伯倫則是這面白旗的親手升起者。歷史證明,英國推行的綏靖政策不僅不能維護(hù)和平和既得利益,反而助長了法西斯的侵略擴(kuò)張,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這是一個(gè)重大的戰(zhàn)略錯(cuò)誤。正如齊世榮先生所說:“英國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但張伯倫之流的愚蠢政策則加深了衰落的過程”。而只有“以戰(zhàn)止戰(zhàn)”、“以戰(zhàn)去戰(zhàn)”,才能制止或推遲戰(zhàn)爭的爆發(fā),并且在戰(zhàn)爭爆發(fā)后,才不至于束手無策,被動挨打,甚至徹底投降,或付出其他沉重的代價(jià)。
參考文獻(xiàn):
[1]牛津英語詞典[Z].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77.
[2]錢其琛.世界外交大辭典(下)[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3]方連慶,王炳元,劉金質(zhì).國際關(guān)系史(現(xiàn)代卷)[M].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第1 版
[4]基思·米德爾馬斯.綏靖戰(zhàn)略[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
[5]羅賽蒂.美國對外政策的政治學(xué)[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
[6]王繩祖.國際關(guān)系史?第五卷(1929-1939)[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
[7]《商君書·畫策》,“以戰(zhàn)去戰(zhàn),雖戰(zhàn)可也”
[8]齊世榮.綏靖政策研究[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