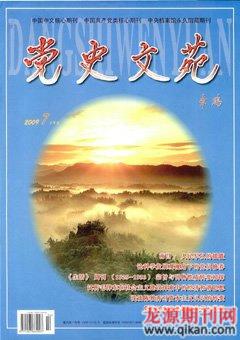《生活》周刊(1925—1933)宗旨與刊物性質轉變初探
趙 文
[摘 要] 《生活》周刊是主要由鄒韜奮主持的民國時期的一份著名雜志,經歷了從中華職業教育社機關刊到都市通俗文化生活雜志再到時事政治周刊的發展轉變,是民國時期影響最大的雜志之一。刊物適應社會需要,始終立足民眾立場,真誠為讀者服務,勇于創新,緊跟時代前進。
[關鍵詞] 《生活》周刊 宗旨 刊物性質 轉變
《生活》周刊1925年10月11日由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于上海,1933年12月16日被國民黨政府以“言論反動、思想過激、毀謗黨國”的罪名查封。對于《生活》周刊,目前學界研究的還不多,對其宗旨和性質亦存在不少誤解。本文將根據史實,初步厘清、闡明《生活》周刊宗旨與性質發展轉變的過程及原因。
一、《生活》周刊作為機關刊創辦的背景和經過
有關《生活》周刊創辦的背景和經過,鄒韜奮在其著述中有較詳細的記載:“當時職教社原有一種月刊叫做《教育與職業》,專發表或討論關于職業教育的種種問題,但是該社同人覺得月刊要每月一次,在時間上相隔得比較的久一些,只宜發表理論或有系統的長篇事實;為傳布職業教育的消息起見,有創辦一種周刊的必要:這是最初創辦《生活》周刊的意旨。”[1]“主筆原來應該由編輯股主任擔任,但因為我太忙了,所以公推新由美國學成回國的王志莘先生擔任,文章由職教社同人幫忙,發行的事情由當時還在職教社做練習生的徐伯昕先生兼任。”[2]
由上可見,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生活》周刊的初衷,確實是要將其作為機關刊,用來宣傳職業教育、發布職教信息的。但在實際創辦時,《生活》周刊的宗旨卻受了黃炎培“大職業教育主義”的影響。20年代中期,為了走出職教事業發展的困境,黃炎培提出,“辦職業學校的,須同時和一切教育界、職業界努力的溝通和聯絡;提倡職業教育的,同時需分一部分精神,參加全社會的運動。”[3]這些主張就是所謂“大職業教育主義”。在其指導下,實際創辦后的《生活》宗旨主要是“促使人們關心各類社會現實生活問題,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以為實施職業教育的依據。”[4]
黃炎培在《生活》周刊《創刊詞》中揭示刊物的宗旨時寫道:“世界一切問題的中心,是人類;人類一切問題的中心,是生活。”“求生活不得,是一大問題;不滿足于其生活,亦是一大問題。物質上不滿足,而生活窮困,窮困之極,乃至凍餓以死,今既時見之矣。精神上不滿足,而生活愁悶,愁悶之極,乃至自殺,今又時聞之矣。……吾鑒夫此問題意味之日益嚴重,與其范圍之日益廣大也,欲使有耳,耳此,有目,目此,有口,口此:合力以謀此問題之漸解,作《生活》。”而《生活》周刊一卷2期“編輯者言”說明該刊編輯旨趣為:“同人信生活是受環境支配的。欲解決生活問題,須先研究已存立社會的生活,所以本刊愿揭出社會上困苦和快樂的生活實況。同人信生活是循一定方向進行的。欲希望生活進行的順利,須先研究人類生活之目的,所以本刊愿揭出人類生活正當的途徑。同人信生活可以用人力去改換的。欲改善生活,須先研究應當致力之點,所以本刊愿揭出改善人類生活的方法。”
不過,雖然創刊后的《生活》決定以探討和解決社會生活問題為主旨,但從何處著手參與社會生活問題的解決?以怎樣的方式促進社會改良?刊物的讀者定位、未來發展方向如何?這一系列的問題在創刊之初并未得到明確,也未能很好地加以解決。加之,《生活》的創辦者中華職業教育社是一個民間教育團體,其活動經費主要來自工商及社會各界的捐助,對于《生活》的資助與扶持有限。因此,第一卷時期的《生活》,發展較為艱難,刊物銷路不暢,影響不大,只能勉力維持、支撐。鄒韜奮回憶說,“當我接辦的時候,它的每期印數約有二千八百份左右,贈送的居多”[5]。那時的《生活》還是個“怪可憐似的”“零仃孤苦的孩子”[6]。
二、鄒韜奮主持下的《生活》周刊轉變為都市通俗文化生活雜志
1926年第二卷起,鄒韜奮開始接辦《生活》周刊。為了落實“大職業教育主義”指導下的辦刊宗旨,“研究社會生活及經濟之狀況。以為職業教育設施之根據。并指導青年從事正當生活之途徑”[7]。在他的主持下,刊物逐步由職教社機關刊轉變成為都市通俗文化生活周刊,成為一份“名副其實”探討和研究“生活問題”的雜志。
1927年3月27日,《生活》二卷21期刊載鄒韜奮《民眾與本刊——本刊動機的重要說明》一文。文章指出,《生活》的主要讀者和服務對象是“一般有正當職業或正在準備加入正當職業的平民”。并明確宣布,“本刊的動機完全以民眾的福利為前提,今后仍本此旨,努力進行……容納民眾之意見,使本刊對于民眾有相當的貢獻”。1927年8月8日,鄒韜奮在為《<生活>第一卷匯刊》撰寫的弁言中揭示《生活》旨趣為:“本刊期以生動的文字,有價值有興趣的材料,建議改進生活途徑的方法,同時注意提醒關于人生修養及安慰之種種要點,俾人人得到豐富而愉快的生活,由此養成健全的社會。”1929年年初,鄒韜奮將“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確定為《生活》周刊的宗旨。[8]從1929年12月1日《生活》五卷1期起,這個宗旨被印在了雜志的刊頭上。
為滿足市民大眾的日常生活需要和文化心理需求,鄒韜奮接辦《生活》后,銳意革新,注重刊物的市民性、通俗性、趣味性,力求以市民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與其交流溝通。刊物新增、新辟了不少新內容、新欄目,如根據讀者要求開設了“讀者信箱”,新增“國外生活概況”“小新聞”“小言論”等欄目,還從二卷12期起使用照片、插圖、漫畫等以增加刊物的趣味性……這就是鄒韜奮后來所說的,“我接辦之后,變換內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評論和‘有趣味有價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欄討論讀者所提出的種種問題。對于編制方式的新穎和相片插圖的動目,也很注意。所謂‘有趣味有價值,是當時《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個標語”[9]。
從第二卷起,《生活》的旨趣已逐漸指向城市平民的日常社會生活。刊物的具體內容從職業生活擴展到家庭社會生活,從國內生活擴展到國外生活,從職業生活、職業修養擴展到人格修養、社會家庭生活的指導與改良。這樣,從個人角度出發,切入城市平民求學、擇業、婚戀等具體生活問題,并進行適當的討論、引導,使《生活》反映生活,改造生活,進而改良社會的努力落在了實處。《生活》由此穩步地由職教社機關刊向都市通俗文化生活雜志過渡。
第三卷《生活》繼續謀求市民大眾的生活改進,以社會改造為己任,關注、探討和解決的生活問題更加集中于戀愛婚姻、大家庭的改造和移風易俗等方面。在語言文字上更加通俗化。三卷中幾乎已無文言文章,詩歌也以新詩、白話詩為主。第三卷《生活》結束時,周刊每期發行已從2萬份增至4萬份。每日收到讀者來信商榷各種問題的,平均總在四五十封以上。[10]這些情況說明,《生活》第三卷已初步完成了由職教雜志向都市通俗文化生活雜志的轉型。
第四卷《生活》進一步明確了刊物都市文化生活周刊的定位,嚴格遵循“由協助個人而促進社會的改進”的辦刊宗旨,刊物欄目更加豐富,內容也更為生動活潑。新的欄目內容有“世界上的破天荒”“時論粹語”“介紹好讀物”“健而美”等。其中“健而美”欄目圖文并茂,吸引了不少青年讀者。本卷國外通訊大幅增加,海外特約通訊記者李公樸、徐玉文、凌其翰、程滄波等為《生活》撰寫了大量“有價值有趣味”的海外見聞。“讀者信箱”中讀者征詢、探討生活問題的來信激增,至1929年6月每日達100多封。[11]《生活》在為讀者真誠的服務中真正地融入了生活,融入了社會實際。此時的《生活》更富趣味性、通俗性,同時雅俗共賞,宗旨純正,頗為讀者稱道。讀者劉俊生評價說:“國內刊物,非失之莊,即失之陋。莊則枯索乏味,陋則鄙邪誨淫,有損道德。未有能如貴刊者,其發展普及,自意中事也。”[12]嚴礪平也稱贊所:“貴刊宗旨高尚,筆墨潔凈,對于惡習慣極盡諍言,描寫社會消息,毫不輕薄,字里行間,常含有一種君子的態度,真不愧為有趣味有價值的周刊。”[13]顯然,第四卷《生活》已被市民大眾廣為接納與認可,成功地轉變為都市通俗文化生活雜志。
三、《生活》最終演變成為一份著名的進步時政雜志
成功轉型為都市通俗文化生活雜志后,《生活》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第五卷起,《生活》改版為本子樣式,篇幅增加至每冊20頁。刊物銷數達8萬份,廣告客戶及收入激增。[14]在強手如林的上海報界,《生活》周刊已從一份貌不驚人的四開小報,發展成為一份享譽海內外的都市文化生活雜志,銷量位于上海雜志第一位。[15]也正是在此時,《生活》的宗旨內容與刊物性質又開始了新的轉變。
《生活》五卷40期《腦際中所亟謀解決者》一文稱,“本刊內容的最近趨勢既注意于時事或現代社會問題的評論……無論對于任何事實,要根據理性作分析的批評,俾國人養成對任何問題均具有分析研究的態度,辨別是非的能力,并時附積極方面的建議,以供國人參考”[16]。1930年12月13日《生活》六卷1期《我們的立場》一文進一步明確,刊物“依最近的趨勢,材料內容尤以時事為中心,希望用新聞學的眼光,為中國造成一種言論公正評述精當的周刊”。
促使《生活》再次發生轉變的原因何在?筆者以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鄒韜奮主持下的《生活》周刊,從他接手起就堅定地立足于民眾立場,堅信“真有生命力的刊物,和當前時代的進步運動是不能脫節的”[17]。始終用“敏銳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誠摯的同情,研究當前一般大眾讀者所需要的是怎樣的‘精神糧食”[18],并據此來不斷調整自己的辦刊宗旨和期刊定位。
鄒韜奮接手《生活》伊始,北伐戰爭剛開始不久。對此,他曾寄予厚望,希望中國藉此能夠統一,結束軍閥混戰的政治局面,按照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建設新中國。然而,隨后的現實讓他失望了。國民黨當權以后,黨國要人們一樣地爭權奪利、禍國殃民。中國依舊貧窮落后,人民照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無情的現實迫使鄒韜奮反思“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的辦刊宗旨。
鄒韜奮的摯友畢云程在《鄒韜奮先生五周年祭》中回憶說:“問題漸漸嚴重起來了,因為當時政治上的日益黑暗和日益反動,引起許多青年的不滿,他們的來信,便好象迫擊炮一樣接連不斷的壓迫著《生活》周刊,壓迫著先生要求提出關于政治問題的解答。這一種群眾的精神上的苦悶要求著壓迫著先生不能不談政治問題。而先生辦刊物的精神是以讀者大眾的利益為本位的。因此,先生雖然不是一個專門研究政治的人,而這一股強大的四面八方的各式各樣的青年讀者們熱情而懇摯的來信,終于迫著他不能不研究政治了。”[19]這種來自大眾的壓力和現實的教訓,轉變了鄒韜奮的思想,也使《生活》隨之改變了它的宗旨和性質。在《經歷》一書中,鄒韜奮寫道:“也許是由于我的個性的傾向和一般讀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漸漸轉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對于黑暗勢力不免要迎面痛擊……不但如此,《生活》周刊既一天天和社會的現實發生著密切的聯系,社會的改造到了現階段又決不能從個人主義做出發點;如和整個社會的改造脫離關系而斤斤較量個人的問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應著時代的要求,漸漸注意于社會的問題和政治的問題,漸漸由個人出發點而轉到集體的出發點了。……后半期的《生活》周刊的新的進展也漸漸開始了。”[20]
從《生活》明確宣布要成為“一種言論公正評述精當的周刊”開始,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大致相當于第六卷《生活》時期),《生活》針砭時弊的言論明顯增多。它對各帝國主義尤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侮辱我國人民的暴行表示憤慨和抗議,對在黑暗社會中痛苦掙扎的“小人物”給予深切的同情與關注,同時憤怒揭發和抨擊國民黨黨治下的種種黑暗,以及達官貴人、貪官污吏等害國害民的各種丑行。這些言論表明,《生活》周刊正由都市通俗文化生活雜志向時事政治雜志轉變。
“九一八”事變爆發,中華民族面臨著嚴重的危機。而國民黨政府對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實行不抵抗主義。面對危難時局,《生活》高舉抗日救國旗幟,積極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它用大量事實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殘暴行徑和妄圖滅亡中國的狼子野心,抨擊賣國投降的不抵抗主義,鼓舞與堅定廣大民眾抗日救亡的信心和意志。“九一八”事變使《生活》周刊的宗旨和性質進一步朝進步時政雜志的方向演變。此后,《生活》基本以抗日救亡,喚起民眾政治覺醒為宗旨和中心內容,刊物宗旨、性質日趨左傾進步,最終演變成為一份著名的進步時政雜志。
1932年1月9日《生活》七卷1期發表《我們最近的思想和態度》一文,正式宣布“本刊最近已成為新聞評述性質的周刊”。在文中,《生活》明確表示,“反對少數特殊階級剝削大多數勞苦民眾的不平行為”,“深刻認識剝削大多數民眾以供少數特殊階級享用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終必崩潰;為大多數民眾謀福利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終必成立”[21]。1932年7月2日《生活》七卷26期《我們最近的趨向》一文再次重申,“中國乃至全世界的亂源,都可歸結于有榨取的階級和被榨取的階級,有壓迫的階級和被壓迫的階級,要消滅這種不幸的現象,只有社會主義的一條路走,而絕非行將沒落的資本主義和西洋的虛偽民主政治的老把戲所能挽救。所以依客觀的研討,中國無出路則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會主義的這條路”。顯然,此時《生活》的宗旨立場已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發生了質的躍進,轉進至革命的民主主義,并且開始向馬克思主義靠攏。從1932年下半年起,《生活》七、八兩卷刊載了大量介紹蘇聯情況的文章。如《庶聯訪問記》、《蘇俄的工人生活近況》、《蘇聯教育的新轉變》、《五年計劃的成果》等。同時,刊發了一系列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如《什么是辯證法》《階級是什么》《反帝的主要隊伍》《什么是革命》《論真理》《論國家》《個人與社會》《論小資產階級》等,對要求進步的讀者進行革命啟蒙。
《生活》宗旨和性質的進一步轉變,使《生活》事業的發展達到了新的高度。“九一八”事變后,《生活》周刊的每期銷量增加至12萬份,其中1931年“國慶與國哀”特刊的發行量高達15.5萬份,創當時報刊發行的最高紀錄。[22]但也正因為此,日益激進左傾,社會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大的《生活》,遭到了國民黨政權的忌恨與壓制。1932年7月,在國民黨的壓迫下,鄒韜奮被迫流亡海外。1933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最終被國民黨政府以“言論反動、思想過激、毀謗黨國”的罪名查封。[23]
縱觀《生活》周刊宗旨變化與刊物性質轉變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王志莘主持下的第一卷《生活》作為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機關刊物,以反映和探討解決職業生活、職業修養等問題為主要旨趣。鄒韜奮接辦《生活》后,適應讀者和社會需求,銳意變革,對刊物進行了改進。從第二卷至第四卷,逐漸演變為都市通俗文化生活雜志。從第五卷起,《生活》開始了新的轉型,向時政新聞周刊轉變,逐漸以針砭時弊,揭露社會黑暗,探討國家民族前途出路為主旨。“九一八事變”后,《生活》完成了雜志宗旨和性質的第二次轉變,演變成一份以宣傳抗日救亡、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喚起民眾政治覺醒為宗旨和內容的進步時政雜志。促使《生活》宗旨、內容與性質成功轉變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鄒韜奮及其主持的《生活》能夠始終如一地堅持進步向上的出版方向,堅持為最大多數讀者群眾服務。它是刊物一貫立足民眾立場,真誠為讀者服務,適應社會需要,勇于創新,緊跟時代前進的必然結果。而《生活》宗旨、內容與刊物性質的及時調整、準確定位和與時俱進,也促成了《生活》周刊的迅速崛起與成功發展。○
參考文獻:
[1][5]《韜奮全集》第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91-192、197-198頁。
[2]鄒韜奮:《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附錄一:生活史話),學林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3]黃炎培:《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征求同志意見》,《教育與職業》第71期,1926年1月。
[4]《〈生活〉周刊第一期出版》,《申報》1925年10月11日。
[6][9][17][20]鄒韜奮:《韜奮自述》,學林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71、73、87、78頁。
[7]《〈生活〉周刊已出版第一期送閱》,《申報》1925年10月13日。
[8]鄒恩潤:《十年來之中國職業教育出版物》,《教育與職業》第100期,1929年1月。
[10]編者:《<生活>周刊究竟是誰的?》,《生活》周刊第4卷第1期,1928年11月18日,總第2頁。
[11][22][23]錢小柏、雷群明編著:《韜奮與出版》,學林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197、197-198、199頁。
[12]劉俊生:讀者信箱《意中事》,《生活》周刊第2卷第25期,1927年4月24日,總第182頁。
[13]嚴礪平:讀者信箱《不斷奮斗》,《生活》周刊第4卷第17期,1929年3月24日,總第181頁。
[14]邵公文主編:《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448頁。
[15]《上海通研究資料》,南天書業公司1972年版,第399頁。
[16]韜奮:《腦際中所亟謀解決者》,《生活》周刊第5卷第40期,1930年9月14日,總第668頁。
[18]鄒韜奮:《韜奮新聞出版文選》,學林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226頁。
[19]鄒嘉麗編:《憶韜奮》,學林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第194頁。
[21]韜奮:《我們最近的思想和態度》,《生活》周刊第7卷第1期,1932年1月9日,總第11頁。
責任編輯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