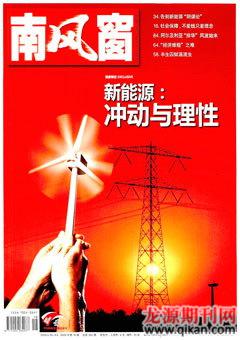“暗中盜竊”的高管薪酬
王建昆
是蘋果爛了,還是裝蘋果的桶爛了?對飽受爭議的高管高薪制度,兩位法學教授——哈佛大學的盧西恩·伯切克和加州伯克利大學的杰西-弗里德——在他們合著的這本書中開門見山地提出問題。他們的答案是后者,被其他國家視為模范的美國公司治理機制出了問題。而問題出現在董事身上。
作者在第一章特別說明,這本書討論的是沒有控股股東的美國上市公司。通常認為,高管們不可能自發地為股東利益服務,因此需要適當的激勵措施去抑制其追求私利的沖動。董事會通過與包括CEO在內的高管們公平議價,設計出符合股東利益的薪酬安排,這是一場公平的市場交易。這種通行的觀點,是公司法學家們和金融經濟學家們討論高管薪酬問題的基礎。
這種“公平交易論”的前提是,董事是為股東利益服務的,而高管則不是。假如我們承認,高管不會與生俱來地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那么我們憑什么相信董事就會這樣做呢?董事雖然持股,但所占份額很少,董事難道不會受到個人私利和偏好的影響嗎?
兩位法學教授指出,董事既可能受到經濟利益的影響,也可能受到非經濟利益的影響。CEO通常擔任董事提名委員會的委員,即便CEO不在其中正式任職,董事會和提名委員會不大可能提名一個CEO明確反對的人選,董事想連任就得和CEO和平相處,和CEO搞好關系,還可以借助CEO之手為自己謀利。CEO的職權使其在公司之外影響也很大,他可以為董事直接或者間接謀利;非經濟利益,主要是社會和心理方面的,董事即便心里對CEO不爽,也怕得罪支持CEO的其他董事,很多董事可能在CEO上任之前就與之有社會聯系。因此,董事可能會制定和批準不利于股東但卻有利于高管的薪酬安排。
也許有人會問,他們這么做無需支付很高成本嗎?不幸的是,董事偏向高管的成本不高,甚至非常低。其成本主要包括董事持股貶值和聲譽降低。董事自己占有一定的股權,也受到股權激勵,但其持股份額依然不高,因此即便薪酬安排不舍理,自己損失也不大。至于董事的聲譽,可能會受到一定影響,但在整個商界,除非你做得如安然的董事會成員那樣非常過火,否則你挑戰CEO薪酬的名聲在外,那么你到其他公司做CEO或者獨立董事的機會也很少。
那么,市場力量足以防止董事會和高管之間的這場交易偏離公平嗎?芝加哥學派認為,經理人市場、公司控制權市場、資本和商品市場的合力,可以保證高管最終代表股東利益。作者認為,市場的懲罰和社會的公憤一樣,只能部分約束他們的行為,他們會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設計復雜而模糊的薪酬形式,從而實現自己的利益再分配。這種再分配比他們接受的市場懲罰要大得多。
這本書出版于2004年。在安然事件之后的2003年,美國證券交易所采取的上市公司新標準并未有效:首先新規則沒有禁止公司在其董事費用外向董事提供報酬,僅僅限制而非禁止公司與獨立董事有關聯的其他公司之間的交易。這一改革未能限制高管回報董事的權力。
既然管理層對董事會施加壓力的原因沒有消失,那么薪酬問題就不再是唯一的問題了,可能在其他領域,董事會同樣無法掣肘管理層。換句話說,公司治理的危機在于高管與董事已經結為利益共同體,一起拋棄了股東。因此,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約翰·卡非教授說:“高管薪酬既不公平,又無效率,既可說是公開談判的產物,又像是暗中盜竊的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