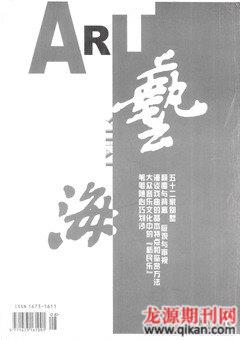女性主義與王家衛(wèi)電影中的女性形象
陳 華
王家衛(wèi)這個身在香港,流有華夏血統(tǒng),理念來自于西方的電影人,與香港一起經(jīng)歷著東西文化的自身整合。兩種文化所賦予的理性精神,往往使他以全球化的眼光探求人性,帶著這種態(tài)度塑造的電影女性形象也融合了東西文化特質,更使人物形象隨著題材以及導演不同藝術追求而發(fā)生嬗變。從《旺角卡門》電影類型中女性角色的突破開始,女性人物就為王家衛(wèi)電影女性定下打破傳統(tǒng)的基調;到都市電影《重慶森林》、《墮落天使》中,王家衛(wèi)電影中的女性及愛情模式被演繹得特別甚至另類;在六十年代懷舊電影中,獨特的東方女性魅力更為王家衛(wèi)電影帶來意想不到的全新視角。本文從王家衛(wèi)《旺角卡門》到《愛神之手》這九部作品類型入手,從時間緯度縱向分析王家衛(wèi)電影的女性形象,探索女性意識下其嬗變的大致方向。
(一)性別平衡視角下的女性
王家衛(wèi)電影,從女性意識角度來看,可以將其以《春光乍泄》為分界線,之前的電影中女性人物的塑造,更多是導演不動聲色的關注。她們形態(tài)各異的女性角色存在,更多只是作為導演表現(xiàn)其現(xiàn)代社會生存狀態(tài)這一主題的必要載體。在人物刻畫中,女性作為第二性的特點被淡化了許多。在電影《重慶森林》中,前后兩段故事中女性形象并沒有傳統(tǒng)意義上的過多女性刻畫痕跡。警察663女友的分手原因莫名其妙,金發(fā)女毒販的角色冷漠孤獨,女性人物的性格若以女性意識角度看來是頗具女性意識的。與中國傳統(tǒng)藝術作品中,女性多愁善感,消極面對人生,女人的命運就像攀附在男人大樹上的花和藤蔓,僅是美麗的附庸不同,王家衛(wèi)影片中的女性人物似乎正好相反。
《春光乍泄》中女性外部特征被淡化,影片中導演并未刻意展示愛情中主人公的性別角色,但在某種程度上卻有著愛情中性別平等的意識。
王家衛(wèi)在性別中體現(xiàn)的平等意識表現(xiàn)在:他不獨立、不刻意去展現(xiàn)女性受到感情傷害后的痛苦與掙扎。在王家衛(wèi)的電影中,男人與女人在感情上是一樣容易受傷害的。在《東邪西毒》中,西毒的愛人,是他的嫂子。她是一個對愛的追求上有強烈反抗意識的女性形象。她同歐陽鋒是互相愛慕的,但對歐陽鋒來說:女人是依附于男人的,女人的感受無關緊要,或者愛不必說。但因為歐陽峰缺乏鄭重的承諾與真誠,女人負氣嫁作了他人婦。許多女性在感情世界,迷失自我又要找尋自我,譬如《阿飛正傳》中的蘇麗珍。但歐陽鋒的大嫂卻在痛苦之中找尋自我價值、重視和尊重,但她那樣極端的方式使她失去了愛與被愛的機會,也以失去自身幸福作為了代價。《東邪西毒》中等待的女子是一個徹底反抗的女人,與其它女人相比,她沒有任何感情負擔,這使她與歐陽鋒為象征的男性世界有著對峙般的姿態(tài)。她拒絕以身體作為交換。以固執(zhí)的姿態(tài)忍受烈日暴曬,等待愿為她報仇的人。影片中洪七與女孩的關系既無功利性的沖突色彩,也無情感性的欲望色彩,是干凈而透明的關系,有著《東邪西毒》中少有的溫暖色彩。洪七的老婆有著淳樸的性格,與洪七一樣簡單、倔強。影片中的她為情感甘愿放棄一切,似乎深陷男性傳統(tǒng)藩籬,但卻幸福無比。她的單純與其它女人的復雜情感在影片中是另一番隔河之景,但清醒的導演與現(xiàn)代觀者都明白,洪七女人式的人物,在現(xiàn)代社會似乎早已絕跡。
早期王家衛(wèi)電影世界中,女人與男人在生存體驗上是相同的,一樣有情感的困惑與無奈。女性并非被輕易納于男性文化的陰影之下,她們在淡化性別特征和退守愛情理想的背后,卻深藏著一個深刻的女性認識。
(二)男性視角下的女性
《春光乍泄》之后的電影《花樣年華》及《2046》,男性角色不再保持男女角色對稱性分布。尤其是影片《2046》中,男主角僅為一名,并且僅作為觀察視角的承擔者而出現(xiàn)在影片,但影片中女性作為第二性的身份卻在無形中被再次宣判!
《花樣年華》中蘇麗珍與周慕云相知相愛卻不能相守,蘇麗珍是一個走不出丈夫名字的現(xiàn)代“娜拉”。她是一個只有夫姓的妻子角色。蘇麗珍與周慕云的無果愛情,是被傳統(tǒng)道德觀念、社會壓力拆散的,這種社會壓力的真正內涵就是女性必須從一而終的社會道德文化。沒有姓名沒有自己的女性孤守住家,在雨巷陰暗處是再也不應該也無法追求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幸福的。
《2046》白玲與lulu(咪咪)的命運與遭遇到的男性緊密相連。白玲先后被男友和周慕云拋棄,落入風塵中的她繼續(xù)深深地墮落,淪為男性的性伴侶角色。在角色的流轉之下是她作為女性內心深處對男性的深刻絕望。絕望源于她曾經(jīng)的深切希望,希望男性是她的天,能為她遮風擋雨。而男性形象的一再坍塌,使她無法逃避深陷的窠臼,她的悲劇命運是注定的;Lulu總在找尋永遠的夢想—一個愛人,一個家。不管她找到與否,女性形象的自我定位,都躲不開男性的陰影。它定格成為附在男性臂膀下的一個伸縮的影子,沒有主體性。作為客體的存在,lulu女性的地位,永遠是從屬的。
影片中以女兒面目出現(xiàn)的男性與女性關系中,父親代表著男性掌握權利。王潔雯這個反叛的女兒,為追求自我,離家出走,最后卻不得不向父親妥協(xié)。影片沒有展現(xiàn)事件的緣由,僅僅通過前后場面的更迭,以結果展示男性與女性的力量對比。女性在強悍的男性面前是無力的。可以說,女性扮演的所有角色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與文化傳統(tǒng)所賦予的。女性的宿命,就是向男性低頭,女性沒有說話的權力。
當王靖雯與男友的戀愛遭遇父親的責難,她沒有語言。她追求的愛在父權代表的世界中無法立足。男性認同的國家、民族、歷史等壓迫著作為女性追求愛情的話語權。她只有借助日語不斷、重復和堅持:“我會跟你走”,來表達自己內心深處的執(zhí)著。她的自言自語可以看作是“現(xiàn)代女性生存困境的指稱和象征,而且從細微處揭示并顛覆著經(jīng)典的男性話語霸權。”(洪春生《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對電影<2046>的女性主義透視》,藝術廣角,2005年第4期)
女性是沒有自主權的,她們都逐漸喪失了主體性。在周慕云這一男性的眼前呈現(xiàn)出“被看”的客體存在狀態(tài)。王靖雯是周慕云的理想愛人,也是導演偏愛的女性。她比蘇麗珍走得更遠,她的內心世界豐富,她的精神是獨立的。她不是依附于男性的,而是真正獨立的女性。這是一種男性設想的女性出路,也是男性尋求的理想愛人。但在這一追逐理想愛人的過程之中,女性卻成為了男性確認自己存在的一種物化手段,另一個“他者”。
《2046》中的女性人物,把自己隱匿在種種角色之下,通過自我隱忍使生命形態(tài)呈現(xiàn)于世。把女性作為片中的主要“風景”,展現(xiàn)了女性在各種形象之下的悲劇命運,強化了女性的性別從屬地位。使影片在內容上表現(xiàn)出強烈的女性主義色彩。
王家衛(wèi)在《2046》公映前,曾透露《2046》是一部表達時間的電影。《2046》中的周慕云與蘇麗珍、白玲、王靖雯等女人的遭遇,使電影呈現(xiàn)出代表過去、現(xiàn)在、未來的多重鏡像結構關系。周慕云通過創(chuàng)作科幻小說,來承載一切記憶,也為電影打造了夢幻般時空。在那里,愛情以男性為中心。男性來去是由自己決定的。作為服務員的女性機器人,在電影中有著直指未來的共同困境:她們終身受制于空間的壓迫,不能有獨立的情感。她們機械地行走及提供服務,高揚的頭,空洞的眼,無處不在暗示她們從身體到精神上的不自由與不自主。“代表女性角色的機器人,機械行走暗示要遵循性別角色。服務功能的設定,指認著女性的從屬性質。隨著時間的演化,未來的女性仍然是被侮辱輕視的弱勢性別。女性的枷鎖不是解脫,而是無以解脫了。”(洪春生《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對電影<2046>的女性主義透視》,藝術廣角,2005年第4期)而這種背景中的女性,又遭遇了整體空間的失語狀態(tài)。其生存的空間困境就愈加深重。
電影中,“2046”列車表面看來是虛幻的,它抵消了過去、現(xiàn)在、未來的時空界限,而在對待這三個時空中的女性的不平等的高度抽象化隱喻中,多元化的“任意能指”也隨機產(chǎn)生。這里,提示出愛情在兩性關系中的真實面貌,也加強了影片對“女性主義緯度的反思批判意向”(陳旭光《當代中國影視文化研究》P29,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2046》中時間與空間虛實相存,在抽象、隱喻中無形拉長了女性的壓抑。無論在什么時空,女性生存的困境都存在,幻境時空更是極大豐富了女性主義色彩。
王家衛(wèi)電影到《2046》,濃重的女性色彩涂抹在影片的外衣上,但是“應該看到這樣對女性第二性身份,地位的確認是在男性的眼光下完成的”(李道新《王家衛(wèi)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含義》,《當代電影》,2001年第3期)。王家衛(wèi)的電影到此,正如評論家李道新所說:“是一種混雜著女性目光的男性視角”仍在繼續(xù)。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梳理出王家衛(wèi)電影女性人物演變的大致方向,由性別平衡視角下的女性到混雜女性目光的男性視角下的女性,王家衛(wèi)電影中的女性人物逐漸跳出了模糊的地位,清晰地演變出作者導演對女性地位的深切關注軌跡。
(作者單位:中州大學文化傳播學院)
責任編輯: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