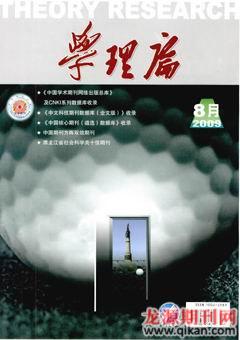利益調整與法律基本價值之實現
黃小英
摘 要:我國目前社會生活中出現了許多新的利益矛盾和沖突,如何對其進行協調和控制是構建和諧社會所必須解決的問題。為此,我們有必要從利益調整中公平與效率的應有之意出發,探討法在利益調整中如何均衡公平與效率,從而使兩者處于動態的平衡,最終促進利益調整中法的公平與效率價值之實現。
關鍵詞:利益調整;和諧社會;公平與效率;社會公正
中圖分類號:DF3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2589(2009)20-0075-04
在社會調整系統中,法是利益關系調整的基本手段,是其他社會調整手段發生矛盾沖突時,最終解決的方法是尋求法律的確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利益關系法律調整的價值取向,以什么為價值目標,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利益關系調整的法律體系,是法哲學要解答的基本問題之一。法的價值作為法哲學領域的一個獨立命題,離不開法律制度的表征和實現,同時又受法律價值觀的約束和指引。為此,我們必須以我國當前利益整合過程中出現的新趨向為視角,探尋實現法的公平與效率價值實現的新路徑。
一、我國利益調整格局的新動向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社會的同質化結構已呈現出多元化的現象,即利益多元化、價值多元化和生活多元化等特征日益明顯,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方面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值得我們重視的跡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沖破了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利益高度一致的利益格局,形成國家、集體和個人不同的利益關系;打破了計劃經濟條件下人民群眾內部同質性的同時,工人、農民與其他社會階層由于經濟基礎、政治資源、文化條件、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差異,正在形成若干不同層次的利益群體。這樣使各利益主體之間的差距迅速拉大,矛盾日益增多,關系變得錯綜復雜。同時,利益關系復雜化,表現為眾多的不協調性。隨著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市場競爭機制作用的增強,我國出現頗具數量的生活困難群體已是不容忽視的客觀存在。在不少地區,下崗職工的生活保障問題和就業問題已經成為最主要的不穩定因素。
馬克思曾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面對這些新動向,我們必須對這些不同利益的進行從新認識并加以協調,進而緩和、化解人與人的矛盾、人與自然的矛盾,才能實現社會和經濟的持續發展。為此,我們黨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概念和發展目標。作為一個全面、系統的和諧體系,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兼備社會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之雙重特性,奉行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并尊重利益多元的理性社會。[2]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充滿創造活力的社會,是各方面利益關系得到有效協調的社會,也是穩定有序的社會。因此,如何調整各種經濟利益矛盾,并將其控制在一個合理范圍內,是我們目前在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分析當前導致我國社會利益關系矛盾突出的原因,首先與我國經濟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關。當前我國人均GDP不到2000美元,仍然處于工業化的初中級階段,從而使得收入差距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客觀必然性。此外,各種利益矛盾的產生還有經濟體制不健全和政策不合理方面的原因,如競爭條件和機會不平等、調節收入差距的制度不合理、保護弱勢群體權益的政策不健全、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不到位以及由于各種違法腐敗問題所導致的利益關系矛盾等。而從深層次來看,“隨著每一次社會制度的巨大歷史變革,人們的觀念也會發生變革。”[3]產生這些不健全政策和制度的根本原因卻是人們價值觀念的偏頗,沒有能夠很好的處理諸如公平與效率價值在發展中的矛盾和沖突的均衡與取舍。
和諧社會是建立在各種社會利益和關系有機協調基礎之上的,而法律的一項重要社會功能就是通過制定分配和調整人們之間的利益的行為規則,來調整社會關系并保證社會關系的協調和穩定。然而,在進行利益的分配和調整中,公平和效率的價值目標經常處于深沉的張力之中,并表現為人們制定和實施法律行為規則過程中的二難。為此,我們有必要從利益調整中公平與效率的應有之意出發,探討法在利益調整中如何均衡公平與效率,從而使兩者處于動態的平衡,最終使得利益調整中法的公平與效率價值都能實現。
二、當前利益調整中公平、效率價值應有之義
公平正義,是人類追求美好社會的一個永恒主題,是社會發展進步的一種價值取向。馬克思主義第一次把公平正義的實現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為我們在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論基礎。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公平正義是我們在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過程中進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創新的重要依據,是協調社會各階層關系的基本準則,也是增強社會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旗幟。其基本內涵是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制定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的基本著眼點,正確兼顧不同部門、不同地區、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依法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使公平正義具體體現在人們從事各項活動的起點、機會、過程和結果之中,切實保障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權益,使全體人民在共建中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邁進。
效率是反映經濟活動配置和利用社會資源的有效比率及社會經濟發展成效的概念,從廣義上講,通常是指不浪費,或者是指現有的資源得到最佳的利用。正如奧肯所言,“對經濟學家來說,就像對工程師一樣,效率意味著從一個既定的投入中獲得最大的產出”、“一旦社會發現一種以同樣的投入可以得到更多的產品的途徑,那它便提高了效率[4]。一方面,效率一般指的是投入與產出或成本與收益的比率,它體現的是人們在改造自然、社會和人自身活動中所具有的能力、達到的水平;另一方面,效率也有社會效率與經濟效率的區別,因為效率應該包含“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盡其流”的效率增長和“按效益分配的原則”兩種情況。[5]理性的、高級的衡量標準則是根據預期目的對社會資源的配置和利用的最終結果作出的社會評價,即社會資源的配置和利用使越來越多的人改善境況而同時沒有人因此而境況變壞,則意味著效率提高了。這種效率觀顯然包含著社會公平因素,是倫理與功利的統一。就實質而言,資源的配置是由社會制度即國家一系列法律和政策規定的。目前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本應由國家法律制度、國家政策調節的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誤操作為由市場調節的公平問題,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市場調節與國家調節相結合、追求公平和效率的經濟體制,其中市場調節產生的是效率,國家調節針對的是公平。改革開放以來,黨在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上,經歷了一個認識演進及政策調整的艱辛探索過程。十六屆四中全會,“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在黨的文件中淡出,社會公平作為重要關注點不斷加以強調。黨逐步形成并明確提出: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這是又一創新亮點,其一:突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層面,都要構建效率與公平相統一的實現機制。其二,要求處理效率與公平關系的“關口”前移初次分配環節,形成公平要素在分配和再分配領域的“全覆蓋”。在分配系統中,初次分配占絕大部分比重,再分配比重占10%左右,歷史經驗表明,如果初次分配發生大問題,再分配不論怎樣努力也無濟于事。十七大報告首次強調初次分配中體現公平,這對理順整個收入分配關系具有全局意義。其三,強調正確地組合使用財政、稅收和社會保障等再分配手段,全面解決分配不公。因此,在利益調整過程中,在對待公平與效率的問題上,不能有所謂先后、主從之分。公平與效率是在對立基礎上的有機統一,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效率是公平中的效率,公平是效率中的公平。
三、利益調整中法的公平與效率價值之實現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利益關系法律調整的價值取向,是由構成我國目前所處的這一歷史時代的國家的、民族的特點所決定的。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過程中,法律調整體系的價值取向,一是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地位平等、機會均等、標準公平、程序公開化等是市場經濟公平競爭對法律的要求,因此,法律調整的首要任務是改變由于種種原因而導致的機會與權利的不公平。二是抑制貧富懸殊、限制兩極分化,實現社會利益分配關系的公平,這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要求,也是實現社會穩定、調動勞動者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前提條件。以上兩個方面的目標追求,在法律調整體系中也因社會發展的階段不同而有所側重。正因為如此,中國現行法的價值表現出多質性、沖突性和失衡性。
(一)法律必須以維護社會公平為價值訴求
在我國利益分化和利益結構調整的進程中,要實現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均衡,構建和諧社會,關鍵是要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來容納和規范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表達和利益博弈,實現社會資源和權利的公正分配。誠如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所說,在一個健全的法律制度中,秩序與正義這兩個價值常常緊密相聯、融洽一致的。一個法律制度若不能滿足正義的要求,那么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它就無力為政治實體提供秩序與和平。[6]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和維護社會公正,就是要通過法律制度安排,在社會成員或群體成員之間對權利、權力、義務和責任進行合理配置,使廣大人民群眾對自己的分配所得與他人的差距感到均衡,從而維護社會的秩序和穩定,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公正的利益實現,要求政府政策制定要體現出普惠性,體現政策制度應有的公平價值。政策制定的基本宗旨在于保護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在于使社會成員普遍受益。普惠性的基本要求是,每一個社會成員、每一個社會群體的尊嚴和利益都應當得到有效地維護。任何一個社會群體尊嚴和利益的滿足都不得以犧牲其它社會群體和社會成員的尊嚴和利益為前提條件。如果借用羅爾斯的語言來表述,那就是:“所有社會價值——自由和集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基礎——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對其中的一種價值或所有價值的一種不平等分配合乎每個人的利益。”[7]為此,在法律的基本原則方面必須充分體現對社會公平的特別關懷。法的原則體現法的本質,是法的精神、法的價值取向的理性化,是社會主體利益要求與利益關系的法的集中反映,是法律制度的精髓、靈魂,是立法、執法與守法的指針。所以,法律在確認與保護財產所有權的原則、確認與保護個人利益的原則、保障社會公共利益的原則、利益調整公開化、程序化的原則的基礎上要特別彰顯保護公平競爭的原則和社會福利保障原則。法律應當允許并保護公平競爭,創設良好的競爭環境。同時,利益關系法律調整的原則,既要保護以“勤勞富裕”的社會利益要求,又要限制兩極分化。法律應十分注重社會福利的保障,使在競爭中處于弱者地位、暫時失敗的成員得到救濟援助。國家必須通過稅收,抑制一次分配所造成的利益分配差距,實現二次分配所要求的利益分配公平。
(二)法必須關注經濟發展中的效率價值
現代法律應以解放人為出發點,以發展人為使命,在充分重視人的主體性基礎上承認并充分保障個人的利益與需要。需要的滿足、利益的追求是人最基本的心理特征,是社會發展的本源動力。現代法律就應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為目標,在進行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礎上,設置有利于資源充分利用、效率最大可能發揮的制度,保障效率的發展,促進效率的提高。法律資源配置上的效率居先意味著:在整個法律價值體系中,效率價值居于優先位階,是配置社會資源的首要價值標準。[8]當然,效率居先并不排斥自由、公平、秩序等其他價值,而恰恰是以自由、平等為內在機制,以秩序為外部環境的。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法律應當把提高效率、發展生產力作為自己的主要職能。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生產力始終是社會變革與進步的決定性力量。“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變革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9]而經濟手段的運用必須是依法辦事,用法律手段來引導、確定、規范、保障和約束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市場經濟建立在充分競爭的基礎上,這就需要用法律來激勵人們去競爭;同時,為了防止高的交易成本及實現個人效用的最大化,進而實現市場效率,又需要有約束競爭方式的行為規則。“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的最根本特征在于它能夠提供一組有關權利、責任和義務的規則,能為一切創造性和生產性活動提供最廣大的空間,每個人都不是去想方設法通過占得別人的便宜來增進自己的利益,而是想方設法通過提高效率,并由此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0]因而,明確責、權、義,規范競爭的法制也就應運而生,從而有利于節約社會主體交易費用和減少交易成本。
(三)法必須努力實現公平與效率價值之均衡
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是與時俱進的。黨的十六大提出了一次分配主要講效率,二次分配主要講公平,作了一個區分。這就告訴我們,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效率優先,應該區別不同的階段、不同的情況、不同的對象、不同的問題,來具體而不是籠統地討論二者的相互關系。一次分配也不僅僅是個效率問題,也有公平問題。二次分配也不完全是個公平問題,反過來也有效率問題。為此,我們提出所謂“公平與效率的均衡”[11],主要含義是:(1)既不過分強調效率,適當追求較高的效率,也不過分強調公平,要保障相對的社會公平。這樣的公平與效率是相互結合而不是相互排斥的。(2)效率是實現公平的前提和條件,而不以犧牲公平為條件;同樣,公平也是保持和提高效率的前提和條件,而不以損失效率為條件。這樣的公平與效率是互為條件和前提的。(3)進一步說,公平水平的提高會帶來和促進效率水平的提高;同樣,效率水平的提高也會帶來和促進公平水平的提高。二者不但不相互抵消,而且相互促進、共同提高。這一觀念對于解決當下反壟斷法方面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效率和公平是內在統一的,沒有公平的效率只能是皮鞭下的效率和饑餓壓力下的效率,這種效率只能為不平等的社會提供物質基礎。沒有效率的公平只能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公平,是一種沒有意義公平。因此,我們的任務是盡最大努力協調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使兩者得以協調和平衡,爭取真正的效率與真正的公平的兼得。實質公平正義與社會整體效率共同作為法的基本價值,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法通過對一般的、不合理的行為和狀態的禁止和對特殊的、合理的行為和狀態的適用除外,既可以通過禁止性規范來保障有效競爭,以實現提高經濟效率,保障經濟公平的目的;又可以通過對特殊行為的鼓勵,來防止過度競爭,以實現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目的。法的這兩個方面的價值目標應當盡可能協調兼顧,而且基于其社會本位性,從社會根本的整體的利益和需要出發,它們之間也完全可以實現協調兼顧。在特定情況下確實需要選擇出一個更優先的價值目標時,更能體現法律本質的公平正義目標應當優先于效率目標。“公正目標不僅僅與我國經濟體制的過渡性特點、大眾的心理特點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穩定的客觀要求有關,也是由我國政治、法律和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本質所決定和要求的。社會主義法律的生命力,也就在于能夠在各種利益沖突中保持合理的平衡,從而充分地保護所有人的利益。在我國,雖然黨和國家的有些政策文件曾使用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但它只適用于特定時期內某一國民收入再分配政策領域,既不應當不適當地擴大其適用范圍,也不應渲染其一般價值意義或普遍指導意義,更不能以此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價值目標或政策目標。對社會公正本身的追求,應當永遠是社會主義法律的根本目標。”[12]
國家作為管理者,具有管理經濟的職責,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和宏觀經濟效益的增加是國家管理經濟的目的所在;消費者希望有自由選擇商品和交易對象的機會;經營者渴望有理想的競爭環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對于法的價值需求是多元的,矛盾也是難以避免的。但是,筆者認為各價值取向之間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作為彌補市場缺陷,干預主體自由之法,限制經濟人私益最大化,以追求社會整體效益最大化為目標;其限制個人自由之無限,維持整體競爭秩序之活力;其以競爭為起點,努力實現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的實質公平。“效率盡其所能,公平跟蹤效率,效率反哺公平”。[13]在構建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進程中如何的為實現社會公平、社會的高速發展及在公平與效率之間搭起溝通和對話的橋梁,是我國法必須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為此,我們必須認識到增長和效率是無法脫離以合理和公平經濟體制為基礎的。在制度成本較低和相對公平的狀態中實現增長和效率是合理的,也是改革的最佳目標。在充分認識效率與公平已經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并且公平問題已經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后,就要采取積極的行動盡快改變這種狀況,緩解社會矛盾。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
[2]羅豪才,宋功德.和諧社會的公法建構[J].中國法學,2004,(6):3.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40.
[4](美)奧肯.平等與效率[M].王奔洲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5]厲以寧.經濟學的倫理問題[M].北京:三聯書店,1995.
[6][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318.
[7][美]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62.
[8]張文顯.市場經濟與現代法的精神略論[J].中國法學,1994,(6):10.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8-9.
[10]樊綱.漸進之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21.
[11]中國社科院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尋求公正與效率的均衡[J].求是,2005,(23):21
[12]王源擴.我國競爭法的政策目標[J].法學研究,1996,(5):121.
[13]李厚廷.和諧社會的制度架構——基于效率公平關系的研究[J].社會科學研究,2005,(3):53-54.
The benefit adjustment and the law basic value realization
HUANG Xiao-ying
(Law department,Jiangsu police officer college,Nanjing 210031)
Abstract: Currently in our country appeared many new benefits antinomies and conflict in the social activities, how as to it's carry on moderate and control is set up the harmonious society must resolve of problem.For this, we have the necessity to adjust from the benefits medium equity and efficiency should the idea of have set out, the study method is in benefits adjust how balanced equity and efficiency, the balance that thus make both be placed in the dynamic state, end promote benefits adjustment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quity and the efficiency value of the method.
Key words: benefit adjustment; harmonious society;justice and efficiency;society equity
(責任編輯/王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