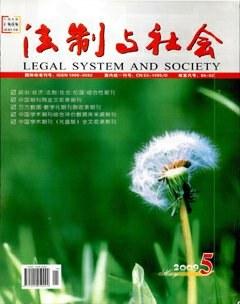無限上訴制約論
朱怡婧
摘要由于上訴權在我國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加以規定保護,從而造成較多的無限上訴的局面,使得二審法院不堪重負,甚至成為當事人提起惡意上訴的手段。因此亟需規定上訴利益為提起上訴的要件之一,在源頭上縮減不具上訴利益的案量;建立惡意上訴制約機制,明確惡意上訴的侵權性;改善先予執行制度,擴大其制度功能以保障權利人利益的及時實現。
關鍵詞無限上訴 惡意上訴 上訴利益
中圖分類號:D92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09)05-029-02
一、無限上訴的弊端及反思
無限上訴是由于立法對上訴要件的寬松規定造成上訴泛濫的現象。既表現為當事人紛紛上訴維權,呈現出法院工作欣欣向榮的良好局面但又折射出二審法院應接不暇的困境,甚至成為當事人濫用程序性權利的手段。
(一)民事上訴率反映的問題
上訴作為一種救濟機制,是當事人發泄其對一審裁判不滿的重要渠道。《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審判決(裁定)的,有權在判決(裁定)書送達之日起十五(十)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這一權利性規范賦予了當事人極大的上訴空間,體現在近年來,全國法院的民事上訴率始終保持在20%左右。而這一上訴率一旦與我國法院一審案件不斷上升的總量相結合,就清晰地呈現出民事二審案件不斷增多的趨勢。加上數量龐大的刑事、行政案件,我國法院系統不堪重負。
(二)無限上訴誘發惡意上訴
惡意上訴是指上訴人故意以他人受到侵害為目的,無事實根據和正當理由而提起上訴,致使對方遭受損失的行為。一般而言,當事人行使上訴權,目的是使其部分利益獲得法院的公正分配。但在利益的驅動下,不少當事人以投機的心態輕易地啟動二審程序,期待意料之外的利己裁判。更有甚者,惡意利用上訴程序以損害對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以轉移財產、逃避債務,或意圖以漫長的訴訟折磨拖垮對方當事人從而迫使其做出妥協,造成惡意上訴現象的出現。無限上訴容易為當事人濫用,為其惡意上訴披上合法化的外衣,造成當事人利益的減損。一方面,由于司法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一案當事人對其的非法占用間接影響了其他案件當事人獲取高質量司法救濟的現實可能性;另一方面,無限上訴的制度缺陷一旦被利用,還將必然減損該案對方當事人的利益。因此,亟需對無限上訴的程序缺陷進行分析,以杜絕上述不合理的現象。
二、無限上訴缺陷之原因探討
(一)上訴要件過于寬泛——基于上訴制度價值的考量
公正與效率是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題,也是其永恒的追求目標。然而公正與效率一直保持著緊張關系,體現在為了實現正義而對上訴要件進行寬泛的規定,從而影響效率。上訴要件形式上的約束意味著賦予當事人糾正一審瑕疵裁判的平等機會,而不對當事人是否真的有這種訴訟需求做制度上的甄別,導致上訴泛濫。然而,司法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法院不能為了平等地對待一切當事人而不加區分地賦予他們上訴權。于是學者紛紛提出,司法資源的利用要符合且只能符合分配正義原則的要求,因而有必要對上訴要件進行限制,使司法資源能夠在需要正義的當事人中間公正地分配。
(二)缺乏惡意上訴的制約機制
惡意上訴是無限上訴誘導的程序濫用現象,它的存在與寬泛的上訴要件不無關系,然而僅僅在上訴要件層面規范仍不能解決惡意上訴的問題。原因在于,“惡意本身也是個游移不定而須在不同的侵權中具體認定的概念”。作為啟動二審程序的上訴行為,其是否符合條件只能在程序啟動之初,根據一審裁判情況而做出的形式判斷。因此,為了解決無限上訴引發的惡意上訴問題,需要從惡意上訴形成的原因本身進行探討。
惡意上訴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方面,由于我國現行法律沒有將惡意訴訟明確規定為侵權行為,惡意上訴作為惡意訴訟的一種,上訴人在無限上訴的庇護下更加有恃無恐。然而值得欣喜的是,盡管近年來司法實踐中惡意訴訟的案例逐年上升,不少的惡意訴訟人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因此可借助實踐推動立法,明確惡意訴訟的侵權性;另一方面,訴訟程序的啟動除了占用了法院的司法資源,同時也需要花費當事人大量的金錢、時間以及精力。訴訟成本的支出在實踐中竟成為當事人侵權的特殊手段,而惡意上訴人需要承擔的僅是有限的訴訟費用,因此需要設置制裁機制給予惡意上訴人一定的懲罰。
三、構建無限上訴的制約機制
(一)完善上訴要件——增加上訴利益的規定
1.上訴利益的概念探究
從上訴利益設置的初衷考量,它是通過設立一定的“標準”對尋求法院司法救濟的當事人進行篩選。面對一審法院的利益判斷,只有在其所主張的利益被否定,即一審裁判對其造成不利益時,該方當事人才會“不服”。正因為如此,才有學者認為上訴利益又稱為不服利益,是因為它實質是上訴人被一審判定應當承擔的不利益。然而,“利益”與否也需要一個評斷的標準,考量的主體應當是決定司法資源具體分配的法院。只有獲得法院認可的“利益”才能夠進入司法程序,而法院要將寶貴的司法資源對其進行分配,是因為該“利益”存在救濟的必要。
從訴的利益角度出發,訴的利益從本質上說是當事人的權利和法院權力之間的利益衡量。“在民事訴訟中,并非所有的爭議都能夠憑借主體的起訴行為而當然地進入到國家司法評價的領域,而是在制度上預先設置一道關口,使得那些符合某種要求的訴請才能夠獲得法院的確定判決。”上訴利益正是一個這樣的關口,因而可將上訴利益定義為:原審法院做出于當事人不利的裁判時,當事人請求上級法院予以救濟的必要性。
2.上訴利益的具體界定
作為啟動二審程序的要件之一,對上訴利益的判斷只能在二審啟動之前進行,并且只能以一審的具體裁判結果為判斷基礎。筆者認為應當從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對抗性出發,進行形式上的判斷:(1)對判決的上訴。民事糾紛的利益沖突性決定了原告與被告在訴訟中的利益是相互對立的,雙方當事人的利益沖突在訴訟程序中往往以原告的訴訟請求以及被告在一審訴訟過程中的聲明、抗辯體現出來。因此,可將原告的訴訟請求或者被告的聲明與抗辯與一審判決結果進行比較。此時,對于一審法院的判決書,倘若己方聲明的部分或全部被一審判決承認,則被承認的一方對該被承認的部分或全部不存在上訴利益,此時對方當事人對該部分或全部存在上訴利益。(2)對裁定的上訴。一類是駁回管轄權異議的裁定,在民事訴訟中,由于原告是訴訟程序的啟動者,被告只是被動地參與到訴訟當中,所以管轄權異議一般由被告提出。而駁回管轄權異議的裁定,明顯有悖于被告對于法院管轄權的異議聲明,此時被告有上訴利益。然而實踐中存在不少當事人惡意利用管轄權異議引發上訴以拖延訴訟的情況。若對被告的上訴利益采用形式判斷的標準,任何因管轄權異議而上訴的被告都擁有上訴利益,表面看來無法抑制惡意上訴的行為。但筆者認為,設置上訴利益作為實質性的上訴要件,旨在改善無限上訴的局面,并不能起到二審裁判明辨是非的效果。對于惡意濫用管轄權異議及上訴程序的行為,一方面,可以通過設置有關的惡意上訴制裁機制予以控制;另一方面,二審法院也可對這類上訴逕行做出裁判,及時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另一類是不予受理與駁回起訴的裁定,法院做出的這兩種裁定是對原告起訴要件欠缺的判斷。由于《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應當在立案之次日起5日內將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告,意味著,法院在做出不予受理裁定時并不存在被告的抗辯,法院在做出駁回裁定時被告也不一定已經做出抗辯,所以被告是否具有上訴利益難以通過比較其聲明與裁定書主文得出結論。筆者認為,這兩種裁定將原告的起訴拒之于法院的大門之外,并沒有對原告的利益產生任何影響,更遑論對被告不利,且《民事訴訟法》規定“原告對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訴”,似乎暗喻著被告此時無上訴的必要。因此,為了節約司法資源,對于這兩種裁定應認為只有原告具有上訴利益。
(二)構建惡意訴訟侵權行為制度
立法的先天不足使二審程序成為滋生惡意上訴的溫床,因此必須構建惡意訴訟侵權行為制度并明確惡意上訴乃侵權行為。由于惡意上訴乃惡意訴訟的一種,本文立足于對無限上訴的限制,僅討論惡意上訴的構成要件:第一,上訴人的主觀狀態應為故意。惡意乃嚴重的故意,一般的上訴是出于維權的目的,而惡意上訴則以侵權為目的。表現為當事人明知二審法院不可能對一審裁判進行改判或發回重審的,但為了延續對方當事人權益不確定的狀態而上訴,以實現案件裁判結果以外的目的;第二,客觀上實施了惡意上訴的行為,表現為惡意啟動上訴之后消極對待庭審程序、轉移或隱匿一審判定給對方當事人的財產等;第三,惡意上訴行為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果,使被上訴人遭受不必要的利益損失,令國家司法資源造成不必要的的浪費。其中主要的是被上訴人遭受的經濟利益,不僅包括訴訟成本的耗費,在上訴人轉移財產的場合也包含債權無法實現的經濟損失;第四,被上訴人的利益損失與惡意上訴行為存在著因果關系,即不存在惡意上訴行為,就不會存在該部分的利益損失。
對于惡意上訴人造成的危害后果,應當在立法上明確其責任范圍。被上訴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范圍應當包含參與二審的基本費用支出,如誤工費、差旅費、律師費等。倘若造成被上訴人社會評價的降低,同時構成名譽侵權或其它人身權受損的情形,還應當包含精神損害賠償;為了保證司法資源的合法利用,可以考慮在立法上將嚴重的惡意上訴行為確定為妨害民事訴訟行為的一種,對上訴人適用《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給予其罰款或拘留的處罰,以起到懲戒的效果。
(三)改善我國的先予執行制度
為了防止惡意上訴,不少國家和地區采用假執行制度對其進行規制。假執行是指尚未生效的判決經一定程序被賦予執行力,可予以強制執行,這是為了保護未確定判決的勝訴方利益而設立的特殊制度,以防止敗訴方拖延訴訟,使將來的判決難以執行。其法理基礎在于,一審法院已對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做出權威性的判定,當事人爭訟的法律關系得到了審理法院的確定。但由于審級制度的設計,一審裁判做出但并不立即生效,目的是為了給當事人提供宣泄不滿的渠道,并通過二審保證一審裁判的正確性。然而對于某些財產案件,敗訴方可能通過濫用上訴權而獲得時間轉移財產,使得二審法院的生效裁判最終成為法律白條,嚴重損害司法的公信力。因此部分國家或地區在程序上進行了平衡保護設計,讓財產案件可以通過假執行制度先行執行。即使敗訴方通過上訴獲得了二審改判,也可通過對財產案件執行回轉使其恢復原狀,不至于對上訴方造成過分的損失。
盡管我國尚未確立假執行制度,但現行的先予執行制度也可起到保全權利人合法權益的功能。兩者相比,區別在于制度的設計初衷。先予執行以解決原告生產或生活急需為要,適用范圍較小,無法涵蓋假執行制度防止惡意上訴的功能。在我國確立制約惡意上訴的相關制度之前,完善現有的先予執行制度,賦予其一定的假執行功能,以避免正義的遲到,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概而言之,可以借鑒國外立法,通過適當調整先予執行的適用范圍,擴展至財產爭議案件;并賦予二審法院啟動先予執行的職權,即發現上訴人出于惡意而上訴時可以裁定對一審判決先予執行,除非上訴人提供相應的擔保;同時在原告申請先予執行的場合(非生產生活急需的情形),規定被告的擔保可以阻卻法院對原告申請的批準等。通過細化先予執行的適用條件,賦予其更強的可操作性,更大程度地保護當事人的權益。
注釋:
杜開林.法院判決結案的現狀與改革方向.法學.2006(5).
齊樹潔.民事上訴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德]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下卷) .焦美華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于海生.訴訟欺詐的侵權責任.中國法學.2008(5).
邱星美,唐玉富.民事上訴程序中的利益變動.法學研究.2006(6).
徐靜.論先行執行與制約惡意上訴.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6).
姚志堅,陳傳勝.假執行與濫用上訴權懲罰制度之設立.人民司法.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