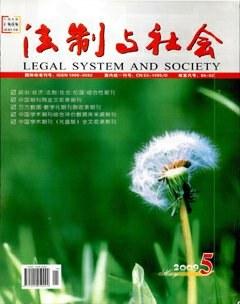淺析綁架罪的既未遂標準
姚桂紅
摘要綁架作為一種常見多發的犯罪,對社會有著嚴重的危害性。對此,法律制定了非常嚴格的處罰制度。有關綁架罪的問題在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存有較大爭議,本文主要圍繞其中較突出的問題之一——綁架罪的既未遂標準設定展開分析,對完善綁架罪的現行立法做出了思考和探索。
關鍵詞綁架罪 既未遂標準
中圖分類號:D92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09)05-074-01
2009年2月28日通過并公布了我國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七)》,其中對我國《刑法》第239條做出的修改后的條文中增加了一檔刑罰: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對此修改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研究認為,綁架罪嚴重危及公民人身安全,應予嚴懲;同時,考慮到實際發生的這類案件的具體情況比較復雜,在刑罰設置上適當增加檔次,有利于按照罪刑相適應的原則懲治犯罪。
有學者認為,《刑法修正案(七)》僅增加一個量刑檔次并沒有完全解決我國現行綁架罪立法設置中存在的起刑點高、最高法定刑重的缺陷。這也致使本罪的既未遂標準經常成為爭議焦點與調節刑罰輕重的關鍵因素。
有關綁架罪的既未遂標準,理論界雖見仁見智、莫衷一是,但分歧主要源于對綁架罪是單一行為還是復合行為有不同看法。
持單一行為說的學者認為,只要行為人實施了綁架行為,將被綁架人置于自己的實力控制之下,即構成綁架罪既遂。綜觀持單一行為說的學者的主要觀點理由有:(1)綁架罪的立法宗旨是著重保護公民的人身權益而不強調行為人是否實現犯罪目的,且根據《刑法》第239條所規定的罪狀,刑法評價的重心在“綁架”一詞上;(2)從構成要件上看,要求有勒索財物和提出其他要求的目的,此目的屬于主觀要件,不一定要對應有目的行為;(3)按照單一行為說,綁架罪也存在犯罪未遂、中止的余地。例如,如果行為人已著手實施綁架行為,但由于被綁架人全力抗拒等行為人主觀意識以外的原因未能實際控制被綁架人的,屬于綁架罪的未遂;如果行為人著手實施綁架行為后,實際控制被害人之前,由于良心發現或懾于法律制裁等原因,自動中止了綁架行為的,則構成綁架罪的犯罪中止。并且,合理解釋綁架罪的形態特征,也不妨礙對承繼的共犯的認定和處罰。
而持復合行為說的學者認為,綁架罪的既遂,不僅要求有綁架行為,還要有進一步實施目的的行為,即行為人實施了勒索財物的行為或者提出其他要求行為。筆者贊同復合行為說的觀點。下面具體加以闡述。
首先,正如有學者論述的那樣,若堅持單一行為說的立場,有兩個問題得不到正確、合理的解決:一是犯罪中止問題。按照單一行為說,行為人一經實行綁架他人或偷盜嬰幼兒行為,既遂即成,行為人即使自動放棄勒索財物或提出其他要求的行為,也沒有成立犯罪中止之余地,這不僅不合情理,也不利于鼓勵綁架者迷途知返,在司法裁量上也難以體現罪刑相當原則的基本要義。二是共同犯罪問題。司法實踐中,有的行為人在其他犯罪分子實施了綁架行為后,中途參與實施勒索他人財物的行為,對于此種情況,如果按照一經實施綁架行為就成立犯罪既遂的主張,顯然不能按綁架罪的共同犯罪處理,因為行為人的行為屬于事先無通謀的事后行為。對于事前無通謀的事后行為,構成其他犯罪的,按其他犯罪定罪處罰;不構成犯罪的,以非罪處理。但對于這類情況不按綁架罪的共同犯罪處理,于理于法都是說不通的。筆者認為,綁架罪往往由多人共同實施或由多人前后相繼地分擔強行綁架、看守人質、取得贖金等任務,理應構成本罪共犯。
其次,除前所述的兩個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外,還有學者分析指出:(1)通過采用罪質、罪量分析法,立法者為該罪設置了特殊嚴厲的法定刑,昭示了綁架罪的罪質內容應當包含較同類犯罪對法益的更烈危害之處,否則不足以合理解釋綁架罪的罪量限度。(2)有學者分析認為應以具體犯罪案發時的常見狀態為標準認定綁架罪的既遂形態。而綁架罪案發的常見狀態大多是在綁架者實施了劫持人質、勒索或提出其他要求的復合行為以后,達到犯罪目的之前。于此,應將綁架罪的既遂形態設定為過程行為犯。(3)按照單一行為說,綁架行為一成立即構成綁架既遂,存在著過度壓縮本罪之未完成形態的存在空間,容易造成罪刑失衡的問題。況且,只有綁架行為即可成立犯罪既遂,其在客觀表現上就與非法拘禁罪無甚差異,何以匹配如此嚴厲的法定刑?
綜上,筆者認為,復合行為說的觀點較為妥當。主要有以下幾點補充理由:
第一,《刑法》第239條將“以勒索財物為目的”明確規定為綁架罪的主觀目的,但并不排除有與之對應的勒索財物之實行行為存在。并且實踐中綁架罪的犯罪分子在綁架他人或偷盜嬰幼兒后,都往往有勒索財物的實行行為。這符合主客觀相統一的原理。綁架罪的主觀目的需要客觀的實行行為來體現。在判斷某一犯罪的主觀方面時,必須以客觀的標準去衡量,而不能主觀臆斷,這是不可靠的。因此,宜將實行目的行為納入判斷既遂形態的標準之中。
第二,復合行為說符合我國的刑事政策,同時體現罪刑相適應原則。把凡是實施了綁架行為的,不管其是否實施了勒索行為,是否占有財物,都認為是既遂,不利于貫徹我國的區別對待、分化瓦解犯罪分子的政策,將既遂標準后移符合我國的刑事政策及立法精神。再者,以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為指引,也理應認定為復合行為并以此完成作為綁架罪的既遂標準。
第三,從本罪侵犯的客體上看,通說觀點認為是復雜客體,即認為侵犯的是他人的人身自由和財產權益及其他個人、社會利益,此觀點也為筆者所認同。在這些客體中,人身自由是該罪最基本、最固定的內容,而財產權益和其他個人、社會利益為法規中的“勒索財物”或“綁架他人作為人質”所侵犯的法益,為次要客體。雖次要客體之侵犯不一定要有實行行為來體現,但一定要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有此目的才成立綁架罪,因此不可或缺。
誠然,綁架罪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犯罪,自現行刑法頒布實施以來,無論是在刑法界還是司法實踐中也都對綁架罪展開過廣泛而激烈的討論,然而對該罪的諸多問題仍然存在著較大分歧。筆者在此也只是對其爭議較多中的一點問題所作的膚淺分析,殷切期待我國的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踐能繼續深入地研究,從而對完善我國現行立法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顧紅艷.綁架罪若干問題研究.網文.
[2]陳興良,周光權.刑法學的現代展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丁慕英.刑法實施中的難點疑點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黃祥清.綁架罪的既未遂標準設定.人民司法.20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