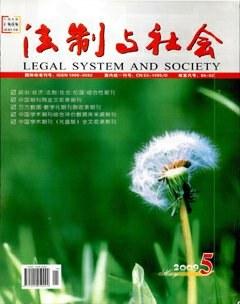大國責任與中國的國家利益
劉振華
摘要隨著中國國家地位和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的“大國責任”問題開始凸顯。中國履行更多的大國責任已是形勢所趨,但同時應該以國家利益為首要考量,強調權責相適、協調發展,實現中國和平崛起。
關鍵詞中國 大國責任 國家利益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09)05-193-02
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特別是經濟實力的迅速提升,世界各國廣泛關注中國,熱議中國的發展變化與崛起道路。西方國家在驚呼中國崛起的同時,還要求中國承擔相應的大國責任,鼓勵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而不能只是成為“搭便車者”。在國內,很多國人在回顧歷史、暢想未來的時候大國情緒開始高漲,也認為中國應該在各種國際事務中有所作為,承擔更多的“責任”。實際上,西方國家所說的“大國責任”與中國一直倡導的“負責任大國”概念之間是存在差異的。中國是否應該按照他們的期待履行大國責任,大國責任的承擔是否符合當前我國的國家利益,這是我國制定和實行對外政策所必須注意的重要問題。
一、中國所面臨的“大國責任”問題
什么是“大國責任”?國際政治學家赫德利·布爾( Hedley Bull) 曾經指出,“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關系中國家擁有權力就要負相應的責任。”。布爾認為,由于國際社會中的各國在權力上不平等,所以大國在享有特權的同時也承擔著維護國際秩序的管理性責任和義務。然而,世界各國對大國責任并沒有明確而一致的規定,維持現有國際秩序成為國際社會關于大國責任的最低限度共識。
中國的大國責任問題,是伴隨著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增長而進入人們視野的。它最開始出現于冷戰結束后,并且發展和演變至今。縱向來看,中國對國際社會所作的貢獻呈不斷擴大之勢,然而國際社會對中國大國責任的期待也水漲船高。
上世紀90 年代中期開始,鑒于中國國家實力的迅速崛起,作為對“中國威脅論”的回擊,中國政府適時地提出了“做國際社會中負責任大國”的外交理念,積極參與國際機制。具體表現在:積極參與地區和全球多邊機制;倡導國際政治多極化與民主化;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采取“負責任大國”作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參與東盟地區合作;強調文化多樣性,呼吁文明共處等。中國在踐行“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戰略的同時,更為注重“有所作為”,顯示出更多的自信與能力,一定程度上已塑造了“負責任大國”形象。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崛起從現實的可能成為存在的現實。2006年,中國的GDP近21萬億元,規模僅次于美日德,并有望在2008年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場”,全球經濟的實際增量約1/3來自中國,直接影響世界經濟的運行。而且,中國大國地位不斷提升,直接影響區域的政治發展,軍事實力也由國土防御型向攻防兼備型轉變,中國成為國際事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隨著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迅速提高,越來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國,國際社會要求中國承擔大國責任的呼聲日盛。
2005 年9 月, 美國時任常務副國務卿羅伯特·佐立克提出鼓勵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希望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2006年8月,接替佐立克的柯慶生表示中國還不是“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認為中國的軍事不夠透明,在國際上的一些作為也令美國失望,因此再次向中國提出了責任要求。此外,歐盟在2006年10月出臺的第六個對華政策文件《歐盟與中國:更緊密的伙伴,擴大的責任》中,也特別強調中國的“責任”。
應當看到,“中國責任論”的興起并非偶然,有著深刻、復雜的國際背景。這既與中國快速發展,實力不斷增強,國際社會寄望中國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有關,又與其它國家希望將中國融入世界體系有關。對于中國一個快速發展且被認為“處于戰略十字路口”的國家,國際社會希望我們能夠多承擔一點國際責任,發揮更大的作用,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履行此類大國責任是否都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是需要我們進行衡量的。
二、大國責任給中國國家利益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國際政治理論的建構主義者認為,身份和利益有著密切關系,國家是具有身份和利益的實體。因此,國家利益的界定,必須明確國家的身份或進行自身定位,并作出相應的判斷。中國雖然是大國,但其地位還無法與美國這種“超級大國”相比。就發展水平、富裕程度和地緣政治影響力來說,中國只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地區大國。中國目前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現在仍然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在發展與復興中的大國。中國的國家利益主要體現在地區安全與經濟發展,以及全球化所帶來的與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聯系。分析中國的大國責任,也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和身份出發。
履行大國責任,是中國實力地位的體現,也是是拓展更多國家利益的機遇。十多年來,中國已通過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贏得了國際聲譽,有效地促進了中國的和平崛起。在亞洲,中國開展睦鄰友好合作,援助東南亞渡過經濟危機,支援印尼地震與海嘯救災,倡導南海的共同開發,為中國營造了和平的周邊環境,促進了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在國際上,中國廣泛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倡導軍控裁軍和防擴散,打擊恐怖主義,參與國際多邊合作,共同應對多種非傳統安全威脅,對于化解“中國威脅論”、樹立大國形象、實現中國國家利益的全球拓展大有助益。新時期的大國責任,只要是與中國當前實際相適應的權責,基本上都是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維護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負有重要責任; 作為世界上重要的核大國, 中國對全球安全狀況尤其是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負有重要責任。作為亞太地區的重要國家, 中國對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大國,也是實現中華崛起和民族復興的良好機遇。
與此同時,我們不能被權責帶來的榮光沖昏了頭腦,更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的現狀來之不易,國內的持續穩定發展仍是第一位的。中國雖然現在經濟發展速度較快,有了一定的物質基礎,但是人均GDP仍然在世界第一百位之后,長期的過度開發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問題,東西部發展嚴重不平衡,仍然存在大量貧困人口,這些問題的存在決定我們還不適合過早地承擔過多的責任。國際上,不同國家和力量要求我們承擔大國責任的目的是不同的。例如,中國要成為美國標準的“利益攸關方”,可能要承擔的責任就包括大幅升值人民幣、按西方標準減排二氧化碳、孤立伊朗遏制朝鮮、繳納大量聯合國會費、為美國制造的戰亂國家提供援助等。要滿足歐盟的標準,雙方作為伙伴就需要負有對等的責任,不過作為處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兩個政治實體來說,強調對等責任對實力較弱的中國來說,會造成巨大的壓力。此外,在經濟方面,大國經濟責任主要包括:維護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與規則,參與解決日趨嚴重的全球失衡和環境問題,擴大金融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及增加國際援助等。以上大國責任的過度承擔將增加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本,擴大我對外援助支出,加劇各項制度改革的風險。
由此可見,西方大國之所以要求中國履行大國責任,有其認可中國實力崛起的一面,但另一面是想把中國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推行其全球政治霸權與經濟殖民主義作推手,甚至想借“盡責”來拖累中國既定戰略的實現,要求我在享受和平與發展“紅利”的同時進行“納稅”,一定程度上制約中國的經濟進程與軍力發展,這是美國“接觸加遏制”戰略的政策體現。
三、中國的現實性選擇:以國家長遠利益來衡量
中國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發展,一方面要抓住機會埋頭苦干、解決問題,另一方面要努力化解“中國威脅論”的影響,這就決定我們必須妥善地應對大國責任,實現和平崛起。如何解決利益與責任的問題以及國內與國外的關系,需要結合本國能力與國際情勢綜合判斷。
從正面來看,國際社會用橄欖枝來編織“大國責任”,雖然可能包含著其它目的,但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機遇大于挑戰,我們不妨聰明而又大方地接收,進行評估后再行實施。一味地把別國的好意視為“洪水猛獸”,“糖衣炮彈”是不合適的,自己在猜忌的同時也會增加其它國家的戰略懷疑。一個國家的崛起靠的不僅是經濟、科技和軍力的發展,在當代還依靠諸如外交政策、文化與意識形態等“軟權力”因素,而軟權力的建立更需要日積月累、慢慢形成。中國的國際聲望(或軟權力影響力)總依靠常任理事國的“老本”是不夠的,必須“開源”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和更大的拓展。但是不能等到急切需要時才去做相關的工作,必須未雨綢繆、預做準備。因此,當前適當承擔大國責任,例如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強合作與互助,改變一味重視自身發展的“自私”印象,積極參與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揮主導地區安全環境的角色,更多地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等,對于提高我國國際聲望,降低西方國家敵意,提高周邊國家向心力等都有很大的幫助。
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自己必須看到超出能力的大國責任可能會對我國帶來的制約。因此,必須量力而行,同時學習美國那種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美國作為全球首強,在大國責任的履行上也經常持兩種標準,一味要求別國承擔責任,但在關系國家重要利益的問題上自已絕不讓步。例如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撕毀《反彈道導彈條約》,違抗《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拒不批準《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拖欠聯合國巨額會費,堅持農業保護主義等。中國要承擔大國責任。我們對別國開列的要求清單也不能照單全收,而應該根據情況區別對待。我不能透支去承擔那些本不該去承擔的“責任”,但可以量力而行且不違反道義地為世界做一些扎扎實實的事情。此外,中國還需要強化對外宣傳,讓世人了解我們所作的貢獻。它不僅包括對外的大國責任,還有國內的國家責任。因為中國解決占全球1/5人口的發展問題,就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所盡的最大責任。
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國內民眾的基本富裕和國家基本安全仍然沒有完全解決,它的本土責任仍然重大,而在地區主義的建構方面遠遠與它的地區大國身份不相稱。因此,中國目前的大國責任重中之重應該放在地區層次,同時繼續追求適當的全球責任。中國雖然不必像俄羅斯那樣表現出對世界權力的渴望和恢復強國地位的急切,但我們可以高姿態地接受“大國地位”并承擔合理的大國責任,而不必畏首畏尾,失去大國的風范。對于國際義務的履行,我們不唯上(美國),不唯書(教條),應當根據自身的理解進行責任的承擔。如果要我們大幅犧牲經濟發展來盡責任,或者要我們犧牲重要國家利益,那我們絕對不能答應。但是,作為一個擁有常任理事國席位和世界第三的經濟體,不能長期游離于大國責任的邊緣,我們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雖然我們人口眾多、人均GDP量小,但是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負擔轉化為優勢,并為全球提供有益的幫助。例如我們可以向聯合國派出更多的國際維和部隊、警察和民事人員,向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國家加大提供醫療、公共事務援助,大力興建教育、醫療場所,少花錢、多出力、多做事,把中國人勤奮的美德、以和為貴的思想和禮儀之邦的傳統帶向全世界。
換個角度看,大國責任還是一種權力,它與國家利益是相輔相成的。履行更大的責任,是為了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和長久化。滿足了國家利益,又會更主動去承擔更多的重任。以國家長遠利益為準繩,來衡量和履行中國的大國責任,是中國在崛起道路上的現實性選擇。
注釋: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Macmillan, 1977.206 – 209.
溫特·亞力山大.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0年版.第281頁.
肖歡容.中國的大國責任與地區主義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1).第49頁.
參考文獻:
[1]方長平.國家利益的建構主義分析.當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2]江涌.大國責任的挑戰.瞭望.2007(41).
[3]李寶俊,徐正源.冷戰后中國負責任大國身份的建構.教學與研究.2006(1).
[4]林濤.和諧世界: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戰略主張.新疆大學學報.2007 (11).
[5]秦治來.開放條件下的中國國家利益.大家思考.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