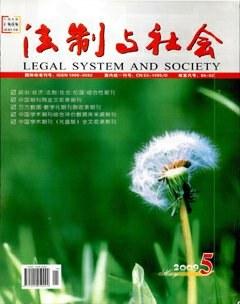刑法罪過與侵權法過錯之比較
周雪梅
摘要刑法上之罪過和民法上之過錯,作為不同部門法歸責原則之核心,雖都關涉行為人的內心狀態,但基于刑民法之不同任務及不同歸責理念,兩者有著顯著的實質性區別。在罪過和過錯的評價基點、故意和過失的區別度、過失的范圍及被害人過失等問題上,兩種部門法給出了不同的解說。
關鍵詞刑事罪過 侵權過錯 故意 過失
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09)05-330-02
刑事和民事的分立,是現代各國實體法律制度中一種基本的制度格局。這種格局,是隨著近代社會公法和私法的逐步分化而漸次成型的。現代意義上的侵權法和刑法的分立,是隨著歐洲中世紀法的消失,國家提起的刑事訴訟從私人提起的訴訟中獨立出來開始的。一般法律傳統認為,刑法和侵權法分屬不同的法領域,當然具有各自的獨立性。面對損害,刑法和侵權法通過程序適用和責任效果的差異,向社會民眾傳遞各自的價值所在。與刑法和侵權法分立形影相伴的是面對損害的法律適用又常常還有重疊之處。如何應對并化解重疊臨界處的沖突,對刑法和侵權法歸責原則的核心“罪過”和“過錯”作深入的解讀。以期能為司法中的損害分類處置提供一種視角和合理解釋。
“自從羅馬法學家對故意和過失這兩個概念的使用作了區分以來,西方傳統中的法學家就依賴這對概念來分析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西方的全部法律文化都承認,故意實施的違法行為和過失實施的違法行為之間有不同,但是人們對它們承擔責任形式的外部界限和內部含義卻有著很大的不同看法”。對于“故意”和“過失”這兩個概念,我國刑法總則中明文規定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對規范中的 “故意”和“過失”,刑法理論一般將其合稱為罪過,刑法學者也就多在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對罪過進行理解并在實質上對故意和過失進行詳盡解釋。而在民事侵權領域,故意和過失僅僅被作為過錯的基本方式在理論上加以討論,民事侵權規范意義上多被表述為行為人的“過錯”。
刑法規范界定故意和過失,民法規范界定過錯,在理論層面刑法將罪過作為犯罪構成不可或缺的核心評價要件,潛心研究故意和過失的各種形態并為嚴格界定其本身提供標準。在民事侵權中過錯理論涵蓋故意和過失但不限于二者,其理論解說重點更多在討論判斷過錯的標準,而非區別故意和過失本身。刑法和侵權法面對同為行為人心理層面的故意和過失,規范界定方式不同、理論爭論焦點迥異的根源正是法域的價值取向不同所導致的。
一、“過錯”與“罪過”
過錯和罪過的本質雖都指向人的內心狀態,但作為不同法域的歸責原則,對于各自的本質闡釋和判定標準卻有著不同側面的理論解說。
(一)“過錯”是對行為本身的評價
侵權法所確定的法律秩序表達這樣一種觀念:“所有權人自吞苦果”,他人只有實施了不正當行為,才可能替代遭受損失的人承擔責任。為此,在什么條件下應由他人承擔責任,也就是將損失歸責于他人的原因和標準就一直視為侵權法的中心論題。就侵權法的發展來看,過錯理論目前仍是侵權法歸責的基礎理論,對過錯的本質屬性及認定標準的爭議從過錯責任取代結果責任后就持續不斷,針對過錯的非難指向的是需查證的行為人故意或過失的心理狀態還是行為人的外部行為,存在著主觀過錯說和客觀過錯說的爭論。主觀過錯說認為,過錯是行為人主觀上應受非難的一種心理狀態。過錯并不包括行為人的外部行為,由于行為人的內在心理過程無法自我表達,因此在歸責時,還必須根據行為的違法性來作為確定行為人應對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的根據。客觀過錯說認為過錯是指法律用客觀的標準對行為人行為進行評價,違反了該行為標準就表明了行為人具有過錯,而無須探究其內心狀態。19世紀早期主觀過錯說是侵權法的主導理論,而到19世紀后期,客觀過錯說在民事侵權立法和司法中已被采納和廣泛運用。
侵權法領域過錯學說之爭重心在于法律作否定評價的關節點落在那里,在要求加害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時其根據是行為人的主觀心理還是外在行為本身。由于客觀過錯說通過法律上擬制的人的行為模式作為期待人們所為的行為準則,使過錯的判斷不再是單純的哲學或道德上的范疇,這樣法律的非難就有了相對清晰、明確的指引。表現在民事司法實務中,“與認定過錯問題相關聯的事實是行為人有怎么樣的行為而不是行為人的心理狀態或意志狀態,只有行為方式是實存的能由證據證明并由經驗所感知的”。由此看來“過失的客觀化醇化了傳統個人主義的過失責任,不再強調行為人道德的非難性,而著重于社會活動應有客觀的規范準則。”
(二)“罪過”是對行為人內心狀態的評價
各國刑法中的罪過原則普遍認為只有有目的、明知和輕率的行為才能構成犯罪。構成犯罪應當具備其中一種心理狀態。只有按照這一歸責原則,犯罪行為才能限于那些在倫理上有罪過、反映出人格缺陷、人們可在行為時避免的行為。與侵權法民事過錯判斷標準不同的是,刑法中罪過的非難直接指向行為人的內心狀態,而不是僅憑行為外在樣態及客觀損害后果要求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究其原因,刑法的基本理念認為人的罪過真實的取決于他的心靈和精神的內在狀態,而不是外在行為,外在行為的實際存在和違反了法律規定的事實只能為刑事反應的開始提供根據。
由于罪過的實質就是行為人對對法律所保護的社會價值持敵視、蔑視或者漠視、輕視的態度。正是有了這種態度,行為人才會形成抗法性的意識,當這種意識外化為具體的行為時就轉化成罪過 ,成為支配行為人實施危害行為的內在動因。犯罪行為實際上是行為人的主觀罪過在現實中的展開。所以在認定罪過的標準上,主觀罪過的條件永遠都是個別的和特殊的,不僅在每一個罪犯身上而且也在每一單個的犯罪之中。它們具有的不是外在的生理和物理性質,而是內在的心里和精神本質。因此法律的非難關節點一直落在犯罪人的主觀層面。
二、故意和過失的區分
(一)“罪過”評價需要嚴格區分故意和過失
在刑法中,故意和過失都是責任條件,所以,因故意而成立犯罪的以及刑法明文規定得以過失成立犯罪的,都要承擔刑罰后果。行為在故意或過失的主觀心態支配下,即使法益侵害沒區別,刑事責任承擔上卻相差甚遠。因此區分故意和過失成為刑法主觀罪過歸責層面首要的任務。對二者的區分在刑法上是通過界定故意的界限完成的,關于故意的本質先有“意志說”和“認識說”,后繼有“蓋然說”和“容認說”,這些學說重在尋求成立故意的認定因素,以排除過失情形不合理的納入故意之中。目前容認說在德日及其他大陸法系國家普遍得到實務和理論的認同。容認說認為行為人具有實現構成要件的意志因素時,才成立故意。但這種意志不以意欲、目的、希望為必要,只要有消極容認、放任、同意危害結果發生就成立故意。
在我國故意和過失這兩種罪過形式的界限,在認識因素上看行為人對自己的危害行為造成危害結果有無認識及認識程度;在意志因素上看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態度如何。在這兩個判斷標準中,意志因素上的法敵對意思的強弱或有無迄今為止一直是區分故意與過失的主要標準,也就是說對法益受害的結果所報持的接受或反對的態度就成為故意與過失區別的主要依據。“由于故意表明反對、敵視規范并對犯罪后果追求、容認的心理態度,因此刑法處罰每一種犯罪的故意犯,故意犯也因此成為最基本的犯罪形態,故意責任亦成為最基本的歸責形態。與此相反,由于過失犯欠缺明顯的法敵對意思而僅僅是對法益保護不夠專注,刑法處罰過失犯的重點就不在它對規范的敵意,而是僅僅對其“不專注”而選擇性的根據特別防衛社會目的決定其處罰范圍,以填補法益保護的漏洞。而過失犯由此成為特別的歸責形態。”
(二)“過錯”化解了故意和過失區別的意義和功能
侵權損害賠償的作用在于將風險責任轉由侵害行為人承擔,并由此來減少損失。在責任承擔時會考察侵害人行為的不正當性,而過錯責任客觀化趨勢,不再考慮行為人心理層面不同而導致規范譴責程度的差異。另一方面侵權法在一百多年的發展時間里,價值取向已經從承擔過錯轉移到了補償損失,也就是淡化責任承擔而強調損失補償的觀念。面對行為引起的實際損害,無論故意和過失體現的過錯性有何區別,均會要求行為人對損害后果承擔責任,并且在責任程度上沒有明顯差別。由此看來,民法上的侵權行為不區別故意和過失,責任相同,刑法上的犯罪,因故意過失而責任各異。原因在于,一個是以賠償被害人的損害為主旨,另一個是以矯正犯罪人的非社會性為目的,趣意不同,結果當然有差異。
三、對過失的不同討論
在侵權法中,過失的行為人之所以在法律上應負責任,不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沒有預見或沒有認識,而在于行為人的行為背離了法律和道德對其提出的應對他人盡到適當注意的要求,以至于其行為造成對他人的損害。哈特教授認為,過失是“行為人沒有奉守任何有理智的正常人本來可以遵循的行為準則,而這一準則就是要求行為人采取預防措施,以免造成危害。……過失不是一種諸如‘他的內心一片空白之類的直接說明心理內容的措施。”哈特教授的此番解說從一側面說明,作為侵權法價值評價中的過失,法律關注的不在于行為人內心是疏忽或懈怠而對結果未能預見或注意的狀態,而是行為人違反對他人的注意義務并造成對他人的損害。行為人對受害人應負的注意義務的違反是行為人負過失責任的根據。所以,在判斷行為人的過失時,也無須像刑法中區別行為人是過于自信還是疏忽大意過失,只需直接運用客觀尺度,根據行為人的行為來考察其是否具有過失。因此,過失行為的種類在侵權法沒有限制,即便是輕微的行為,只要說具有過失,也能認定賠償責任。
刑法從實質內容來說,“過失是一種與故意截然不同的罪過形式。故意的內容由有關犯罪行為的真實的心理因素組成,而過失則基本上是一種法律的評價,即對主體是否遵守與其行為相關的注意義務的判斷”。注意義務是確定行為是否正當的標準,過失犯罪首先是違反了注意義務,但是注意義務的違反引起了刑事責任的問題,卻不是刑事歸責的內容本身。因此注意義務在體系上先于主觀特征,而不是主觀特征的內容本身。所以對于過失的注意義務范圍,有學者認為應當嚴格地以法律(法規、規章、條例等)的要求為依據。認為沒有違反法律規范要求的和行為人自己的行為所產生的注意義務,就不存在過失心理。在為實現報應、預防而發揮作用的刑事方面,刑罰的必要性和損害賠償相比是間接的。由于處罰過失為例外,因此,在刑事方面過失注意義務的范圍不但在規范層面有明確的依據,在法律解釋上也嚴格限定擴大解釋,也就是只有相當高程度的過失才受到處罰,輕微的譴責可能性被排除在外。
注釋:
①[美]邁克爾·D·貝勒斯.法律的原則——一個規范的分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249頁.
②[美]喬治·P·弗萊徹.蔡愛惠,陳巧燕,江溯譯.刑法的基本概念.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頁.
③[德]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著.齊曉琨譯.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
④喻敏.對侵權行為法中過錯問題的再思考.現代法學.1998(4).
⑤王澤鑒.侵權行為法·基本理論——一般侵權行為.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頁.
⑥張明楷.刑法學(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217頁.
⑦于改之.刑民分界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8-69頁.
⑧王覲.中華刑法論.中國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頁.
⑨[美] 哈特.王勇等譯.懲罰與責任.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頁.
⑩[意] 杜里奧帕·多瓦尼.陳忠林譯.意大利刑法學原理.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頁.
馮軍.刑事責任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