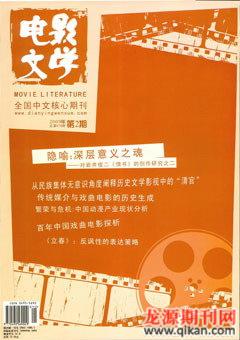殘雪小說(shuō)的女性主義解讀
王建斌 馬 超
[摘要]殘雪從1985年開(kāi)始發(fā)表作品至今持續(xù)20年一直受到關(guān)注,人們對(duì)殘雪作品的評(píng)價(jià)20年來(lái)一直存在著嚴(yán)重的分歧甚至對(duì)立。殘雪以女性化了的怪異感覺(jué)對(duì)現(xiàn)存的男性話(huà)語(yǔ)進(jìn)行了徹底的顛覆和解構(gòu),表現(xiàn)出極強(qiáng)的獨(dú)立思維能力和創(chuàng)造欲望。其作品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女權(quán)主義思想和現(xiàn)代主義色彩,這也是她引起評(píng)論界,特別是國(guó)外評(píng)論家關(guān)注的原因之一。
[關(guān)鍵詞]突圍與表演;殘雪;女性主義
殘雪作為中國(guó)當(dāng)代最有爭(zhēng)議的一位女作家,評(píng)論界對(duì)其謎一樣的作品進(jìn)行猜謎式的解讀曾形成了一個(gè)特定的“殘雪現(xiàn)象”,殘雪從1985年開(kāi)始發(fā)表作品至今持續(xù)20年一直受到關(guān)注,這在各領(lǐng)風(fēng)騷三五天的新時(shí)期文壇上實(shí)屬奇跡。值得注意并耐人尋味的是對(duì)殘雪作品的評(píng)價(jià)20年來(lái)一直存在著嚴(yán)重的分歧甚至對(duì)立:評(píng)論界的熱鬧與讀者的冷落、國(guó)外好評(píng)如潮與國(guó)內(nèi)批評(píng)界的相對(duì)滯后、奉為經(jīng)典的交口稱(chēng)贊與一無(wú)是處的指責(zé)等等,不管我們?nèi)绾慰创龤堁┑淖髌罚珜?duì)“殘雪現(xiàn)象”的關(guān)注和研究無(wú)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在20年來(lái)對(duì)殘雪的研究中,從文本試驗(yàn)的方面、從存在主義的角度、從心理分析的方向、甚至地域文化的途徑都進(jìn)行了許多探索,本文試從女性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上來(lái)重新解讀殘雪。
上世紀(jì)80年代中期,西方思潮全面涌入中國(guó),面對(duì)紛亂如萬(wàn)花筒般的文藝思潮,殘雪等先鋒派作家應(yīng)運(yùn)而生,殘雪以她女性特有的敏感與奇特得有些神經(jīng)質(zhì)的臆想方式營(yíng)造了一個(gè)夢(mèng)魘迷幻世界,由于這種極其個(gè)人化的體驗(yàn)使得進(jìn)入這一世界對(duì)于讀者來(lái)說(shuō)顯得格外困難,所以盡管某些評(píng)論家和出版商試圖聯(lián)合導(dǎo)演“殘雪年”,而最終以失敗告終,但在所謂的純文學(xué)普遍衰落、先鋒派作家進(jìn)入90年代后“勝利大逃亡”的時(shí)代大潮下,殘雪這一面“先鋒”的旗幟卻一直未倒,并引起了西方評(píng)論家的極大興趣。
殘雪的《突圍表演》一書(shū),堪稱(chēng)世紀(jì)之交的中國(guó)女權(quán)文學(xué)宣言,其對(duì)大男子主義的否定和叛逆達(dá)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她將女性體驗(yàn)提升到改造國(guó)民性這一理性層次進(jìn)行重新審視、重新認(rèn)知,從而為詮釋女性的生命狀況注入了全新的理念內(nèi)涵。無(wú)論從思想的開(kāi)掘之深或者作品的藝術(shù)信息密度來(lái)看,《突圍表演》都堪稱(chēng)中國(guó)優(yōu)秀的女性文學(xué)作品。無(wú)論從智力潛能、文化層次、情操修養(yǎng)、心理承受能力和實(shí)際行動(dòng)能力方面,她們都遠(yuǎn)遠(yuǎn)超越了五香街的男人,以至于所有的大事都是由女人們干出來(lái)的;或者說(shuō),五香街的世界是女人味十足的世界,而那些軟弱和慵懶的男人,至多只能做個(gè)陪襯而已。作品中的女性表現(xiàn)出極強(qiáng)的獨(dú)立思維能力和創(chuàng)造欲望。總之,五香街文化是地地道道的女性文化,每一個(gè)女人都敢作敢為,風(fēng)流偉岸,那一份女性的自信與成熟、廣闊的思想視野以及由此而產(chǎn)生的文化精神、批判精神和創(chuàng)造精神,正構(gòu)成了五香街女性文化的本質(zhì)特征。
在殘雪的創(chuàng)作欲望中,包含著強(qiáng)烈的破壞欲和毀滅欲,她自覺(jué)地去破壞男權(quán)價(jià)值觀和審美觀。傳統(tǒng)男權(quán)視角專(zhuān)一描寫(xiě)女性的美,寫(xiě)女性如何具備羞花閉月之容,沉魚(yú)落雁之貌,這就在將女性捧為美的偶像的同時(shí),把女性的獨(dú)立人格給悄悄地置換掉了。在男人眼里,女人不知不覺(jué)地變成了花瓶,變成了尤物。殘雪則以自己光怪陸離的作品,將男權(quán)主義的審美趣味進(jìn)行徹底的顛覆和解構(gòu)。她大量采用直覺(jué)、夢(mèng)幻、無(wú)意識(shí)、扭曲變形等手法,運(yùn)用噩夢(mèng)式的故事和荒誕的處理來(lái)解構(gòu)男性審美趣味。《公牛》中的小女孩,整天在做著白日夢(mèng),即使看見(jiàn)樹(shù)上晾的一張床單,也會(huì)揣測(cè)那是用來(lái)包裹媽媽的尸體用的。她外表也同樣丑陋不堪,限里流著綠眼屎,舌尖上長(zhǎng)起了黃豆頭大的血泡。《山上的小屋》中那個(gè)小妹妹,像男孩子一樣滿(mǎn)山亂竄,專(zhuān)以玩弄死蛾子死蜻蜒為樂(lè)。姐姐卻不停地做著下流的夢(mèng),胃里還結(jié)出了小冰塊,成為莫名其妙的人格變態(tài)者。《霧》中那些女人們,“突然都失去了原形,變成了一些捉摸不定的影子”,而且“每個(gè)人都變得很急躁、古怪、甚至輕挑起來(lái)”。《天堂里的對(duì)話(huà)》那位女郎,“小腿變得柔軟而冰涼,胸口有一個(gè)很大的窟窿,潮濕的小石頭在里面嘩啦作晌”,讓每一個(gè)男人想起來(lái)就惡心。《關(guān)于菊花的遐想之二》中的女孩,衣袋里永遠(yuǎn)裝滿(mǎn)了她掐死的蟲(chóng)子,她還不停地撒謊說(shuō)“那是她采集的玫瑰”。至《蒼老的浮云》中的慕蘭,她老是不停地吃著椿樹(shù)花熬的湯,并且不停地放臭屁。她那古怪、晦澀、荒誕的夢(mèng)囈式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文學(xué)界如此強(qiáng)烈的驚訝與不滿(mǎn),正是因?yàn)樗_(kāi)創(chuàng)了同傳統(tǒng)文學(xué)格格不入的趣味。殘雪的藝術(shù)世界體現(xiàn)了不僅是激進(jìn)的而且是積極的文學(xué)價(jià)值。這就是女性的特質(zhì),而女性想象力無(wú)非是將女性特質(zhì)藝術(shù)化和具體化罷了。殘雪創(chuàng)作的最大特色,也恰恰在于這類(lèi)非同凡響的女性想象力。她不再訴說(shuō)男人的語(yǔ)言,也不再是模仿男性聲音的口技表演者,而是用女性話(huà)語(yǔ)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亦真亦幻夢(mèng)境般的女性藝術(shù)世界。
殘雪作品中表現(xiàn)出的女權(quán)主義思想,也許只是她不厭其煩地重復(fù)表現(xiàn)現(xiàn)代人的“異化”處境時(shí)的副產(chǎn)品,以致有人認(rèn)為其作品與女性主義無(wú)關(guān),其實(shí)我們可以看出殘雪追求的正是女性主義發(fā)展的第三階段一“女人”階段,其作品夢(mèng)一樣的場(chǎng)景和非理性的、也非正常態(tài)感覺(jué)的敘述都是對(duì)男性話(huà)語(yǔ)的徹底顛覆。盡管殘雪不斷地強(qiáng)調(diào)卡夫卡等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大師和西方現(xiàn)代哲學(xué)對(duì)自己的影響,但從閱讀作品中我們依然真切地感覺(jué)到支撐其形成這種夢(mèng)幻敘述風(fēng)格的基礎(chǔ)實(shí)際上還是她那種非常態(tài)的、極度夸張了的女性所特有的敏感、直覺(jué)、臆想等個(gè)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