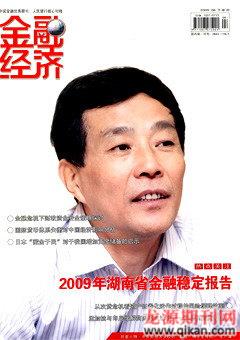大危機是經濟重心轉移過程中的必然現象
任遠果
一、新興經濟體競爭力的不斷增強與發達經濟體產業空洞化的趨勢
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較長時期內分別處于全球制造體系的低端和中高端,兩者為互
補關系。但隨著新興經濟體產業的不斷升級,對發達經濟體的中高端制造業產生了競爭壓力,并不斷向新興經濟體轉移。這便造成了發達經濟體實體產業空洞化的趨勢。
從數據上看,90年代以來中國制造業和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是不斷提高的。但中國工資成本較低,而美國勞動力工資成本相對較高,從而中美之間勞動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為例,按照現行匯率計算,美國制造業工資是中國的29.2倍,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19.2倍。20世紀90年代以來,無論是工資增長率,還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中國都明顯高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1990年-2001年,中國分別提高了 1.04倍和1.29倍。雖然兩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均快于工資增長率,但是中國的速度明顯快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工資增長率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比重,中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國從1990年的 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更快于工資的增長速度,從而在中美貿易中,中國產品就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在現行的中美匯率保持相對穩定的條件下,中國對美國出口就會增加,從而表現出貿易順差,而美國則是貿易逆差。
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中國不僅培養了大批熟練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積累了較為豐富的人力資源,而且未來的潛力更大。據統計,2005年中國在校大學生人數有2300萬人,而美國為1660萬人,中國在校大學生人數已遠超過美國,并且中國大學生中理工類學生占50%左右,美國僅33%,中國科技人員的后備力量相當充足。而且中國科技人員成本僅為美國的1/5至1/8,這為中國加快技術進步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例如深圳比亞迪公司積極發展新能源汽車,在其核心技術汽車電池方面集中了上1000名科技人員攻關,而美國這方面科技人員全部加起來也不足1000人。因此,該公司研制的新能源汽車敢于向美日挑戰,這是巴菲特堅決看好該公司的重要原因。
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實現產業大轉移后,出現了實體產業空洞化的趨勢。美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已經從1990年的28%下降到目前只有13%。自1981年以來,美國就再沒有出現過經常項目順差,并且在過去的20多年,貿易逆差從幾十億美元急劇擴大到2007年的超過8千億美元。美國經濟構成中高度依賴服務業,尤其是房地產和金融業,這兩個經濟部門在頂峰時期一共占到GDP的78%。
自本世紀初科網泡沫破滅后,自80年代后期引領美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信息產業技術在趨于成熟,并向全球擴散。美國所具有的技術創新優勢有所弱化,但高成本的劣勢卻突顯了出來,美國經濟的競爭優勢已受到削弱。因此,2001年科網股泡沫破滅后美國經濟應有一個自然衰退的趨勢,但美國通過虛擬經濟成功制造了次貸泡沫,人為延長了美國經濟的繁榮期。
二、美國經濟面臨去成本的壓力
目前市場高度關注金融危機,但金融危機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其背后的實質是實體經濟問題,因為這是由許多長期因素積累而成的結構性大調整問題。目前美國出臺的各種救市計劃都在力求解決金融危機,即使金融危機得到解決,實體經濟問題也不一定能夠得到真正解決。
美國實體經濟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供應而不是需求問題,因此,凱恩斯主義通過財政赤字刺激需求的政策不一定有效。但供應問題的背后是成本問題,傳統的供應學派降稅的方法可能也難以解決問題,因為勞動成本高,在美國生產不經濟。
面對中國的競爭,美國經濟將會有一個去勞動力成本的問題,即要降低工資福利,而這勢必影響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消費能力,對美國經濟將形成較長期的壓力。美國去勞動力成本有幾個實現方式,第一種方式是直接降低工資福利,這會非常痛苦,而且會面臨工會、輿論等各方面的政治壓力;第二種選擇就是那些高成本、無競爭力的企業大規模的破產倒閉,這有可能帶來經濟的蕭條;第三種方式就是發行貨幣,貶值本幣,以降低比較成本和實際成本,減少進口,增加出口,增強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擴張性貨幣政策也有助資產價格的回升,減輕國際債務,因此,美國選擇第三種方式的可能性很大,這是由美國內在經濟因素和國際經濟格局所決定的。雖然這可能使美國經濟陷入滯漲格局,但兩害相權取其輕,滯漲或許比大蕭條要好。當然還有第四種選擇,那就是再推動一次新的技術革命,發揮美國的科技優勢,恢復美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但現在還看不到有能象信息技術那樣深刻而廣泛影響全球經濟的新技術革命,這也是很難速成的,即使有,也可能會面臨來自中國的競爭。實際上作為一個綜合的經濟政策,上述幾種方式可能都會綜合運用,但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美國采取大量發行貨幣應對危機的方式將可能是最主要的選擇。如果美元大量發行,將迫使人民幣升值,同時美元相對貶值,否則高通脹必將傳導至國內。
三、中國將以提高國民福利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由于中國在較長時期內實施出口導向型戰略,形成了龐大的產業鏈和巨大的生產能力,但目前外需遇到了問題,外需增量部分基本消失,產能過剩的壓力突顯。這表明中國經濟已面臨東亞模式的陷阱。
在實施出口導向型戰略中,通常會以犧牲國民福利來壓低勞動力成本,以增強國際競爭力。以中國13億人口之眾,并且不斷進行產業升級,繼續實施低成本的出口導向型戰略,最終全球發達經濟體的主要實體產業將被嚴重掏空,而中國自身也不過是生產出大量過剩的產品,這對全球經濟將會產生極大的壓力,也會對中國自身的發展不利。這可能也是產生中國威脅論以及西方國家指責中國的原因所在。
因此,中國經濟增長需要尋求新的增長動力,那就是通過提高國民福利創造龐大的內需市場來推動經濟增長。這不僅可以使中國經濟增長擺脫對外需的過分依賴,更具內生的持續性,也會使全球經濟增長更加平衡。
提高國民福利有著多方面的途徑,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等,關鍵是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能力。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改變二元經濟結構。在實施出口導向型戰略階段,二元經濟結構可以無限地提供低成本的勞動力,成為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來源。但要轉向以內需為主的發展階段,二元經濟結構必然是一個障礙。因為中國的農村經濟具有很強的自然經濟特征,生產效率較低,加之缺乏社會保障體系,對商品的消費能力必然較低。
通過城市化建設以及建立廣泛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是解決二元經濟結構一個重要的途徑。中國已進入到工業化的中后期,但城市化建設還處于初中期,城市化建設本身存在缺位,應大規模建設非商品化住宅滿足大量低薪階層的住宅需求。城市化建設以及所帶動的基礎建設可以拉動投資,從而帶動整個GDP的增長;城市化建設可以減少農村人口,有助提高農業的集約化經營;城市化尤其是都市化建設帶來的人口積聚效應有助于發展服務業,增加就業機會,并可以改善教育,全面提高人口素質,并有助于實現社會穩定。如果這輪金融危機對中國有什么機遇的話,那就是這輪危機緩解了中國面臨的資源瓶頸,為中國展開大規模建設提供了較低廉的資源。通過城市化建設逐步解決二元經濟結構問題也是實現國家現代化必要的一個步驟。
城市化建設需要大力改善社會保障體系,并通過社會保障體系來緩沖經濟波動時的就業壓力,不能長期依靠二元經濟和人為刺激GDP增長緩角就業壓力。社會保障體系的實質就是將一部分供應能力轉化為公共消費能力。中國目前有著充足的勞動力和生產能力,增加部分供應不是什么難題。此外,通過提高國民福民,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費能力,可以加快汽車消費普及,以及其它消費升級等,為國內經濟發展創造巨大的市場空間。
中國展開大規模基礎建設和城市化建設可以代替原來由出口帶動的產業鏈條運轉,但這只是一個過渡性的階段,這可以為中國走上以技術創新提升經濟效率的增長方式爭取時間。
未來中國產業結構上或許應實現三足鼎立,即高新技術產業、中低端制造業和服務業并舉。以技術創新的高端制造業提升勞動生產率,以中低端制造業和服務業解決就業,將第一產業勞動力部分向第二產業但重點向第三產業轉移,應在勞動生產率提高、GDP增長、就業和國民福利之間取得適度平衡。
從以上分析來看,只要有適當的經濟政策,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國經濟仍有內在的強勁增長動力。
四、金融深化將是促進經濟轉型的重要因素
要把中國在宏觀要素積聚的優勢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增長優勢,特別是要走以技術創新來推動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推動經濟發展的道路,則必須要靠一大批創新型的民營企業來帶動。而金融深化對推動技術創新和提高經濟效率具有重要影響。
中國是全世界金融約束較強的國家。但我們也可看到金融約束并沒有妨礙中國經濟過去多年來的高增長,原因在于中國經濟具有低成本勞動力的優勢,在外需強勁的帶動下,一直以要素投入為主的增長方式高速發展,金融約束對經濟增長沒有太大的阻力。所以各方呼吁的利率市場化、發展直接融資等改革政策都是遲而不到。但中國經濟要擺脫東亞模式陷阱,必須進入鼓勵創新型企業發展、以經濟效率提升為主推動經濟發展的新階段,金融深化是必不可少的一個推動力。金融深化或金融市場化可以真正讓金融市場具有風險定價能力,從而實現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在現有的政策格局下,使得大量金融資源向壟斷型國企集中,真正具有創新動力的大量民營企業卻無法得到金融資源的支持。所以現有的金融體系難以適應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內在要求,金融深化勢在必行。
經過近幾年的金融改革,中國的國有銀行大部分都已改制上市,中國銀行業的資本實力大為增強,不良資產大大降低,盈利能力得到很大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經營管理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都有較大提高,這在客觀上都為推進利率市場化等金融深化政策創造了條件。
目前中國的金融體系距發達國家金融體系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中國和美國剛好相反,美國是金融業過度繁榮,而中國則是金融業發展不足,而金融深化是推進中國金融業發展的重要途徑。金融深化首先是國內金融體系的市場化,包括利率市場化、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充分發展債券市場等。同時金融業經營主體也將進一步實現市場化的多元經營,以擴展范圍經濟和分散風險。國內金融市場化發展到一定的階段,金融體系承受風險能力增強以后,將為金融體系的國際市場化即以匯率市場化為核心的金融深化創造條件,中國才可望真正建立國際性的金融中心。
從歷史上看,經濟重心轉移過程必然產生重大危機。因為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總會導致全球產能的擴張和過剩,原有的供求平衡關系將被打破,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全球性的經濟大調整,通常會表現為重大的金融或經濟危機。這實質上是一個大范圍的經濟洗牌過程,或者說是一個創造性的毀滅過程。通過這一過程將會淘汰那些缺乏競爭力的產能,而具備競爭力的新興經濟體則將在危機后再度崛起,并提升其經濟地位,形成新的經濟重心。原有經濟霸主的地位將被削弱,并走向相對衰落。
在20世紀20年代末的大危機就是全球經濟重心由歐洲向北美轉移過程中的一次經濟大調整,美國此后逐步成為全球經濟霸主,英帝國則走向相對衰落。70至80年代日本開始崛起,向美國發出了挑戰,美國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滯漲壓力,美國普遍充斥了日本威脅論,但日本的經濟潛力并不足以完成這一挑戰,最后以失敗而告終。而目前這輪危機則是經濟重心從歐美發達經濟體向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轉移的一次契機,同時也是對中國經濟潛力的一次考驗。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可以看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有兩個關鍵素,其一是比較穩定的社會環境,其二是以中國式智慧成功引入了市場經濟制度。近三十年中國系統性地引入和深化市場經濟,帶來了13億人口之眾的大國前所未有的巨變,也帶來了全球物質產品的極大豐富。可以說中國成功引入市場經濟制度實現了一次生產力的大解放。只要能繼續保持這兩個關鍵因素,并施以正確的經濟政策,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潛力仍將是巨大的,足以推動全球經濟格局的改變。
目前金融危機正是這一經濟重心轉移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短期內對全球經濟的壓力不會消失。而中國自身經濟結構的調整也需要時間。只有在完成這一調整之后才可望進入一個新的增長階段。在經濟調整過程中競爭力得到提高的企業也將在下一輪增長中得到更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