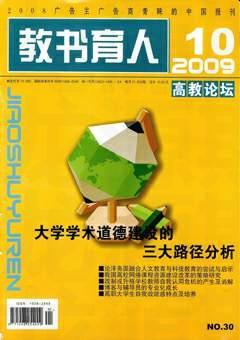論洋務派融合人文教育與科技教育的嘗試與啟示
周詩伍 王 凌
一、洋務派融合人文教育與科技教育的思想
1.政治主張——“自強”和“求富”
“自強”即學習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以應付西方;“求富”即利用西方先進科技改變中國落后的現狀。該政治主張的本質是為了維護清政府的封建專制統治。李鴻章認識到惟有借西方國家之法,也就是辦洋務,中國才能圖強。因此他大力提倡和推行洋務運動,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張之洞則在文章中說到:“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1]
2.思想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清政府統治的基礎是傳統的封建專制體制,因此必須重“道”,必須以中學為體。李鴻章變“器”而不變“道”的根本思想是很明確的,他只承認西方的“技藝”,而否定西方的制度和思想[2],他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綱常名教不必變,因為中國的禮儀教化遠勝于西洋諸國。張之洞則認為中學為“體”對西學為“用”具有主導和導向作用。他認為通“中學”是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基本條件,直接關系到一個人對國家、民族和祖國文明的情感。因此,學者必須在通“中學”的基礎上,“然后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闋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
二、洋務派融合人文教育與科技教育的實踐嘗試
洋務派在現實中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教育的缺陷在于“務虛”,“中國之睿知運于虛,外國之聰明寄于實。中國以義禮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禮為輕。”[3]洋務派看到西學之長在于科學技術,中國要擺脫危機走上自強之路,就必須盡快學習西方科技。洋務派學習西方科技有兩個途徑:一是學堂傳授,二是留學教育。
1.開辦洋務學堂
興辦洋務需要大批洋務人才,而這種人才又是科舉制度培養不出來的,因此,洋務派興辦了一批新式學校。洋務學堂是洋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是培養洋務活動所需要的翻譯、外交、工程技術、水陸軍事等多方面的專門人才,教學內容以“西學”和“西藝”為主。[4]大體有三類:外國語學堂、技術學堂和軍事學堂,現以這三類學校的典型進行闡述。
首先,外國語學堂的典型是京師同文館。它最初是作為外國語學校設立的,是近代中國被動開放的產物,它典型地體現了洋務派的辦學思想和改革中國傳統教育的努力嘗試。京師同文館創建之初旨在培養“認識外國文字,通解外國語言之人”的“譯才”。[5]隨著各地洋務事業的開展,洋務官員們越來越感到培養科技人才的重要,便有人倡議在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同時,兼學西洋格致之學。[6]奕忻等人上奏朝廷,請求添設天文、算學館,認為“洋人制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從天文、算學中來”。[7]這一請求遭到守舊派士大夫的公開抵制和攻擊,引發了近代以來關于教育改革問題的第一場爭論,即“義禮”之學與“技藝”之學的爭論。守舊派反對學習西方科技,他們認為科技不足為立國之本,“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8]而洋務派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祖宗之法解決不了問題,必須學習西方科技,自強之道不僅在“義理”,更在學習“技藝”。[9]在一番歷時半年之久的爭論后,1867年,天文、算學館終于成立,1869年京師同文館又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逐漸擴大了課程范圍。從1876年擬訂的京師同文館分年課程計劃中可以看出,西方科學技術知識已成為除外語以外最主要的教學內容。
第二,技術學堂的代表是福建船政學堂。洋務派主張“師其所能,奪其所恃”,[10]并大量購買和制造輪船、槍炮,從而建立制造軍火的兵工廠。洋務派興辦了大量技術學堂,如福建船政學堂、天津武備學堂等,在這些學校里,主要學習西方的實用科技知識。如福建船政學堂的課程主要有:英文、算術、幾何、代數、三角、動靜重學、水重學、電磁學、光學、化學、地質學、天文學、航海術等,由此可見這些學校基本上都是將實用科技知識列為最主要的學習課程。盡管如此,這些實業學校里仍始終保留著中國傳統的人文教育,要求他們學習中國經史之學,了解祖國的歷史文化,培養中國傳統的人倫道德。
第三,軍事學堂的典型是天津水師學堂。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太平天國運動,給清朝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一些封建官僚更進一步地認識到發展軍事力量對穩固封建政權的重要意義。因此,洋務派設立了軍事學堂以培養軍事人才,如天津水師學堂,學堂內開設英語、地輿圖書、算學、幾何、代數、駕駛諸法、重學等課;但同時,學堂很注重“教之經俾明大義,課以文俾知論文;瀹其靈明,即以培其根本。”[11]又如廣東水師學堂“限定每日清晨先讀四書五經數刻,以端其本。”
綜上所述,這三類學堂具有以下四個共同點:一是它們都是職業、技術學校;二是它們都以“中體西用”作為基本方針和指導思想;三是它們都以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為主要課程;四是它們都重視“固本”教育。洋務派辦西學,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是要用西方的“長技”武裝自己,以更好地鞏固封建統治,因此無論哪種學習西方的學堂,都規定學生必須要讀“四書五經”,必須要接受正統的封建倫理、道德、思想的教育,傳統人文教育占很大比重,只不過洋務派出于現實的考慮,已經將實用的科技知識的教學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教學的重點明顯傾向于實用科技知識。無論如何,西方近代的科技知識已經正式成為學堂的教學內容,并逐漸為社會廣泛接受,這使得中國傳統教育向近代化大大邁出了一步。西方科技教育和中國傳統的人文教育在學堂中雜和、并存的局面突破了中國傳統教育的單一模式,給中國的教育帶來了新的生機。[12]
2.洋務留學教育
19世紀70年代初,洋務派人士認識到,要全面深入地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僅僅靠國內創辦的洋務學堂,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是遠遠不夠的,國內的學堂存在師資、社會文化環境等諸多局限。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要深入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就必須向西方派遣留學生。于是,洋務留學教育得到很大發展,這一時期的留學教育主要是派遣留美幼童和留歐學生。
以派遣留美幼童為例。在“中體西用”思想的指導下,洋務派對留學生的教學內容和管理人員上作了精心地安排,有中文和經學老師隨行,不中斷“中學”的學習,管理人員也以陳蘭彬等守舊派人物為主。[13]學生到美國后除學習西學外,仍要兼講中學,課以《孝經》《小學》《五經》以及《國朝律例》等。而且“每遇房、虛、昂、星等日”,還要“傳集各童宣講《圣諭廣訓》,示以尊君親上之義”。[14]更有甚者,當時在舊學派與新學派之間產生了留學教育之爭,舊學派官員陳蘭彬以容閎“偏重西學,導致中學荒疏”為由,增加留學生誦讀儒經的時間和內容。
雖然洋務留學教育規模小、人數少,但它是中國教育走向世界進程中最名副其實的一步。就引進“西學”而言,洋務學堂固然能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是留學于西方國家、直接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卻是一條更為徹底的途徑。雖然清政府及守舊派在教學內容、管理上作了精心安排,后又將留美幼童撤回,但從客觀上來說,派遣留學生到西方國家學習也是將人文教育與科技教育融合起來的探索與嘗試。
三、現代啟示
1.適應多元文化必須防止文化封閉和全盤照搬
當今世界的開放性是以文化的多元性為前提的,而多元文化的存在又使得文化之間相互碰撞、交流與合作成為時代發展的特征。時代的發展要求開放和交流,因此既不能自我封閉,也不能全盤接受。正如馮驥才先生說過的:“在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封閉起來,但也不能因此丟掉自己的文化。”
首先,從歷史角度來看,在資本主義國家日新月異發展的同時,閉關鎖國的清政府還做著“天朝上國”的美夢,因此導致了在鴉片戰爭中中國被迫打開國門,進一步拉大了近代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并阻礙了近代中國的發展。因此,任何一個國家都應該意識到順應時代的發展、積極融入世界,并在交流中學習和發展的重要性。
其次,借鑒、吸收別國經驗的同時還要與本國實際相結合,有區別、有選擇地引用才能使之成為“自己的東西”。每一個獨立的個體,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都擁有屬于自己的獨特的實際情況、發展水平和目的,因此只有將別人的先進經驗與自身相結合,才能真正做到借鑒,而不是照搬。
2.建構現代教育要求人文教育與科技教育并重
洋務運動以來,人文教育與科技教育就作為教育的兩個對立面而存在,二者相互沖突又相互融合。科技教育的發展依賴人文教育,同時也促進著人文教育的發展;而人文教育的發展也依賴于科技教育,同時也促進著科技教育的發展。制約我國當前教育發展的因素之一就是重科技輕人文,因此在大力發展科技教育的同時,需要加強人文教育的發展。現代教育培養的應該是同時具有人文精神與科技精神的人,因此在建構現代教育的過程中,應該通過教育活動將人文知識、人文精神和人文價值內化為受教育者的精神,使之成為全面發展的人。
參考文獻:
[1]張之洞.勸學篇下(設學第三)[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秦君英.科學乎?人文乎?-中國近代以來文化取向之兩難[M].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3]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M].刻本.楊書霖編.1890(清光緒十六年).
[4][6][7][13]孫培青.中國教育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5][14]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文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8]高時良.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9]何志魁.從科學與人文之爭看近代中國高等教育思想中的文化心態[J].思茅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3).
[10]中國史學會.洋務運動(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11]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2]劉紹春.中國近代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撞擊與融合[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