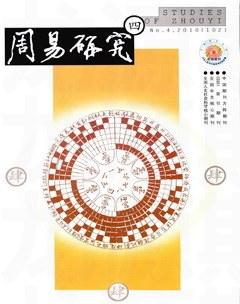海峽兩岸鄭玄學術研討會開幕辭
劉大鈞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各位朋友、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上午好!經過一年多的協調籌備,在各級領導和學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海峽兩岸鄭玄學術研討會”今天如期召開了。首先我代表大會組委會對關心和支持本次會議的各位領導、各位同仁致以由衷的謝意,對各位領導、各位同仁、各位朋友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
高密是大經學家鄭玄的故鄉。生當東漢末年的鄭玄,面對西漢以來經學今古文對峙、各家經說日趨繁雜的局面,以“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為職志,“囊括大典,網絡眾家,刪裁繁誣”,打破今古文經學的門戶,疊用今古而遍注群經,實現了今古文經學的融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注解方法到注解內容都為后世所效法,成為中國經學的典范,影響深遠。一千八百多年后的今天,鄭玄經學依然以其不可替代的學術魅力,吸引著我們去探索、去思考它所蘊含的豐富學術意蘊和精神價值。
眾所周知,儒學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干,經學則是儒學的根本。孔子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刪《詩》《書》,修《禮》《樂》,贊《易》,作《春秋》,接續起上古以來的禮樂文化,并將深沉的人文價值理性貫注其中,以仁為指導理念,塑造出一個融舊鑄新的儒家哲學文化和王道政治系統。雖然后世儒家經書數量不斷擴充,由六經而七經、九經,最終確立為十三經,但是這并沒有改變儒家經典進德修業的精神主旨。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使儒家經學從諸子學中脫穎而出,成為官學,其后兩千多年經學一直是古代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和學術研究的主流。經典不僅僅屬于過去,文本意義的開放性和解釋者的創造性,使儒家經學以多面向的理論內涵,緊扣歷史的脈搏,鮮活地呈現于各個歷史時期,展現出歷久而彌新的哲學一文化意蘊。各個時代的人們藉著經典而走進歷史,成就自我,走向未來。兩千多年的儒學發展史可以說就是經學發展史。馮友蘭先生在其兩卷本《中國哲學史》中將漢以后的中國古代哲學史稱為“經學時代”,可以說是獨具慧眼。兩漢的學術固然是經學的天下,魏晉的玄義風流在老莊的濃妝重彩下,其底色何嘗不是儒家經學的意趣。宋學則更是漢學以后從方法到義理都發生了極大轉換的經學新樣態,出現了以理學為主體的新儒學,錢穆先生甚至提出宋學較之漢學更為接近先秦儒學。清代以降,經學由精微玄妙的哲思轉入求真務實的樸學研究,崇漢學而貶宋學,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標的,在經典本來面貌的考據訓釋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不難看出,兩千多年來中國學術思潮的形成與轉進基本上都是圍繞經學問題而展開的。
儒家經學就其表象來說是對六經、十三經文本的解讀,是在研究這些書籍,但其實質則對宇宙人生、歷史文化、典章制度、天文歷法、語言文字等涵蓋當今眾多學科的問題的思考和研究,是一門綜合性的學問。以本次會議的主題人物鄭玄來說,首先他是一位杰出的經學家,再具體而言,他又是訓詁學家、文字學家、政治學家、歷史學家、思想家、天文學家、術數學家,等等,所有這些名號都不過是就鄭玄經學成就的某一方面而言,在鄭玄那里它們都是一體相通的。清代中后期以來,經學自身內部日益與時代問題脫節,外部則受到西方學術思想的猛烈沖擊,尤其是到“五四”以后,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傳統經學被視為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絆腳石,在“打倒孔家店”的聲討中,很快走向沒落。以西方學術體系為藍本所建構的中國現代學科,將經學四分五裂,曾經作為中國人價值來源和學術中心的經學,徹底成了無處安身的游魂。
上個世紀30年代,有人提出“五四”以后經學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我們所要做的只是經學史的研究。暫且不論這種看法的偏激和對傳統文化的敵視,所謂我們需要做的經學史的研究也并不令人滿意,片面而乏味。一直以來,經學史的研究論著,包括皮錫瑞的《經學歷史》、馬宗霍的《中國經學史》和現當代的些許經學史作品,都不過是在描述經學的形成過程和經學史上的歷史事件,并不關心經學的義理和其核心價值之所在。這也無怪乎今天許多經學史論著都出自古籍文獻研究機構。反過來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研究則是拋開經學而另起爐灶。于是,經學史中無思想,思想史中無經學,前者沒有靈魂,后者沒有根基。真正能夠在深入考察辨析的基礎上統合義理、考據、辭章的經學史著作尚未出現。正因如此,我們此次鄭玄學術研討會邀請了海峽兩岸文、史、哲領域的眾多學者,希望通過多學科、多角度的探討能夠對鄭玄經學、漢代經學乃至經學之整體形成一個整體性的認識和理解。
近二十年來,經學研究逐步走出“五四”的低谷,開始擺脫某些錯誤觀念的束縛,正視自身的學術特色和思想資源,學術界也在努力尋求恰如其分地研究經學的方式與方法。經學史的研究在一定層面上也是經學的研究,關鍵在于能夠直面經典,把握住經學和經學史中的問題,我們既要弄清古人在經典及其注疏中說了些什么,更要思考古人為什么這樣說,如果不能明白經典之用意,那么對經典本義的理解就不夠充分,甚至產生誤解。通過對經典之用意、經典之問題的理解,我們才能真正走進經學,把握其偉大的意蘊。不斷地向經典回歸,是中外思想史發展的普遍現象。當走進經典的時候,我們面對的絕不僅僅是過去,經典所開啟的宇宙人生之思,為我們思考和處理現時代的問題提供了深刻的啟迪和指導。儒家經學所詮釋的禮樂文化,向世人所揭示的乃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有序與和諧,而這些正是人類社會發展和自我成就的永恒主題。因此說,今天經學研究的意義,并不是純粹整理故紙堆,而是透過經典走進歷史、審視當下、走向未來的人文學術研究,是我們實現傳統與現代的轉接所必不可少的文化探索。今天的中國學術研究尤其是中國哲學研究所面臨的話語范式轉變的困境,也只有重新回到經學,回到中國思想文化的原初土壤中去,才能發掘出自身的資源和優勢,才能在現代問題的考量中開顯出新時期的中國哲學話語體系。
近幾十年來,尤其是世紀之交,大量簡帛文獻出土,如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上博簡中的孔子《詩論》,清華簡中的古文《尚書》以及郭店戰國楚簡等等,都是經學史上石破天驚的大事,為我們重新解讀儒家經典、研究古代歷史文化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李學勤先生甚至提出:“世紀之交出土的簡帛,已經涉及到中國學術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關系到整個學術史以及有關問題。”簡帛文獻無疑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但傳世文獻的研究還應是學術研究的重心,兩者并無抵觸之處,完全是彼此相應的。所以我們在簡帛文獻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的時候,在鄭玄的故里舉辦這次海峽兩岸鄭玄學術研討會,一則是希望以鄭玄經學研究為向導,推動兩漢經學乃至整個經學史的研究,二則希望傳統經學研究能夠與簡帛學術研究相呼應,從而使中國經學在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交互研究中能取得更大的成績。清儒王夫之云“六經責我開生面”,做好傳統經學研究,做好經學與現代的對接,正是我們現在無可推卸的責任。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現在我宣布:海峽兩岸鄭玄學術研討會開幕!我們主辦方一定盡最大努力為各位同仁營造一個良好的研討環境,如有不到之處還請大家及時批評指正。祝各位領導、各位與會代表心情愉快,身體健康!謝謝!
責任編輯:張克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