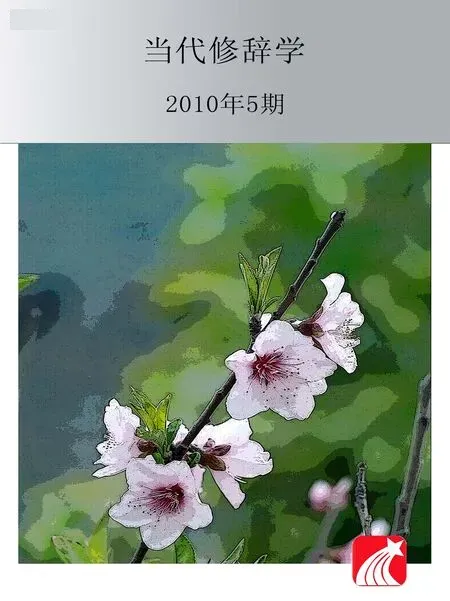“修辭學是邊緣學科”的界定及其應用*
——兼評鄒立志《語言論稿》
張煉強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100089)
提 要 “修辭學是邊緣學科”的說法,雖然已為多數(shù)人認可,但似尚無一個明確的界定,也似未見對其實際應用進行分析、研究的實例。本文的論述,或許可以提供一些進行分析、研究的實例,同時為如何給修辭學是邊緣學科下一個明確的定義提供參考。
修辭學界多數(shù)人認為修辭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是一門多邊性的邊緣學科。陳望道在《在復旦大學語言研究室的講話》中指出:“修辭學介于語言、文學之間,它與許多學科關系密切,它是一門邊緣學科。正如生物物理、生物化學、數(shù)學物理等邊緣學科一樣,研究時要先學生物,再學物理或化學、數(shù)學;研究修辭也要具備多門學科知識。”胡裕樹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在《學習〈修辭學發(fā)凡〉,為促進修辭學的繁榮貢獻力量》中指出:“修辭學是研究語言的調(diào)整和運用的。它雖然隸屬于語言學,但實際上是一門邊緣學科。它與哲學、邏輯學、文藝批評、美學、文章學(辭章學)、心理學和語言學中的語音學、語法學、詞匯學、文字訓詁等都有著十分密切的聯(lián)系。”他在評介拙著《修辭藝術探新》時還指出:“然而,怎樣憑借、綜合運用鄰近學科的理論以促進修辭學研究的不斷深化,這還是個有待探討的課題。”我的這篇文章,正是進行這種探索的一個嘗試,意圖從修辭學的邊緣學科①的實際應用的分析說到如何給修辭學是邊緣學科作出界定。而進行這種嘗試,最好有一個較好的平臺。最近讀到鄒立志的新著論文集《語言論稿》(即將出版。除非特別說明,下文提到的論文均出自該論文集),覺得此書比較成功地應用多種邊緣學科來對修辭現(xiàn)象和語言現(xiàn)象進行觀察和論析,這是此書值得肯定、值得評論的重要特點之一。我就以該書為平臺談些想法。
我一貫認為,應用新理論、新方法進行語言和修辭研究,是取得成果的重要條件。當然,所應用的理論和方法,總是要關及各種語言層面的,而這各種不同的語言層面是語言本身所具有的,以它們作為研究語言的視角和切入口,是理所當然的。這些不同的語言層面雖多,但概括地說,不外三種,即語法、詞匯、語義、語音的語言層面,修辭、語用的言語層面,心理、認知、邏輯的思維層面。
值得注意的是,此書所收的某些論文,盡管論題不完全相同,甚至相差很大,但應用的理論和方法大致是相同的,亦即應用了作為邊緣學科的認知心理學的隱喻、轉(zhuǎn)喻的理論和方法,來對修辭現(xiàn)象和語法現(xiàn)象進行論析。當然,應用時根據(jù)不同論題的需要對所用的理論和方法有所選擇和有所側(cè)重。鄒著中《詞義比喻引申的語言心理基礎分析》一文著重論述了“比喻引申一覽”、“比喻義的轉(zhuǎn)化過程”、“比喻引申的心理基礎”、“比喻認知模式的應用價值”,《言語行為下的比喻觀》一文著重從“語義變異論”和“交互作用說”探討“兩種比喻理論”,從“引進行為解釋的必要性”和“行為觀下的比喻層級體系”來討論“行為觀下的比喻”,《論潛喻》一文則著重論證潛喻概念的確立及其“內(nèi)部運行機制”。這些論文都無不應用了認知心理學的隱喻理論和方法。如果說在修辭篇內(nèi)探討有關比喻的論題時應用這些理論和方法是分內(nèi)的事,那么,在語用篇、文學語言篇、語言習得篇等部分對其他論題進行論述時也應用隱喻、語義分析的理論和方法,就是貫串全書的應用了。比如語用篇中的《“吃+N”結(jié)構(gòu)的形成機制及語義關系》一文就應用了詞匯、詞義層面上的隱喻和轉(zhuǎn)喻進行論述;文學語言篇中的《詩歌語體的隱性語義變異》一文就在“詞義的再生”一節(jié)中以比喻(隱喻)的理論和方法對“復活舊比喻”和“建立新的比喻關系”進行論述,以體現(xiàn)在聯(lián)想和想象上的隱喻和體現(xiàn)在語義變異上的語義分析的理論和方法對詩歌語體的隱性語義變異進行論述;語言習得篇中的《普通話早期兒童趨向動詞習得個案研究》一文,也不乏應用隱喻理論和方法進行語義分析而一語中的的表述:“趨向動詞的語義問題可以說是它的核心問題,因為‘運動—路徑’作為人類最基本的認知圖式很容易發(fā)生隱喻投射,從而進行語義引申。”這些大體相同的理論和方法廣泛應用于不同論題的論文的論述中,是各取所需,而不是簡單的重復。我想,這也不是作者故意為之,而是作者根據(jù)實際需要自然而然的應用。這也說明,隱喻和轉(zhuǎn)喻的確是語言和修辭的重要基礎,比喻和借代在修辭學中具有很強的生命力,而語義的轉(zhuǎn)移、變異又是隱喻、轉(zhuǎn)喻和比喻、借代得以形成和使用的關鍵所在。
鄒著后記說:“本書的語用篇、修辭篇、文學語言篇、語言習得篇等,幾部分看似散珠,實則一脈貫穿,它展現(xiàn)了我對語言進行思考的心路歷程。”其實散珠能夠成串的原因,也在其中不少論文都應用了作為邊緣學科的認知心理學、詞義學的隱喻和詞義的理論,這給人全書有一氣呵成的感覺。
鄒著中《修辭學理論的現(xiàn)代化進程——從宗廷虎、李金苓先生的學術貢獻看修辭學的發(fā)展》一文贊同宗廷虎、李金苓先生關于修辭學屬于語言學、修辭學是一門多邊性學科的觀點,認為“單純從語言學本位上來理解修辭學顯然是不夠的”,“如果認識不到修辭學特殊的邊緣性質(zhì),很可能導致修辭學研究視野的狹窄和研究思路的僵化”。這些看法是正確的。當然修辭學的邊緣學科②或者說鄰近學科到底是哪些?到底有多少?迄今尚無明確的答案。也就是說所謂“邊緣性”、“多邊性”只是一個概括卻又籠統(tǒng)的概念而已。按現(xiàn)有的較為通行的說法,修辭學的邊緣學科是心理學、邏輯學、語用學,而“語法”、“修辭”、“邏輯”在語言的學習和使用中由于三者關系密切而被相提并論。然則現(xiàn)在既然認可邏輯學是修辭學的邊緣學科,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認可語法學是修辭學的邊緣學科呢?如果是,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認可與語法同屬語言層面的詞匯學、詞義學、語音學也是修辭學的邊緣學科呢?至于同屬語言層面的語法學、詞匯學、詞義學、語音學、是否可以互為邊緣學科的問題,也是有待尋求答案的。
錢鐘書在《七綴集》中說:“人文科學的各個對象彼此系連,交互映發(fā),不但跨越國界,銜接時代,而且貫串著不同的學科。”如此說來,各種學科,至少是各種人文學科都可以有自己的邊緣學科,它自己也同樣可以成為別的學科的邊緣學科。為此,同行有人把文學、哲學、美學看作是修辭學的邊緣學科。
我現(xiàn)在還不能給“邊緣學科”、“修辭學的邊緣學科”下一個嚴格的定義,說明它們的內(nèi)涵和外延,也不能對“修辭學是邊緣學科”給出準確的說明,只能對它們作一個描述性的解釋:如果某一種學科同另一種學科在學科性質(zhì)上有較多的相近相通之處,因而它的某些理論和方法可以被用到另一種學科上來并起到積極作用,那么,它就是這另一種學科的邊緣學科。因為如果不是這樣,一種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是不可能應用到另一種學科上并起到積極作用的。此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應該說,從這種描述中可以引出“修辭學是邊緣學科”的結(jié)論。鄒著就應用邊緣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觀察研究屬于另一學科的論題并取得成效。比如“吃+N”結(jié)構(gòu)是語法學研究的對象,就是應用了認知心理學的隱喻理論和方法和語義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論述,并且取得了成效的。《詩歌語體的言語行為解釋》一文,應用了心理學的理論,說明了“看似荒唐的表達(“你挽著你的遺孀朝我走來”)卻別有深意”。這類表達在日常用語中也偶然可以見到,如“你要是守不住陣地,提頭來見!”說一個已經(jīng)死了的人還能夠提著自己的頭走來,當然是“看似荒唐的表達”卻也無疑具有“下達死命令”的深意。這種表達,是以超現(xiàn)實的想象為基礎的。如果應用邏輯學的理論來解釋,就是無邏輯之理;如果應用心理學的理論來解釋卻是有心理學之理有修辭學之妙。這是應用心理學的理論來觀察屬于修辭學研究對象的修辭現(xiàn)象和詩歌的語體特征。《詞義比喻引申的語言心理基礎分析》一文,論述比喻引申的心理基礎時,應用了邏輯學的繼發(fā)性思維理論,拿它來和心理學的原發(fā)性思維理論作比較,指出邏輯學的繼發(fā)性思維活動,遵循的是“同一律”,心理學的原發(fā)性思維活動遵循的是“相似即同一”的規(guī)律,而詞義比喻引申的基礎是心理學而不是邏輯學,從而正確地論證了論題。
我們注意到,此書的一些論題,同時應用了多種不同的邊緣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進行論述,而這些邊緣學科在所論的語言現(xiàn)象中,所起的作用不是對等的,有強弱不等的差別。這種差別是語言現(xiàn)象本身客觀存在的,持論者必須作如實的揭示,才能說明論題。如果在所論的語言現(xiàn)象中,某一種邊緣學科所起的作用通常是強勢,而另一種邊緣學科所起的作用通常是弱勢,卻出現(xiàn)了強弱易位的情況,那就是一般規(guī)律出現(xiàn)了例外。持論者就應該發(fā)現(xiàn)這種例外,并對造成這種例外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釋。《普通話早期兒童趨向動詞習得個案研究——以“上、下”兩組趨向動詞為例》一文,就是這樣處理的。在兒童早期理解過程中,他們對事物性的理解是最為優(yōu)先的,因而他們對名詞的理解和習得優(yōu)先于其他詞類,對實詞的理解和習得優(yōu)先于虛詞,這是一條符合認知常規(guī)的一般的認知規(guī)律。為此,此文認可兒童趨向動詞習得在認知發(fā)展上反映出“路徑→結(jié)果→時間”的隱喻投射,在語義發(fā)展上反映出“空間→路徑→結(jié)果→狀態(tài)→時間”的實義虛化過程,在語法發(fā)展上,反映出“詞匯范疇→詞匯—語法范疇→語法范疇”的轉(zhuǎn)變規(guī)律。這些應該是符合兒童習得一般規(guī)律的。不過,此文又指出,兒童習得的這種一般規(guī)律,也可以出現(xiàn)例外:“幾乎所有趨向動詞的頻率都是沿著‘趨向義—結(jié)果義—狀態(tài)義’呈現(xiàn)出遞減趨勢,反映了‘路徑—結(jié)果—時間’的隱喻投射機制在兒童認知心理的作用過程。但唯獨‘上’是個例外,‘上’的結(jié)果義以壓倒多數(shù)的絕對優(yōu)勢占據(jù)了第一位,反而更為基本的‘上’的趨向義卻寥寥可數(shù)。”造成例外的原因,此文認為是:“總的看來,兒童的語義—語法發(fā)展跟他們的認知發(fā)展基本一致,不過語用頻率因素可能壓倒認知原則從而使某些詞義習得違背一般的習得序列。”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在這一語言現(xiàn)象中,本應起強勢作用的認知心理因素同本應起弱勢作用的語用頻率因素,兩者強弱易位造成例外。因此,在應用多種不同的邊緣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分析某一種語言現(xiàn)象時,要看清有無強勢弱勢的現(xiàn)象,如果出現(xiàn)強弱易位而造成例外現(xiàn)象,要說明原因。
我們從此文對作補語的“上”和它前面的動詞一起考察所得的結(jié)果,可以具體地看到“上”是如何成為一個例外的,并且可以推知出現(xiàn)例外的具體原因。此文考察了242個語例,其中“上”為趨向義的僅9例,而為結(jié)果義的卻多達232例,其語用頻率占絕對優(yōu)勢。這是詞義的語用頻率壓例認知原則的最有說服力的數(shù)據(jù)。此文考察到表示結(jié)果義的“上”,它前面的動詞是“戴”、“蓋”、“穿”、“關”、“粘”、“掛”等。我推想這些詞都是早期兒童的常用詞,而結(jié)果義的“上”作為這些詞的補語,也是早期兒童常常聽到的,因為家長常常這樣說,或者經(jīng)常囑咐他們完成好這些動作,如叫他們“戴上帽子”、“蓋上被子”、“穿上大衣”、“關上窗戶”、“粘上信封”、“掛上書包”、“弄上早點”、“接上繩子”、“套上筆套兒”之類,“上”的結(jié)果義的語用頻率自然會大大地超過“上”的趨向義的語用頻率了。這里的“上”,都可以換成充當這些動詞的補語表示結(jié)果義的“好”,盡管“好”同“上”詞類不同。可見“上”的結(jié)果義很明顯,易于被兒童習得,它的語用頻率特別高或許與此有關系。這是語用作用影響甚至壓倒本應居強勢地位的認知作用造成的一個例外,這是作為語法學邊緣學科的認知心理學和語用學強勢弱勢易位的個例。
由實詞演變?yōu)樘撛~,由實義演變?yōu)樘摿x,是語言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而人對客觀事物的認知過程一般也是遵循由實到虛、先實后虛的規(guī)律的,所以語言演變過程和語言習得過程同認知活動過程是一致的。不過,語言現(xiàn)象不僅僅受到認知規(guī)律的制約,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約,當其他因素變成壓倒認知規(guī)律的強勢因素的時候,語言現(xiàn)象的一般規(guī)律就會出現(xiàn)例外。此文認為,這種例外,不獨出現(xiàn)在“上”的個案上,還出現(xiàn)在“把”、“被”、“就”等等虛化程度很高的詞上,造成例外的原因,也在這些詞的高頻率使用上。我們以“把”為例作一些具體說明。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中冊)第三章論述處置式的產(chǎn)生及其發(fā)展時說,“把”作為動詞的實詞用法早在七世紀以前已經(jīng)存在,而“把”作為虛詞來用,大約產(chǎn)生在第七世紀到第八世紀之間,到了中、晚唐以后,用得更加普遍起來。這很符合詞義由實義到虛義的一般發(fā)展規(guī)律。現(xiàn)代漢語中“把”的實詞用法語例極少(如“把大門”、“手把手”)這顯然就是古代漢語“把”的實詞用法的沿襲和殘留,而“把”的虛詞用法卻比比皆是,“把字句”的使用頻率是極高的。不過,盡管如此,這種情況仍然符合由實詞演變?yōu)樘撛~,由實義演變出虛義的一般規(guī)律。因為現(xiàn)代漢語“把”的虛義用法仍然是由古代漢語“把”的實義用法演變而來的。至于現(xiàn)代人尤其是早期兒童由于“把”的虛詞用法的使用頻率極高而先于其實詞用法的習得則是不難說明的,因為所謂“習得”是“習”而“得”之,不習不得,少習少得,多習多得,而使用頻率極高,提供了多習多得的最好的平臺。而所謂“得”就是理解和掌握“把”的虛詞用法。
和“上”一樣,這也是語用因素影響甚至壓倒認知作用,作為語法學的邊緣學科的認知心理學和語用學強勢弱勢易位的個例。一般來說,語法學關注語言層面的問題,語用學探討的是言語層面的現(xiàn)象,關系并不十分密切,但是在論述語法現(xiàn)象的歷史發(fā)展過程的時候,就往往少不了借助語用分析了。因此,就上面這個例子來說,我們也是可以把語用學看作是語法學的邊緣學科的,正如錢鐘書所說的那樣,它們是“彼此系連,交互映發(fā)”地“貫串著”的。
由于各種學科(包括語言學、修辭學自身)都處于不斷發(fā)展更新的過程之中,難免未臻完善,所以應用邊緣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說明論題,有時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詩歌語體的隱性語義變異》一文中“邊緣義的凸出”,與記憶和聯(lián)想密切相關,此文準確地抓住這一點進行論述,先引用了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的有關論述(“在話語之外,各個有某種共同點的詞會在人們的記憶里聯(lián)合起來,構(gòu)成具備某種關系的集合”,“聯(lián)想集合的各項要素既沒有一定的數(shù)目,又沒有確定的順序”),接著指出“根據(jù)邊緣義組織的聯(lián)想系列就是如此”,詩歌語體中,凸出的邊緣義是附加在義位基本成分之上的由詞的指稱對象引起的感受、情調(diào)和聯(lián)想產(chǎn)生出來的表象義、情感義、社會文化義。該文以“火”一詞的聯(lián)想系列為例來說明:

a、b組是事物表象引發(fā)的性質(zhì)或有類似表象的物質(zhì)聯(lián)想,c組主要是情感的聯(lián)想,d組主要是社會文化義的聯(lián)想。這些都是相似聯(lián)想,相似比相反更易引起聯(lián)想,但也不乏相反聯(lián)想的存在(如“水底的火焰燒彎了兩肋”)。毫無疑問,此文的這些論述,是以記憶和聯(lián)想為心理基礎的。記憶是聯(lián)想的前提條件,而離開了聯(lián)想,也不可能引起表象義、情感義、社會文化義。既然如此,我們就有理由應用認知心理學的“以語義聯(lián)系或語義相似性將概念組織起來”的“激活擴散模型”(Spreading Activation Model,Collins&Loftus(1975),參見王、汪安圣(1997)第六章第二節(jié))加以說明。在這個模型中,“火”是一個結(jié)點,可以看到它同另一個結(jié)點“紅”聯(lián)系,但對a、b、c、d各組的其他的詞都沒有反映,所以無助于我們對詩歌邊緣義的凸出進行觀察和分析。詩人寫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詩心如火,情動江關,浮想聯(lián)翩,思接萬里,其所用的詞語,邊緣義凸出,是情理中的事,也是修辭和文學的事。激活擴散模型是依據(jù)一般人的記憶和聯(lián)想構(gòu)建出來的,若用來分析、欣賞詩歌語言的邊緣義凸出,它就無能為力了。我們希望從認知心理學找到一個可用來觀察、分析、欣賞詩人寫作用詞的心理活動的激活擴散模型,讓它作為我們研究詩歌語體的隱性語義變異的他山之石。
這是修辭學和文學如何應用其邊緣學科認知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的問題。
鄒著令人關注的地方,當然不限于應用邊緣學科來說明論題,在選題新穎、論述深入方面,也值得肯定。比如《論古今漢語詞類活用的不同本質(zhì)》一文,就不是老生常談,而是新題新說。論及漢語詞類活用的,在修辭學和語法學中都并不罕見,但如此文那樣,專以古今漢語詞類活用不同的本質(zhì)為論題進行深入論述的,即便不是沒有也應說是罕見。陳望道先生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出版的《修辭學發(fā)凡》中就把詞類活用稱作“轉(zhuǎn)類”作為修辭格加以論述;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中冊)的“語法的發(fā)展”一章中以“詞在句中的臨時職務”一節(jié)論述古代漢語的詞類活用。王力先生把大部分詞類活用現(xiàn)象分別歸入(甲)致動和(乙)意動兩類之內(nèi),并舉了大量的語例說明。(甲)致動如“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民”(《老子》),就是“使民聰明,使民愚”的意思。“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荀子·儒效),就是“使政美、使俗美”的意思。“匠人而小之”(孟子·梁惠王下)就是“匠人砍小了它”的意思。(乙)意動如“爾欲吳王我乎?(《左傳·定公十年》),就是“你想使我做吳王嗎?”的意思。“細萬物、則心不惑矣”(《淮南子·精神》)就是“以萬物為小”的意思。陳、王兩位先生都沒有論及古今漢語詞類活用的不同本質(zhì),這很可能是因為他們關注的焦點不在這個問題上。至于漢語詞類活用何以有本質(zhì)不同,此文認為是因為古代漢語詞匯相對貧乏,語法相對簡單,需要以詞類活用“救語言文字之窮”,而現(xiàn)代漢語詞匯相對豐富,語法相對復雜,無需以詞類活用來“救語言文字之窮”了,而盡量發(fā)揮詞類活用可以提高語言表達能力的效用,也就成為修辭的必需了。因此,此文明確指出,“現(xiàn)代漢語的活用主要是修辭現(xiàn)象,而古漢語的活用卻主要是‘詞匯—語法’現(xiàn)象”。由此引出古今漢語詞類活用具有不同本質(zhì)的結(jié)論。我想,如果以穿衣來比方,古代漢語詞類活用類似于為御寒而穿衣,而現(xiàn)代漢語詞類活用則和為扮靚而著時裝相類似,因各自滿足人們的不同需求而產(chǎn)生了實質(zhì)性的差異。
關于古代漢語的“語言文字之窮”和“救語言文字之窮”的問題,王力先生有精辟的論述。他在《漢語史稿》(中冊)的“語法的發(fā)展”一章里談到“使成式的產(chǎn)生及其發(fā)展”的問題時強調(diào)說:“由致動發(fā)展為使成式,是漢語語法的一大進步。因為致動只能表示使某事物得到某種結(jié)果,而不能表示用哪一種行為以達到此一結(jié)果。倒如“‘小之’可以是‘削小它’,也可以是‘裁小它’、‘砍小它’等……使成式的產(chǎn)生,使?jié)h語語法更完善、更能表達復雜的思想。……使成式產(chǎn)生于漢代,逐漸擴展于南北朝,普遍應用于唐代。”至于現(xiàn)代漢語,我認為使成式普遍使用,而致動用法則廢置不用了,無需以古代漢語的致動方式作詞類活用了。這種語言發(fā)展的事實和論述,有力地支持了此文的看法。不過,王力先生又針對古代漢語說:“‘致動’和‘意動’是修辭上的一種手段。”把古代漢語的“致動”和“意動”看作是修辭現(xiàn)象,就與此文的看法相左了。我支持此文的看法。
王力先生《漢語史稿》中有這樣一個“國”的詞類活用的語例:“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史記·晉世家》),就是“封異姓使為國”的意思。魯迅先生的雜文《“友邦驚論”論》也有一個用“國”的詞類活用語例:“可是‘友邦人士’一驚詫,我們的國府就怕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失去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只有幾個學生上幾篇‘呈文’,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獎,永遠‘國’下去一樣。”兩相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出,前一語例的“國”的詞類活用,時在使成式剛剛產(chǎn)生或者說并未普遍應用的漢初,是司馬遷對先秦詞類活用的沿用,所以目的還是“救語言文字之窮”,不是出于修辭的需要。而后一個是“國”詞類活用的現(xiàn)代用例,目的不再是“救語言文字之窮”,純粹是一種修辭現(xiàn)象了。如果從應用邊緣學科的角度說,《論古今漢語詞類活用的不同本質(zhì)》一文是在應用作為語法學邊緣學科的修辭學和詞匯學去分析詞類活用問題。
語言處于不斷發(fā)展過程中,難免出現(xiàn)不符合現(xiàn)有語言規(guī)范的語言現(xiàn)象,如動賓式詞語帶賓語。《動賓式動詞規(guī)范問題的深層理據(jù)》一文從語言規(guī)范的角度看是一篇具有實踐意義的論文,從揭示其深層理據(jù)上說又是一篇具有理論價值的論文。我從文中的一些例子產(chǎn)生了興趣,“動賓式動詞+賓語”同“動詞+賓語+于(於)+補語”之間是否有某種聯(lián)系?這些語例有:
(1)a躋身世界強隊之列 稱雄世界 揚威柏林 移民加拿大 執(zhí)教懷仁堂
b造福八萬人家 服務上海東區(qū)顧客 投身國家建設 問鼎總統(tǒng)寶座
我發(fā)現(xiàn),這些語例的“動賓式動詞+賓語”結(jié)構(gòu)都可以在最后的一個賓語前加“于(於)”,轉(zhuǎn)換成“動詞+賓語+于(於)+補語”結(jié)構(gòu),而語義基本不變。a組各例加介詞“于”(於)介引出表示動作處所的補語,b組各例加介詞“于(於)”介引出的是表示動作對象的補語。由此,我們有理由把動賓式“動詞+賓語”結(jié)構(gòu),看成是“動詞+賓語+于(於)+補語”結(jié)構(gòu)的一種省略形式,也就是把“于(於)”省略了。這種省略句的語例古代漢語里有,沿襲古漢語用法的文言文、成語里也有。例如:
(2)因問王曰:‘今東鄉(xiāng)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史記·淮陰侯列傳》)
乞寄命交州,以終余年。(《三國志·孫權致曹丕書》)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魯迅《自題小像》)
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毛澤東《蝶戀花·答李淑一》)
至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問鼎中原”“逐鹿中原”作為成語也常用在現(xiàn)代漢語的書面語和口語之中。以上所舉的“動賓式動詞+賓語”結(jié)構(gòu)的語例,可能是基于語言的經(jīng)濟原則和修辭的言少意多的需求有意省略了“于(於)”而形成的。而事實上,“動詞+賓語+于(於)+補語”結(jié)構(gòu)的完全句的語例無論在現(xiàn)代漢語中還是在古代漢語中都是經(jīng)常地、多量地使用的,它們?yōu)檫@些省略句的出現(xiàn)提供了充足的語源。比如,(1)組各例加上“于(於)”字,都是現(xiàn)代漢語的通行說法,如“躋身于世界強隊之列”、“稱雄于世界”、“服務于上海東區(qū)顧客”、“傾情于上海灘”等等。《現(xiàn)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對介詞“于”釋義時,所舉例句,也有這種完全句:“告慰于知己”、“獻身于科學事業(yè)”、“有益于人民”。這種完全句在古代漢語中也不乏其例,如“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論語·顏淵》),“救民於水火之中”(《孟子·滕文公》),“托勝於山林,寄情於物外”(劉晝《韜光》),“制勝于無形”(《史記·太史公自序》),“九月風高,孟嘉落帽於龍山”(《幼學瓊林·時歲》)等等。可見,以上的“動賓式動詞+賓語”的語例,源頭水源充足,是不容易斷流的。我的這些看法是否可以作為對“動賓式動詞+賓語”的研究的一個參考呢?謹質(zhì)于明敏的讀者。如果從應用邊緣學科的角度說,在這里,我也是在應用作為語法學邊緣學科的語用學、修辭學來分析語法結(jié)構(gòu)的發(fā)展變化。
我對“邊緣學科”、“修辭學的邊緣學科”的描述性解釋,得到來自鄒著比較成功地應用認知心理學、心理學、語用學、修辭學、邏輯學、詞匯學、語義學等學科理論和方法的事實的支持。這些事實,具體地說是:①用認知心理學、語義學探討語法問題(“吃+N”結(jié)構(gòu));②以心理學、邏輯學論述修辭現(xiàn)象(詩歌語體的語言特征);③以認知心理學、語用學論證語法現(xiàn)象(“上”、“把”的習得序列出現(xiàn)例外);④以心理學、認知心理學解釋文學、修辭現(xiàn)象(詩歌的言語凸出邊緣義);⑤以修辭學、詞匯學研究語法問題(古代漢語的所謂“詞類活用”實為語法現(xiàn)象)。這些事實還表明,這些學科是可以互為論述對象的。比如③的語法問題(“上”充當結(jié)果義補語),就可以用來論述語用學(語用)可能壓倒認知心理的問題,而④文學、修辭現(xiàn)象(詩歌的言語凸出邊緣義)就可用來論述心理學、認知心理學(激活擴散模型的局限)。從邏輯上說,甲與乙挨邊,則乙也必然與甲挨邊,這些學科可以互為對方論述的對象,正好說明它們具有“多邊性”、“邊緣性”,它們都是邊緣學科,如果它所論述的對象是修辭學,它就是修辭學的邊緣學科了。當然,它們在學科性質(zhì)上有較多的相近相通之處,是構(gòu)成邊緣學科的最為根本的內(nèi)在條件。以上分析,或許可給我們準確理解“修辭學是邊緣學科”提供參考。
注 釋
①②本文所說的“邊緣學科”是指有鄰近、交叉關系的兩個或多個學科(它們互為邊緣學科),有時也指在某一個學科群中處于非中心地位的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