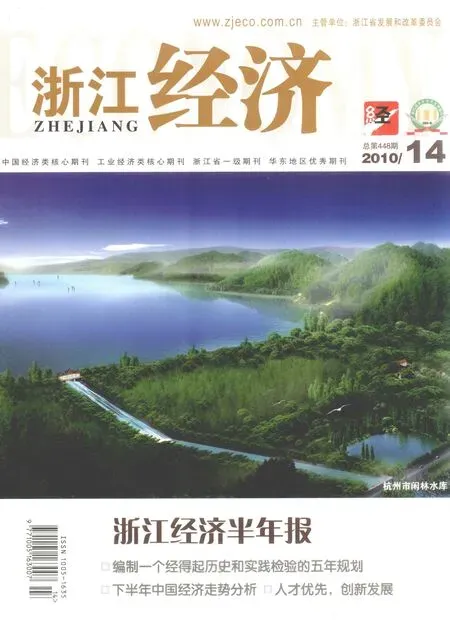電視“媒介”還是“媒婆”?
文/劉洪波
大眾媒介投身于媒婆行業,不預示媒婆這樣一個傳統行業在當代社會具有復興的趨勢,而只意味著媒介對自身的否定
電視是一種媒介,因為相親節目的火熱,現在更像是一個媒婆。
媒婆是私人在進行社會性活動,媒婆是一個個體,而“做媒”意在完成婚配,婚配是私人性的,但具有一定的社會性,因為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位,而婚配是家庭的前提。
電視相親則是一種由公共機構進行的私人性活動。電視是公共機構,相親是私人行為。相親以婚配為目的,有一定的社會性,但終究而言,仍是個人事務。電視的介入,使相親這種私人事務變成公共事務,從而制造了一種奇特的“相親明星”。
媒介與媒婆,共有一個“媒”字,這顯示了媒介這個詞在語源學上的來歷。世界上先有媒婆,后有媒體。準確地說,人們先認識了媒婆,然后才認識了媒體。
保媒拉纖是一種歷史悠久的人類活動,而把信息交流的中介視為媒體、大眾媒介,則是觀念革命的產物,源自于傳播學的興起。
字面上說,“媒”可以理解為一種以匹配男女為目的的行為,而且匹配對象具有不確定(某)性。“做媒”是在不認識的男女之間架設婚配的橋梁。包括電視在內的大眾媒介也以不特定對象為目標,但其目的在于信息交流。
因此,從媒婆到媒介,是中介性的擴大;而從媒介做回媒婆,不是媒介對其功能的窄化,而是媒介否定自我的一種純粹語源學的返祖。
從社會學意義上說,媒介與媒婆其實并不搭界。因此,電視熱衷于成為媒婆,就連“認祖歸宗”都談不上,只能說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玩樂。
大眾媒介投身于媒婆行業,不代表“接近性”、“服務性”的增強,不預示媒婆這樣一個傳統行業在當代社會具有復興的趨勢,而只意味著媒介對自身的否定。
其實,作為媒婆,電視媒婆是不真誠的。媒介變成媒婆,本身就很怪異,而變成不真誠的媒婆、偽媒婆,以利用媒介的大眾性而裝媒婆,就更加令人作嘔。
相親貌似一種“功能性”節目,要完成婚配的目的,但實際上是一種惡搞的娛樂秀。相親節目不是相親的地方,而是假裝相親。沒有相親是可以保證成功的,相親的這一特性,為偽裝的相親留下了空間,唯其如此,相親就可以不斷地相下去。
相親節目成為一種特殊的“造星運動”,顯示了高熱的人氣。
一個嘉賓能夠從汲汲無名之輩,通過相親而成為明星,既有類似于“超級女聲”的草根成功因素(嘉賓以普通人身份、相親這種普通人的行為,獲得普通人的關注),也有相親行為作為婚配許諾與交媾認可的標準使人們產生興趣的因素,還有電視舞臺在相親節目中變成類似于夜總會“金魚缸”式的肉體展陳場所的因素。相親節目的人氣中,混雜著好奇與窺私、欲望與獵艷、審美與審丑。
雖然電視相親中出現的許多觀念,作為現象可以說體現了社會生活的實況,然而生活的實況與生活的應然不同,真實與否與合理與否是兩回事。
廣電管理部門終于對相親節目忍無可忍,先是點名批評,后是出臺規定要規范節目。
基于對大眾傳播的理解,筆者并不覺得有一個行政機構對電視臺直接發布各種號令是正常的,或者可喜可賀的事情。然而,電視相親節目全無傳播倫理約束,必得行政機構直接出馬,則制造了一種媒體自律無效、社會無法約束媒體、傳播倫理無用的假相,使得管理機構的存在及號令行為看上去十分必要。
中國有很多事情都是如此。雞生蛋,蛋生雞,糾纏不已,使人很容易模糊是非,不知道到底是過于依靠號令產生了問題,還是國情有別,國人異秉,非得嚴加號令而不能產生一種過得去的秩序。而筆者始終相信,有責任的媒介,存在于能夠自我負責的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