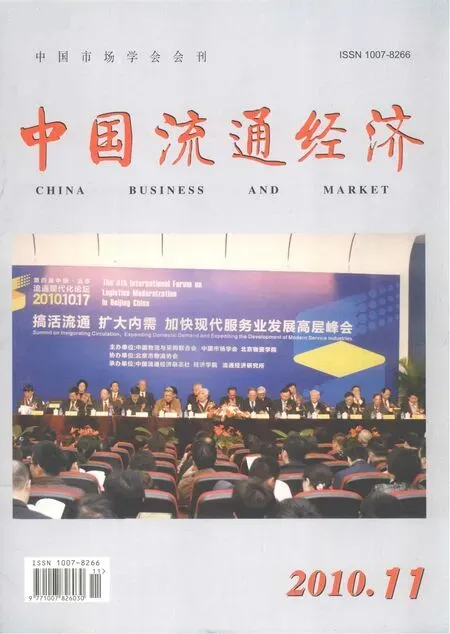論城鄉一體化
厲以寧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北京市 100871)
論城鄉一體化
厲以寧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北京市 100871)
今后30年,我國改革的重點將是消除城鄉二元體制,進而實現城鄉一體化。城鄉一體化應該是雙向的,即農村居民可以遷往城市,在城市工作或經營企業,城市居民也可以遷往農村,在農村工作或經營企業。我國目前的城鄉一體化之所以是單向的農村居民向城市遷移,關鍵不僅在于城鄉居民戶籍分列,更重要的在于土地制度的二元結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雙向城鄉一體化的體制障礙,應該盡快消除這種體制障礙,賦予農村居民財產權,發放房屋產權證,將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雙向的城鄉一體化,有利于中國經濟走向以居民消費拉動為主,有利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有利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
城鄉一體化;農民財產權;財產性收入;就業渠道;
一、為什么農民沒有財產性收入
在農村調查時,幾乎所有的農民都提出為什么不發房產證的問題。有的農民說:城里實行的是土地國有制,在那里,無論是祖傳的房屋還是新購的商品房,都有房產證;而農村實行的是土地集體所有制,祖傳的房屋也好,農民在自家宅基地上建的住宅也好,為什么不發房產證呢?農民們想不通。看來這個問題是帶有普遍性的。
農民還反映,由于自家的房屋沒有房產證,既不能抵押,又不能轉讓,要進城經商、開店或打工,如果把家屬也帶到城里去住,只好門上一把鎖,讓老鼠在房屋里做窩。那么,為什么不出租呢?有熟人愿意租房,當然是件好事,但正因為出租者沒有房產證,只能廉價租給熟人,等于請人代為照看住宅,而不敢租給陌生人。怕自己沒有房產證,人家拒不支付租金怎么辦?或賴著不走又怎么辦?村干部說,還有更糟的呢。比如,農民一家人都進城了,門上鎖了,有的卻被撬開,在空房子里堆炸藥,于是變成了地下爆竹作坊;有的變成煉地溝油的黑店,還有的成了聚賭嫖娼的窩點,給村里帶來不少麻煩。
至于那些為住房上鎖而進城務工的農民,則是兩手空空,什么資本也沒有,因為房屋不能抵押,不能轉讓,不能合法租出,還有什么資本可以帶走?即使進了城,沒有房子可住,只得搭個窩棚聊以棲身、安置家屬,或者租間地下室住,又潛入地下,過著極其簡陋的生活。這就是所謂“兩只老鼠”的故事(農村里的自家房屋成了老鼠窩,進城后又過著同老鼠一樣的地下室生活)。
這里不妨以19世紀中期以后法國工業化過程中農民進城的情況為例。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不少貴族地主逃亡國外,法國革命派把他們的土地沒收之后分配給無地的農民。拿破侖當權后,用法律確認了新的土地關系。波旁王朝復辟后,不敢把農民分得的土地重新歸還貴族和地主,因為擔心社會動蕩。這樣,法國的小農土地所有制鞏固了下來。19世紀中期以后法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加快進行,農民紛紛進城。法國成立了不動產抵押銀行,容許農民用自己的田產房產作為抵押,帶資進城。于是,準備進城的農民不是空手進城,而是帶資進城,或開店,或做工,且有房子可住,并且隔一段時間之后把家屬也帶到城里,工業化和城市化都在有序進行。農民的田產房產雖被抵押,但等到進城的農民收入增加了,借銀行的錢還清了,田產房產依然是農民的。如果農民感到在城里有更大的發展前景,這時還可把田產房產賣掉。
然而,在我國農村所看到的卻是另一種情形:農民沒有房產證,他們想開店創業,或在農村擴大經營規模,但靠什么作為抵押品取得貸款呢?農民的房屋不能抵押,這意味著房屋在農民手中并未被確定為個人財產。不僅農民的房屋未被確定為個人財產,連宅基地、承包土地也都如此。農民沒有財產權,怎么可能有財產性收入呢?農民沒有財產權,想轉讓自己的承包土地、宅基地和房屋也就不可能如愿。
假定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那么在當前條件下,能不能把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的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開處理?即房屋可以轉讓,承包土地的使用權和宅基地的使用權也可以轉讓。這是一種變通的做法,而這種變通是必要的。既然承包土地的使用權和宅基地的使用權可以轉讓,那么它們用于抵押,也就無可爭議了。這是一項重大的制度創新,實行這一制度創新刻不容緩。實踐將會證明,它對中國長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二、農民有了財產權以后中國農村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讓我們仍從農民的住房開始分析。
怎樣提高農民收入,擴大內需?給農民各種補貼,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通過農業產業化來增加農產品加工值……等等,這些都是有效的措施。但最重要的是讓農民擁有財產權。首先是給農民發房產證,容許農民用房產證作為抵押,取得貸款;出租房屋,取得房租;轉讓房屋,把實物資產轉化為貨幣資產,再轉化為資本。具體的做法可以先從農民遷入新農村的住宅開始,因為散居的農民和他們的房屋由于宅基地面積大小不一,農民之間矛盾很多,一時不易處理。加之,發房產證從農民遷入新農村的住宅開始,還可以鼓勵散居的農民向新農村遷移。
據2010年6月5日上海《文匯報》第一版所載,上海市嘉定區在農民遷居之后,每戶農民可以分到三套住房,面積分別是 60m2、80m2和 110m2,每戶任選兩套自住,余下的一套供出租之用。三年之后,房屋可以自由買賣。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調研組2010年7月初在山東省威海市調查時,在其近郊的“小城故事”社區看到了類似的情況。這個社區是由幾個行政村合并而成的。在那里,每戶分得兩套住房,都是90m2左右的,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如果農民認為自己住一套就夠了,也可用另一套換得幾十萬元現金。
這樣,農民有了可供出租的房屋,或者像威海市“小城故事”社區那樣,把可出租的那一套房屋變成現金,農民的收入立馬就上升了,日常生活沒有問題,而且還有創業的資本金,開店、做生意、外出務工都行。我們在威海市看到,只要農民有房屋可以出租、抵押或轉讓,他們的經濟便活起來了,他們的內需就擴大了,他們的創業活動也就開展起來了。
到目前為止,由于在現有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限制的條件下,即使地方政府想給農民住房發放房產證,也難以真正落實。據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調研組的調查,在山東省大體上有三種發放房產證的方式:
一是把土地收歸國有后,由房地產主管機構發放正式的房產證。威海市“小城故事”社區就是如此。合并為“小城故事”社區之前,這里原來是幾個行政村,屬于“城中村”改造的范圍,所以行政村一合并,社區一建立,土地變成了國有土地,農民也就相應地成為市民,發房產證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在其他省市,凡屬于“城中村”改造的地帶,也都采取相應的做法。
二是在保留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條件下建成新農村,在農民搬進新居后(如萊陽市的一些農村)由城鄉建設部門發給房產證。有了這種房產權證,農民不僅可以出租自己的房屋,而且還可以用于農村信用社的抵押貸款。對農民來說,因為農村信用社離自己家很近,貸款是很方便的。
三是行政村同龍頭企業融為一體。在龍口市南山集團公司所建的新農村,農民將土地使用權入股,公司經營園藝、果樹、釀酒、旅游、養殖、其他工業品制造等,農民成為公司職工,公司興辦各種福利事業,并建設新農村住房。農民作為股東每年有紅利可得,作為職工每月有工資可領,同時享受各種福利待遇,還分到新農村中的住房,并由集團公司發給房產證(在集團公司內部是承認的)。
農民有了房產證以后,不僅如前所述有了創業的資本(抵押、轉讓),有了經常性的財產收入(出租房屋的租金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市住房緊張的壓力。城市房價高,一般城市居民不一定能買得起商品房,而城市可供出租的房屋通常供不應求,因此農民有多余的房屋可供租賃,對市民是有好處的。離市中心較近的“城中村”改造后,新建的農民住宅中有不少已經租給城市居民,他們上班近,附近又有學校、醫院或衛生站,生活很方便。即使離市中心較遠的農村,只要公共交通通暢,或者租房子的人家有私人小汽車,也可租賃農民的住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離城市并不太遠的農民家庭都有空余房屋出租時,對城市居民方便,對作為房東的農民也有利,因為他們會增加收入。
給農民發房產證的好處已如上述。那么,宅基地與承包土地使用權的抵押和轉讓,又會給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什么樣的變化呢?以下讓我們接著分析。
三、雙向的城鄉一體化
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城鄉一體化都是雙向的。而迄今為止,我國正在推進的城鄉一體化則是單向的。雙向的城鄉一體化是指農民可以遷往城市居住,可以在城市工作或經營企業,而城市居民也可以遷往農村居住,可以在農村工作或經營企業。中國目前的城鄉一體化之所以是單向的(即只有農民由農村向城市的遷移,而不存在城市居民向農村的遷移),關鍵不僅在于城鄉居民的戶籍是分列的,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土地制度是二元結構的,即城市實行的是土地國有制,農村實行的則是土地集體所有制。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是雙向城鄉一體化的體制障礙。
能否繞過這個制度障礙,把土地所有權同土地使用權分別對待?根據龍口市南山集團公司和當地一些行政村融合為一體的經驗,是可以走出一條新路的。這就是農民可以把承包土地的使用權入股于南山集團公司,把宅基地的使用權交給南山集團公司,換取新農村的住房并取得房產證。當然,龍口市的經驗只是改革過程中涌現出來的若干經驗中的一種,但這已經可以說明,如果用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有利于”標準來衡量,承包土地使用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的入股、置換、抵押或轉讓,符合這一標準的城鄉一體化改革的基本思路。
于是,雙向的城鄉一體化就具有試行并逐步推廣的制度條件。雙向城鄉一體化的推進,一方面可使農民“帶資進城”,加快了城鎮化建設;另一方面,城里愿意遷到農村的個人和企業也可以如愿以償,“帶資帶技術下鄉”,在鄉下生活、工作、投資。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將隨之取消,代之以全國統一的身份證制度。隨著雙向城鄉一體化的推進,不僅傳統的服務業會進一步發展,而且現代服務業也會迅速發展,第三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中的比重也將不斷上升,三次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將趨于合理,新的崗位將在第三產業的發展中涌現出來。到了那個時候,城鄉社會保障也將一體化。城鄉居民的后顧之憂將逐漸淡化,追求生活質量成為全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共同愿望。內需將會有大的突破,中國經濟也會轉入以居民消費拉動為主的良性發展。
雙向城鄉一體化之后,中國農業將會有大的發展。限制農業發展的因素主要有四個:體制、資本、技術和物流。其中,體制因素最為重要。
第一,體制。關于體制因素,前面已經提到。農業規模效益之所以難以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農業產業化之所以難以有更大的突破,充裕的民間資本之所以不愿投向農業和農村,以及農業現代化之所以進展得相對遲緩,全都同承包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有關。而農村缺少青壯年勞動力和專業人才,同樣歸因于城鄉二元體制的存在。因此,如果在承包土地使用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方面尋找突破口,繞開現存的體制障礙,中國農業發展的前景是充滿希望的。
第二,資本。一旦體制障礙減弱了、消失了,農村不愁沒有資本可用,農民也不愁沒有融資渠道。特別是在雙向城鄉一體化的條件下,資本下鄉、技術下鄉、人才下鄉總會相伴而行。其中,資本下鄉最為關鍵,而且資本下鄉是先行的。過去被認為沒有投資價值的重大項目,如低產田的改造、沙漠化和石漠化的治理、農村公用事業的建設和發展等,都會因承包土地使用權的流轉而成為新的投資熱點。
第三,技術。技術下鄉要同資本下鄉結合在一起,都應當給投資人帶來收益,否則就是技術下了鄉,也不會持久,更不能使技術的采用范圍大面積地推廣。這個問題也只有在雙向的城鄉一體化過程中解決。要知道,在單向的城鄉一體化過程中,農村的青壯年和專業人才都進城了,誰還會專心致志地使新技術在農村開花結果呢?
可以設想,在雙向城鄉一體化推進到一定程度之后,除了仍有一部分農業中的散戶而外,大體上有三類農業生產者:一是種植大戶、養殖大戶。他們是種植能手、養殖能手,通過轉包、租賃、轉讓等方式,集中了土地,實現了規模經營,使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二是種植業、養殖業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這些專業合作社的骨干,一定是懂得經營、善于管理,并且在農業方面懂行的人才。他們同樣從事規模經營,會使農業進一步發展。三是“龍頭企業+農戶”。這里所說的農戶,可能是承包土地入股之后仍然留在龍頭企業工作的人,也可能是承包土地入股后進城另謀出路的人。這一類農業生產者的最大優點是可以使農產品產業鏈有較大的延伸,并且在營銷方面取得較好的成績。
四、讓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名副其實的新農村
到了工業化后期,尤其是進入后工業化時期以來,為什么西歐一些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農民不再涌入城市去尋求工作?對這個問題需要從工業化的歷史進行分析。
西歐一些國家的工業化,從18世紀70年代算起,至今已有200多年的歷史。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大量農民涌入城市,補充了各行各業的工人隊伍。到現在,農村的多余勞動力已經釋放完畢。現在西歐一些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從事農業勞動的人數只占全國勞動力人數的百分之幾,居住在農村的人口也只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幾。在這些國家,農民擁有自己的家庭農場,擁有自己的住宅,城鄉的生活條件一樣,甚至農村空氣更清新,比城市更能吸引人居住。同時,社會保障體系覆蓋全社會,城鄉沒有差別,現在的農民為什么還要舍棄自己的家庭農場和住宅,跑到城里去打工呢?進城打工,那是他們祖父一代甚至曾祖父一代的事情,他們根本不考慮這個問題。這種情況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從西歐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農村和農民的現狀,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四點啟示:
第一,西歐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城鄉一體化是在工業化后期實現的。而在這之前,即在工業化中期,城鄉一體化的體制障礙已經消失或基本消失,這就有利于雙向城鄉一體化的推進。目前中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由于體制上的某些障礙仍然存在,所以有一個先實現單向的城鄉一體化,再實現雙向的城鄉一體化的過程。消除城鄉一體化的體制障礙應當成為改革的重點之一。
第二,城鄉生活條件一樣,這也是西歐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在工業化后期實現的。對中國來說,這是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因為基礎設施較差,公用事業的發展程度較低。但僅僅依靠國家財政和地方財政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這些領域,以加快縮小城鄉生活條件之間的差距。
第三,社會保障體系覆蓋全國并使城鄉沒有差別,是一個漸進的也是一個較長的過程。根據中國的國情,有必要有序地逐步推進。但最終必須闖過這一關。歸根到底,這是國家和地方是否有足夠財力的問題。因此,經濟發展不可停滯,財政收入應當與經濟同步增長,甚至需要略快增長。
第四,也許最為困難的問題是居民觀念的更新。這里所說的居民觀念更新主要是指:無論住在城市還是住在農村,居民都應當有公民意識,有權利和義務的意識,有社會責任感。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不是什么人的恩賜,也不允許任何人對它進行破壞。有了這種觀念更新,社會保障體系才能長久存在。
阿東說:“蠻好。我姆媽原先每天七點半叫阿里起來,現在叫他提前起。把錄音機帶著,到東湖邊去放哀樂。那里沒有什么人,放多大聲音都不怕。”
這樣,我們對于全國許多地方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會有新的認識、新的要求和新的期待了。
社會主義新農村,豈止是一排排新蓋的住宅樓。應當進一步詢問的是:搬進來居住的住戶們是不是領到了房產證?住戶們有沒有權利出租、抵押、轉讓?也就是說,有沒有產權?此外,社會保障制度是否落實到人?
新農村是一個社區。這里的公共設施如何?孩子們要進幼兒園、小學,有沒有這樣的設施?病人要住醫院,附近有沒有?平時有沒有衛生站可以看病?有沒有救護車可以運送急癥或重病患者?有沒有敬老院之類的設施?水、電、氣、暖的供應狀況如何?方便不方便?這些都是建設中應當關注的問題。
新農村可能位于遠郊,甚至位于距市中心很遠的地帶。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考慮交通和居民生活設施建設。既然要逐步縮小城鄉在生活條件方面的差距,那就不能僅僅以讓農民搬進新房居住為滿足。
新農村作為一個社區,住戶的業主權益應當受到尊重,受到保護。社區應設置公共活動的場館和聚會的會所,使業主有條件行使自己的權利。民主和自治作為社區管理的原則,要始終堅持不懈。
最后,無論城市還是農村的居民,都應當有遷移的權利,也就是選擇居住地點的權利。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大城市的規模應有較嚴格的控制,縣城和鎮應該是放開的,容許居民遷入遷出。愿意住在城市還是愿意住在農村,居民可以自行選擇和調整。如果有條件的,也可以兩邊都有家。這樣城鄉的差距在居民的觀念和心理上自然而然就縮小了。
總之,建設新農村的住房并讓農民搬進去住,這只不過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第一步。要讓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名副其實的新農村,還有大量工作要做,而且決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完成的。在2008年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我曾指出,改革開放開始后的前30年,我們著重于國有企業體制的改革,這一改革在30年內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盡管國企體制改革中還有一些遺留問題需要繼續解決,但大勢已定,改革已不可逆轉。從2009年算起,改革開放后的后30年,即到2039年為止,改革的重點將是城鄉二元體制,以及通過城鄉二元體制改革而實現城鄉一體化。由于前面所說的城鄉一體化任務艱巨,所以用30年的時間能否實現城鄉一體化,還要看我們的努力程度。
計劃經濟體制有兩大支柱:政企不分和產權不清晰的國有企業體制,以及城鄉生產要素分割和農民沒有明確產權的城鄉二元體系。改革開放后的前30年,改革重點是國有企業體制改革;改革開放后的后30年,改革重點是城鄉二元體制;那么,在改革開放60年左右,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作為一種體制將最終退出歷史舞臺。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IYi-ning
(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we should promote the two-way urban-rural integration,which means that the rural citizens can resettle in the city and the urban citizens can also resettle in the rural areas.At present,causes for the existing one wa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o not only include the separated rural and urban residence registration system;the dual structural land system is the more important one.And the rural collective ownership in rural areas is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way urban-rural integration.We should eliminate this institutional barrier,give the rural citizens more right on property,and make the rural citizens to expand income resources by becoming a shareholder,mortgaging or transferring the ownership of housing,land for contract operation and private housing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come and consumption and expand consumption.The two-wa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will make China's economy to be citizen consumption-oriented,benefit build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and benefit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harmoni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wo-way urban-rural integration;property right of rural citizen;income from property;socialist countryside
F120.4
A
1007-8266(2010)11-0007-04
厲以寧(1930-),男,江蘇省儀征市人,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管理科學中心主任、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民營經濟研究院院長、貧困地區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交流協會顧問,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執行副理事長,中國企業投資協會副會長等職,曾任第七屆、第八屆、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主要從事宏觀經濟政策、經濟思想史等領域的研究,在對中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經濟運行實踐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發展了非均衡經濟理論,并運用這一理論解釋了中國的經濟運行,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并從中國經濟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國經濟的構想,并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對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先后獲得“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孫冶方經濟學獎”、“金三角”獎,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獎(個人最高獎)、第十五屆福岡亞洲文化獎——學術研究獎(日本)等,主要代表作有《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經濟學的倫理問題》、《轉型發展理論》,《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羅馬—拜占庭經濟史》、《論民營經濟》等。
林英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