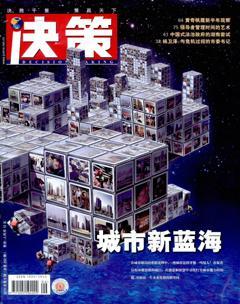貧困縣的造城運動
夢想中的美麗新城未建成,留下的卻是一幢幢“爛尾樓”。這樣一個近似“天方夜譚”的“神話”,為什么會真真實實的發生?
夢想中的美麗新城未建成,留下的卻是一幢幢“爛尾樓”。這樣一個近似“天方夜譚”的“神話”,為什么會真真實實的發生?

[城·事]
內蒙古清水河縣是一個財力只有3000多萬元的貧困縣,當地大多數居民仍然生活在破舊的窯洞中。早在1998年,一位上級領導到清水河縣考察工作,認為老縣城山路崎嶇、交通不便,妨礙經濟發展,不如選一個地理位置好的地方建新區。于是,縣領導計劃投資60億,建造面積為5平方公里的新城。
由于資金無法到位,財力難以支撐,新區建設和搬遷工程于2008年擱淺。歷經10年的造新城運動,耗費了上億元投資,不少單位因此背上了外債。由于沒有得到有關部門的審批手續,如今,這座“半拉子”新城,只能以“違規建筑”名義矗立在荒山之上。
[案例分析]
一個貧困縣為何“敢于”以超過自己財力收入200倍的“勇氣”建新城?夢想中的美麗新城未建成,留下的卻是一幢幢“爛尾樓”。這樣一個近似“天方夜譚”的“神話”,為什么會真真實實的發生?貧困縣的造城運動以喜劇開始,以悲劇結束,這一失敗的案例帶給我們哪些沉痛的教訓?
“拍腦袋”工程
王玉珍(南京市委黨校教育長、教授)
建如此規模浩大的工程,唯一的依據就是上級領導的“點子”,這是一個典型的“拍腦袋”工程。因為領導有想法、有動議,就決定上馬該項工程,這決定了工程從一開始就埋下了悲劇的隱患。
因為“拍腦袋決策”是決策后才為決策尋找合理依據,才為決策補辦各種手續,為決策要實現的目標尋找各種路徑,這種做法必然導致一系列違背規律的現象發生。
首先,決策不是深入縝密調查研究的產物。為什么要遷城?遷往哪兒?應有自然地理位置、經濟社會發展、居民人文心態等方面的調研材料,而在清水河沒有這些基礎資料就已決定動遷。
既然已經決定“造新城”就要從規劃入手,新城的規模大小、空間布局、功能設置等必須進入決策程序,依據新城規劃測算建城財力,經相應部門批準、縣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方可實施。但所有的決策程序這里都沒有,就計劃斥資60多億元建新城。“預算”是如何算出的?它的客觀依據何在?誰也說不清。
其次,新城建設應是規劃藍圖在先,而后按規劃實施建設。但清河新區規劃的總面積超過了現有城區的3.4平方公里,不符合1997年清水河縣編制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規定。而縣城遷址需要由國家民政部審批,審批的要件中要求必須符合縣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否則需進行修改。但當時并沒有修改縣級規劃的相關規定。因為求快,新區建設并沒有進行土地報批,形成了事實上的違法用地。
再次,新城建設需要有穩定的資金來源及財力支撐。盡管有關部門也做了估算,大致決定了資金籌措來源,但這些資金籌措渠道只是寫在紙上的,并未具體落實到位。在沒有正常“預算財力”的渠道下,如此巨大的工程依靠“東挪西借”強行上馬,這種打“強心針”似的發展注定是短命的。
從新城建設的“勇敢”決策,到新城選址再到新城建設資金的估算以及所謂的市場化運作,這一連串的失誤未能及時制止。10年之后,這個殘局至今無法收場。
當時做出拍板決定的領導,因為調動頻繁,至今無人受責。因為決策失誤、違背經濟發展規律而造成的種種惡果,得不到檢查監督部門的及時制止,相關責任人得不到相應的懲處。這種形同虛設的檢查監督機制,是造成此類案例的制度性原因。
科學決策的缺失
顧麗梅(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清水河縣的造新城運動,所反映出決策隨意性,這是中國的政策制定體制中存在的普遍問題,也是美國學者拉塞爾·林登在《無縫隙政府》中所言,政府部門對來自組織內部的需求,尤其是對來自上級組織的需求反饋積極且迅速;而對于組織外部的公眾和客戶端需求反應遲鈍。正是在這種組織環境下,才產生了清水河縣科學決策的缺失。
在某種角度上而言,清水河縣造城工程是為了上級領導而造,而不是為了公民而造。至于這一需求和決策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現實,已經成為決策考慮的次要因素,典型地反映了決策的隨意性。
城市究竟是為誰而建?城市的建設與發展是為了讓當地的民眾生活得更好,經濟社會能夠發展。因此城市建設的主體是公民,城市的建設應當是為了讓公民生活更幸福。可是在清水河的造城運動中,當地居民并未感受到這種幸福。除去道路修繕、環境衛生、市政建設等顯而易見的變化難尋蹤跡外,居民的不滿還集中于各種社會福利的“不到”、“遲到”與“少到”之中。決策主體的缺失,產生了非理性的決策。
另外,決策缺乏可行性和客觀性。可行性是決策的主要原則之一,這是確保決策有效執行和政府行為有效性的前提。從決策的角度而言,清水河縣造新城從根本上違背了決策的可行性原則。缺乏可行性與客觀性的決策必然會導致,曾經希望能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新城,成為滿目瘡痍的“爛尾城”。這本身也是政府壟斷政策制定的必然結果。
[深度解剖]
清水河縣的案例也不是個偶然現象,在全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現在各地都在大興造城運動,其中的問題很多。各地為何熱衷于造新城運動?這樣的發展模式折射出哪些問題?
“強政府”模式之弊
王玉珍(南京市委黨校教育長、教授)
類似清水河縣的案例在我國屢屢發生,是有著深刻原因的。我國的新城建造大都采用政府強力主導,通過借債或運營土地的方式進行,然后先把行政中心搬到新城,再慢慢帶動人氣和土地升值。通過如此這般的操作最終完成新城的建設。
之所以選擇這種模式,是因為這種模式在我國行得通且辦事效率高。這種建設模式,與我國強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有直接的關系。政府是行政決策的主體,擁有行政執法和行政管理的職能,政府的至高權力決定了它幾乎沒有干不成的事。財力不濟甚至沒有基本的財力,只要是政府工程或政府出面擔保,就可以大規模舉債進行,政府甚至可以出臺相應的政策支持該項目的實現。
這樣的制度安排,使得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強勢地位凸顯,這種“強政府的發展模式”助推了政府的非理性行為。各地在推進“造新城運動”時,無一例外地選擇政府主導、強力推進的發展模式,就是這種非理性行為的泛化表現。
這種“強政府的發展模式”,在決策正確運營方式科學的情況下,會產生辦事效率高辦事效果好的結果。而在決策錯誤時會產生截然相反的結果,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從地方官員的角度來說,“以GDP為中心的政績觀”扭曲了他們的價值取向。在我國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績,很重要的是考核地方GDP的總量與增幅,而GDP的快速增長主要靠大的項目的拉動。從經濟學的角度講大項目往往需要大投資,而大投資會帶來大的經濟體量,大的經濟體量會帶來大的GDP總量。
由于GDP作為地方政府和官員政績的主要標竿,在這樣的價值取向下,只要對GDP增長有利,可以不擇手段、不問代價。這就出現了,政府官員對于造橋修路、標志性建筑、新城建設等一些大的工程項目,特別的敏感,特別的重視,特別的有興趣。因此,各地紛紛爭上大的項目,我國城市“變臉”過快的現象便頻頻發生。
驅使清水河縣不惜一切代價地進行造新城運動的內在動力,就是追求GDP的政績觀。因為只要新城建立起來,對于地方政府來說不僅是漂亮的形象工程,而且是卓著的政績工程,這類工程會成為政府官員升遷的主要依據。
[政策建議]
如何確保決策的科學性?
顧麗梅(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第一、強化法治意識,確保決策產生與執行過程的合法性。以法治的原則約束決策制定過程,對于更好地制定決策至關重要。清水河案例揭示出的正是因為法治意識淡漠,在沒有通過審批的情況下,未批先建。
依法行政是指國家的一切行政管理活動,都必須嚴格依法進行。依法行政不僅強調實質合法性,也強調程序合法性。行政管理的依據是法律,地方政府的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法律是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管理活動的依據。
規則、制度是社會的規范,政府管理者和被管理的相對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都要按法律來規范自己的行為。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強化法治意識,就會杜絕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
第二、決策主體的準確界定,鼓勵公共參與,建立科學的決策機制。政策中最重要的是鼓勵公共參與,尤其是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公共參與雖然不能確保最優的決策產生,但是可以保證不會產生最差的決策。公共參與的過程就是決策進行充分調研和論證的過程,這樣才能確保決策的科學性。
筆者認為決策制定的優劣,直接關系到決策的執行、政府管理的有效性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公共決策的制定本身實質上是公權力的行使,對公眾之間的權利義務會產生直接的影響,因此公共決策的制定應當受到行政法的約束。
正如新公共參與理論所言,公民并非簡單地參與政策的制定,影響政策制定的過程,對政府決策與執行施加壓力;而是認為公共參與的主要目的不僅是分享政府的權力,通過公共參與,同時也可以分擔政府的責任,防止不當的決策產生,以建立一個責任共享、利益共擔的機制。
第三、決策制定與執行應遵循可行性原則、合理性原則。以法治的原則約束決策制定過程,對于更好地制定決策至關重要。決策中的公民參與是為了便于決策的實施。
故而,決策要綜合考慮社會環境、決策成本、社會大眾的接受等諸多重要因素,確保公共決策真正代表了公民的利益,保證了決策中的公平與正義,而且體現了決策的可行性與客觀性,才是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公共決策,才能提升公民對于公共決策的合法性認同和政府的公信力。
“清水河現象”治理需標本兼治
王玉珍(南京市委黨校教育長、教授)
“清水河現象”的產生,與錯誤的政績觀有密切的聯系。將GDP的數量和增速作為衡量政績的主要指標,顯然扭曲了領導干部的價值取向。
改變這種現象必須有正確的價值導向,即通過健全政績考核評價體系,科學評估干部的工作實績。考核評價是干部選拔任用和管理監督的基礎環節,是“指揮棒”和“風向標”,對促進科學發展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評價作用和監督作用。干部能否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有沒有科學的考評機制。
清水河縣的發展之所以出了大麻煩,是背離了科學發展的宗旨,采用了錯誤的發展路徑。如果在新城建設中更多地將當地人民的切身利益放在中心位置,多些深入的調查研究,多聽聽他們的訴求,整個動遷規劃就會實事求是。
在具體的建設程序上,如果能遵循自然規律、經濟規律,在力所能及的基礎上實施新城建設,新城的建設規模就不會攤得如此之大,失誤也不會如此之多,損失也不會如此慘重。科學發展必須圍繞人本中心,遵循客觀規律,從當地實際出發,必須一以貫之。
清水河縣從新城建設的拍板到建設進程中的一錯再錯,說明現行體制的自身修復功能和糾錯機制已完全缺失,本質上是制度的缺失。因此,建立健全相應的制度,以制度規制行為已迫在眉睫。
通過制度設置規范決策程序,違規者將付出沉重代價。以制度管人,將違規決策行為降低到最低程度。但愿清水河縣的悲劇不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