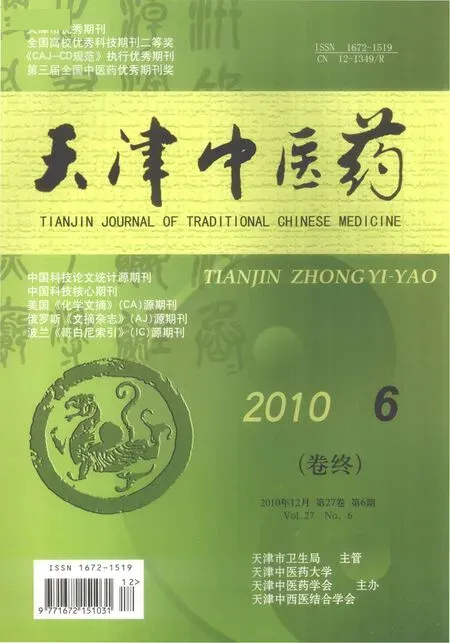同病異治、異病同治血小板增多/減少癥案例探析
周仲瑛
(南京中醫藥大學,南京 210029)
同病異治、異病同治是中醫辨證論治特色在臨床的具體體現,也就是說,病同證異者,治法亦當有異,病異證同者,治法亦基本相同,但同時還應異中求同,把握疾病的共性;同中求異,注意疾病的個性。并在肯定療效的基礎上,應用中醫理論結合現代知識和方法,尋求其療效機制,使中醫藥理論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創新。
臨床實踐表明,同病異治、異病同治的理念,不僅適用于中醫傳統的病證名,還同樣適用于現代西醫學的病名和癥狀名。茲以血小板增多癥和血小板減少癥不同治法的>效案為例,并作探析,以冀提供一條值得重視的臨證思路和研究途徑。
1 原發性血小板增多癥
例1:患者,男,30 歲。
初診:2007年6月4日。1998年因反復感冒,去某醫院檢查發現血小板(PLT)增多,住院確診為“原發性血小板增多癥”。曾服用羥基脲治療,停藥又復增多。現查PLT851×109/L。癥見面色潮紅,偶有肢麻,兩胯常有酸脹疼痛,舌苔黃、中部膩,脈右細,左細滑。辨證屬熱瘀營血,肝腎陰虛。方用犀角地黃湯加味:水牛角片先煎20 g,生地、白薇、漏蘆、鬼箭羽、茜草根各15 g,赤芍、牡丹皮、紫草、地龍、川牛膝、玄參各10 g,炙水蛭、生甘草各3 g。1劑/d,煎服2次。
二診:2007年11月7日。
兩胯脹痛能平,偶有肢麻,口干不顯,大便日行1~2次,偏爛,舌紅苔薄黃膩,脈細。復查PLT 681×109/L,仍守原法出入。
原方加葛根、丹參、澤蘭、雞血藤各15 g,木賊草10 g,炮穿山甲 6 g(先煎),川石斛 10 g,去漏蘆、茜草根、甘草。1劑/d,煎服2次。
此后患者來診,均以二診處方隨癥加減,多次復查血小板漸趨下降,但尚時有波動,動態觀察到2009年3月降至正常,無反跳現象,臨床癥狀亦不明顯。
按:本病臨床多見頭脹痛、面紅目澀、口苦咽干、五心煩熱、手足脹、失眠多夢、大便干結、舌暗紅、脈絡有瘀、苔少微黃、脈弦細沉數,重者可伴有胸腹痞滿、肝脾腫大。根據本例的臨床表現,病由肝腎陰虛,絡熱血瘀所致。針對這一發病機制,治以犀角地黃湯為主方涼血化瘀,配伍涼血之紫草、白薇、漏蘆,因瘀重于熱加炙水蛭、地龍、川牛膝、穿山甲、鬼箭羽、澤蘭、雞血藤、丹參等以消瘀。配以木賊草、茜根炭涼血化瘀。瘀熱傷陰佐以玄參、石斛養陰清熱。取得滿意的療效。提示從“瘀熱”辨治血小板增多癥,以涼血化瘀為其基本治法,是切合臨床客觀實際的,而針對個體加減配伍,同中求異,又是必要的。
例2:患者,女,29 歲。
初診:2003年5月27日。
2003年3月突覺胸悶,呼吸困難,稍有心慌,血查血小板計數最高1300×109/L。當即住院,服用羥基脲(0.5 mg,2次/d),注射干擾素1個月余,因反應較大難以續用,并作多次血小板分離術,血小板計數仍難穩定下降。近兩年來,月經逐漸減少,目前一日即盡,有塊,色暗。形寒、怕風、畏寒、腰冷,大便日行2~3次,成形,納差,厭油膩。半月來體質量下降3~3.5 kg,苔薄黃膩質暗紅,脈細。辨證屬氣虛血瘀,治擬益氣活血。
生黃芪 20 g,當歸 10 g,赤芍 10 g,川芎 10 g,桃仁10 g,紅花6 g,澤蘭15 g,炙水蛭5 g,鬼箭羽20 g,川牛膝 10 g,熟地黃 10 g,山茱萸 10 g,炙桂枝10 g,砂仁(后下)3 g。1劑/d,煎服 2次。
二診:2003年6月24日。
骨髓活檢:符合原發性血小板增多癥改變,纖維組織增多明顯。并查見脾大。復查PLT 676×109/L,白細胞4100×109/L。近期未再做血小板分離。面黃欠華,氣短不能多言,稍有胸悶,頭昏,周身酸脹,尿頻,納可,月經過期6日不潮。苔薄黃膩質暗有齒印,脈細。氣虛血瘀,脾腎陽衰。治予溫陽益氣,活血化瘀。
潞黨參 15 g,鹿角片(先煎)10 g,枸杞子 10 g,肉桂(后下)3 g,生黃芪 25 g,當歸 15 g,牡丹皮 10 g,丹參15 g,雞血藤 20 g,桃仁 10 g,紅花 10 g,砂仁(后下)3 g,山茱萸 10g,菟絲子 15 g,懷牛膝 10 g,淮山藥 15 g,仙靈脾 10 g,補骨脂 10 g,熟地黃 10 g,鬼箭羽20 g,炙水蛭6 g。1劑/d,煎服2次。
三診:2003年8月12日。
仍覺頭昏心慌,氣短減輕,四肢發軟,感覺遲鈍,食納平平,大便偏爛。查血小板576~666×109/L,白細胞4200×109/L。苔黃薄膩質暗,脈細數。氣虛血瘀,腎陽不振。
生黃芪 25 g,當歸 10 g,黨參 15 g,鹿角片(先煎)10 g,枸杞子 10 g,仙靈脾 10 g,桃仁 10 g,紅花10 g,鬼箭羽 20 g,炙水蛭 4g,肉桂(后下)3 g,炮穿山甲(先煎)6 g,山茱萸 10 g,菟絲子 15 g,補骨脂10 g,熟地黃10 g,淮山藥12 g。1劑/d,煎服2次。
四診:2003年9月16日。
病情穩定,頭稍昏,前日受涼,自覺腹部不適,納谷一般,胃部怕冷,脫發,多言氣短,兩臀怕冷。復查PLT 534×109/L,白細胞 3500×109/L。苔薄黃質暗紅,脈細。再予益氣活血,溫養肝腎。
潞黨參15g,生黃芪20g,當歸12g,仙靈脾10g,肉桂(后下)4 g,鹿角片(先煎)10 g,桃仁 10 g,紅花6 g,炙水蛭 4 g,土鱉蟲 6 g,澤蘭 15 g,鬼箭羽 20 g,生蒲黃15 g,雞血藤15 g,補骨脂10 g,菟絲子12 g,川芎10 g,熟地黃10 g。1劑/d,煎服2次。
五診:2003年11月4日。
因頭昏心慌不能支撐,住鼓樓醫院半月,經顱多普勒:腦血管痙攣。經治癥狀改善,出院時查:PLT 571×109/L。目前頭昏不著,胸悶壓塞不舒,稍有氣短,頭皮知覺遲鈍,有緊縮感,口稍干,苔黃薄膩質暗,脈細。經潮量少,質暗,1天即停。仍從肝腎不足,氣虛血瘀治療。
潞黨參 15 g,生黃芪 25 g,當歸 10 g,赤芍 10 g,川芎 12 g,葛根 20 g,仙靈脾 10 g,熟地黃 10 g,山茱萸10 g,菟絲子12 g,鬼箭羽20 g,桃仁10 g,紅花6 g,石菖蒲 9 g,炙水蛭 5 g,生蒲黃 15 g(包),川牛膝10 g。1劑/d,煎服2次。
六診:2004年1月31日。
自覺癥狀良好,早晨鼻涕帶有血絲,食納知味,腰臀部冷減,雙足仍冷,月經過期半月,左上腹痛。苔黃質偏紅,脈細。面色紅潤。PLT從390×109/L下降至189×109/L。守法出入。
制附片 6 g,肉桂 4 g(后下),熟地黃 10 g,山茱萸 10 g,生黃芪 30 g,淮山藥 15 g,補骨脂 10 g,鹿角片 10 g(先煎),潞黨參 15 g,當歸 10 g,炮姜 4 g,焦白術 15 g,桃仁 10 g,紅花 6 g,炙水蛭 5 g,仙靈脾10 g,丹參 15 g,鬼箭羽 15g,葛根 20 g,川芎 10 g,菟絲子10 g,炙甘草3 g。1劑/d,煎服2次。
其后病情穩定,去南方恢復工作。
按:根據四診所見,本例患者以氣虛、陽虛癥狀突出,因腎主骨生髓,髓生血,故病源于腎;舌質暗紅,周身酸脹,感覺遲鈍,經潮后期,量少色黑,脾大等則屬于中醫的血瘀證。與西醫學認為血小板增多使血液黏度增加,頗為符合。故采用益氣溫陽,活血化瘀治法,方中黨參、黃芪益氣,鹿角片、仙靈脾、補骨脂、菟絲子、肉桂溫陽,熟地黃、山茱萸、枸杞子等補腎,當歸、赤芍、川芎、桃仁、紅花、川牛膝、澤蘭、炙水蛭、鬼箭羽等活血化瘀。藥證相合,療效顯著。
原發性血小板增多癥系骨髓增生性疾病,屬于髓系的克隆性疾病,其特征為骨髓中巨核細胞過度增生,血中血小板異常增多,并可伴有質量異常。臨床以持續性血小板增多,伴皮膚黏膜出血,血栓形成,脾臟腫大為特征。本病的治療,西醫常以骨髓抑制劑如羥基脲、甲異啶、馬利蘭等抑制和減少血小板生成,或予干擾素,或施血小板單采,或予抗血小板功能藥物如阿斯匹林、潘生丁等。
中醫治療一般以活血、破血、逐瘀為主,或佐清熱解毒,或佐化痰祛濕。普遍認為益氣溫養之品刺激骨髓造血組織增生,增加血細胞數,屬相對禁忌,而例2用益氣溫陽之品卻降低了血小板數,抑制了骨髓巨核細胞增生,推斷可能是本法具有調節造血微環境或造血刺激因子的作用。例1則從“熱瘀營血,肝腎陰虛”辨治,用涼血化瘀方藥獲效。顯示了同病異治的特色和優勢。兩者異中有同的病理基礎主要在于血瘀。故均重視活血化瘀藥的應用。表明辨證論治,是中醫藥治療疾病的根本法則,只要辨證準確,常能受到顯著療效,而其機制則值得進一步研究。
2 特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
例1:患者,女,25 歲。
初診:2009年3月13日。
兩年前夜晚睡覺時口中流血,肌膚黏膜有出血點,去醫院血查血小板減少,多年來查PLT最低3×109/L,有時最高達10×109/L,診斷為特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常用潑尼松維持。自覺疲勞乏力,腿軟,經潮后期,血量偏多,苔淡黃薄膩,質暗紫,脈細滑。心脾兩虛,肝腎不足,氣血虧耗。
潞黨參12 g,炙黃芪15 g,當歸10 g,炒白芍10 g,炙甘草 3 g,制何首烏 10 g,制黃精 10 g,焦白術 10 g,熟地黃 10 g,枸杞子 10 g,雞血藤 15 g,仙鶴草 15 g,腫節風 15 g,花生衣 20 g,紅棗 4枚。1劑/d,煎服2次。
守法守方加減,曾經配伍過淮山藥、山茱萸、茯苓,或生地、地錦草、旱蓮草,或枸杞子、雞血藤、炙甘草,觀察至9月底。先后來診6次,療程半年,血小板不升。
再診:2009年10月30日。
10月中旬,腹痛兩天,檢查黃體破裂,住鼓樓醫院輸血小板、掛激素治療。現仍有腹痛腰酸,月經7~8日不盡,晨起鼻衄,口干,手心熱有汗,齒衄,下肢有瘀斑,面紅目赤,胸背下肢瘙癢。苔黃薄膩,質暗紅,脈細滑。查血小板計數11×109/L。轉從肝腎陰虛,絡熱血瘀治療。
水牛角片先煎20 g,赤芍12 g,牡丹皮10 g,生地 20 g,腫節風 20 g,地錦草 15 g,旱蓮草 12 g,花生衣 20g,羊蹄 9g,紫草 10g,仙鶴草 15g,地膚子 15g,地骨皮12 g。1劑/d,煎服2次。
復診:2009年11月28日。
藥服月余,近查PLT 116×109/L,地塞米松已從原先每日5片減少至1片,牙齦出血基本控制,皮膚未見紫癜,經潮量少,手心熱轉平,面紅目赤,苔黃質暗,脈細。守法觀察。
水牛角片先煎20 g,赤芍12 g,牡丹皮10 g,生地20 g,腫節風20g,地錦草15g,旱蓮草12g,花生衣20g,羊蹄 9g,紫草 10g,仙鶴草 15 g,雞血藤 15 g,地膚子15 g,地骨皮12 g,炙女貞子10 g。1劑/d,煎服2次。
按:本例初從心脾兩虛,肝腎不足,氣血虧耗辨治,仿歸脾湯、八珍湯意,守法守方,觀察半年,血小板不升,PLT 11×109/L,審其除齒鼻出血,下肢瘀斑外,并見面紅目赤,口干,手掌心熱,肌膚瘙癢,經潮后期,結合苔脈,轉從肝腎陰虛、絡熱血瘀、瘀熱動血治療,用犀角地黃湯加味,滋陰涼血,化瘀止血,并逐步撤減激素。藥服月余,血小板上升,穩定在正常值以上。顯示修正辨證診斷的必要性,若單一辨病治療,恐難另辟蹊徑,取得改善。對照血小板增多癥例1,應屬異病同證同治,而又同中有異,增多者瘀重于熱,故化瘀之藥為多,化瘀重于涼血;減少者,熱重于瘀,故用藥涼血重于化瘀。而其中深層的療效機理,尚難以用藥效的雙向調節作用所能解釋。
例2:患者,女,28 歲。
初診:2009年5月20日。
1998年患者出現鼻腔、牙齦出血,皮膚瘀斑反復發作至今已10年余,確診為“特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曾用大劑量激素、免疫抑制劑等治療,有所控制,但病情反復難愈。2009年3月因全身皮膚瘀斑、紫癜,血小板計數12×109/L。曾在當地醫院使用大劑量激素潑尼松治療2月余,血小板計數僅升至35×109/L。肌膚散見瘀斑,偶有齒衄,月經量多,神疲乏力,腰酸腿軟,夜寐夢多,口干欲飲,二便尚調,舌質暗紅苔薄黃,脈細數。擬從肝腎虧虛,陰血不足,血失歸藏治療。
生地15 g,山茱萸10 g,制何首烏10 g,阿膠珠10 g,白芍10 g,黃精 10 g,女貞子 10 g,旱蓮草12 g,地錦草15 g,牡丹皮10 g,腫節風20 g,雞血藤15 g,茜草根10 g,仙鶴草15 g,血余炭10 g,花生衣20 g,炙甘草3 g。1劑/d,煎服2次。
二診:2009年12月23日。
上方連續服用2月余,并停用激素,皮膚瘀斑消失,月經正常,2009年10月16日PLT計數103×109/L,諸癥已平,無出血及瘀斑,今查PLT計數134×109/L,甘油三酯5.48 mmoI/L。繼守原法鞏固。
原方加山楂10 g,決明子10 g,澤瀉12 g。1劑/d,煎服2次。
按:本案從肝腎陰虛,陰血不足,血失歸藏入手,以《類證治裁》六味阿膠飲、《景岳全書》茜根散、《簡便方》二至丸加減,補肝益腎,寧絡止血。方中生地、白芍、山茱萸、旱蓮草、炙女貞、制何首烏、制黃精、炒阿膠珠補益肝腎,填精益髓,滋陰養血,生地、旱蓮草又具涼血止血之功,牡丹皮、地錦草、茜草根既可涼血止血,又可活血散瘀,花生衣、血余炭止血化瘀,腫節風祛風活血、清熱解毒,雞血藤祛瘀血、生新血、流利經脈,仙鶴草養血活血止血,炙甘草益氣補中,調和諸藥。綜觀全方,以補益肝腎,促進髓海生血為主,兼以散瘀、寧絡。止血,且能一藥多用,又結合了現代研究配以花生衣、腫節風治療血小板減少。標本兼治,以治本為主,故能收桴鼓之效。
成人特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95%以上為慢性型,一般認為系自身免疫性疾病,遷延難愈,目前西醫治療以糖皮質激素、切脾、免疫抑制劑等為主,雖提升血小板較快,但維持時間短,易復發。本病屬中醫“血證”、“衄血”、“紫斑”范疇,古又稱為“內傷發斑”。病機以虛為本,與肝脾腎三臟密切相關。因脾主生血又主統血,腎藏精,主骨生髓,精能化血,肝主疏泄,又主藏血,乙癸同源。故生血化血,攝血藏血功能失調,是引起本病的關鍵。而熱傷血絡,絡損血瘀為病之標。
以上兩例,例1根據臨床癥狀,藥效反饋結果,經修正辨證診斷,改從肝腎陰虛,絡熱血瘀論治,用滋陰涼血、化瘀止血法后,獲得明顯轉折。例2則從肝腎陰虛,陰血不足,血失歸藏辨治,以虛為本,熱傷血絡為標,療效亦頗顯著。兩者虛實各異,治法有別,顯示同病異治的特色,而肝腎陰虛又是其異中有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