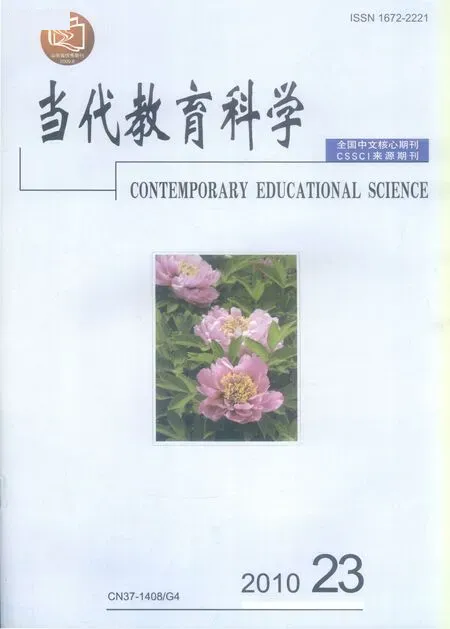先秦儒家人學及其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
●劉琰于欣
先秦儒家人學及其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
●劉琰于欣
以孔子、孟子、荀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基于對現實社會人生的深切關注,闡發了以人的現實人性剖析、理想人格預設及其成就為基本內容的人學思想。這為當代思想政治教育人學研究“以人為本”的理念重構、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最高訴求的目標建構及思想政治教育具體實施中的方法選擇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資源。
思想政治教育;人學;先秦儒家
以人文道德精神見長的中國傳統文化蘊藏著豐富的人學思想資源,其中頗具代表的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闡發的人學思想。這一思想基于對現實社會人生的深切關注,主要涉及人的現實人性剖析、理想人格的預設及成就三個環節。其中雖難免缺憾,但也為當前人學視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理念重構、目標建構和方法選擇提供了諸多重要啟示。
一、先秦儒家人學的現實人性剖析與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重構
先秦儒家人學起始于對人“生而自然”的本性及存在現狀的反思,通過論欲、論心、論群,深入剖析了人的需要、人的思想性、社會性等現實人性。體現人的基本生理心理需要的欲望是人性的重要方面,先秦儒家明確肯定“欲”的存在和滿足具有天然合理性,但同時也深刻體認到“欲”往往與眼、耳、口、鼻、體等感官直接相關,“耳目之官不思”[1],經常為物所蔽,以致“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2]。而且,人之欲無窮,“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余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3]。但縱欲的結果只能是人的物化異化。“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亂其行。……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4]故對于“欲”應堅持養而不縱的適度原則。
“心之官則思”。[5]心官不同于耳目之官,是自主能動的。“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6]心的這種能動性主要體現為知性的思維活動,它能夠根據五官應物而產生的印象察而知之,緣耳而知聲,緣目而知形。但心官之思的關鍵不在于知外物,而在于知善向善。“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7]這是一種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良知良能”,孟子稱之為“性”。荀子雖主“性惡”,但也肯定人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8]由此,先秦儒家為其理想人格的實現奠定了內在的人性論基礎。“人之生,不能無群”。[9]先秦儒家將人視為處于社會人倫關系中的人,強調人具有區別于其他動物的合群的社會屬性。“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10]人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決定了人只能生活于諸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社會關系之中。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11]最終卻能“牛馬為用”,成為能夠勝物用物的主體,其原因就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12]由此形成了先秦儒家人學的社會性視角。
先秦儒家人學的現實人性剖析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人學的理念重構具有重要啟示:其一,以充分尊重教育對象的個人需要、價值和尊嚴為起點,注意保持個人需要和社會需要、階級需要之間的適度張力。其二,進一步強化教育對象的主體意識,以切實落實和充分發揮教育對象的主體地位與能動作用。人具有異于禽獸的思維能動性,這決定了教育對象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者也是學習和自我學習的主體,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具有能動性、自主性、創造性。先秦儒家由“心之官則思”[13]到“人皆可以為堯舜”[14],高揚了人在自我完善中的主體性。今天,我們更應牢記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以教育對象主體的發展完善為目標,也有賴于教育對象主體的積極能動性的充分發揮。
二、先秦儒家人學的理想人格預設與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建構
先秦儒家通過剖析現實人性,深感現實中人的不完滿,由此根據自己的價值標準和道德理想對人“應當是什么”作出了規定和預設,提出了以仁義德性為總特征的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模式。
“內圣”是從理想人格的內在方面講,集諸種美德于一身。“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15]“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謂神”。[16]內圣品性既是善,具有為人們所向往、合乎人們意愿的善良德性;又是真,善良的德性真正為主體所具有而非外在矯飾;還是美,善良的德性充實于身體的方方面面,彰顯出內在的人格美。這樣方能展現外化為強大的感染力和潛移默化、神妙難測的教化作用。在諸多內圣品性中,仁義之德是其總特征。先秦儒家從人異于禽獸的類的視角出發,認為人的本質即在于仁義德性。“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17]仁義之德是最高的道德原則,其他如智、勇、忠、恕、孝、悌、恭、寬、信、敏、惠等美德,或為其所統帥,或由此而生。
“外王”是由內而外的人格展現,即將美好的仁義德性外化于治國安民的社會實踐,實現了經世致用、美政美俗的社會事功。“外王”的具體形式不拘一格。首選的是“美政”,“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18]退而求其次的是“獨善其身”,但這并非專注于個人的心性修養,而是將自身的內圣品性外化于宗族人倫,展現宗族稱孝、鄉黨稱悌的“美俗”事功。此外,先秦儒家還以親身實踐探尋了另一條“外王”之路,即“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19]正是以此方式,先秦儒家實現了宏大的社會事功,開創了影響深遠的儒家文化傳統。
先秦儒家以仁義德性為總特征的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模式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人學的目標建構具有重要啟示:
其一,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應以最大限度地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最高訴求,以提升人的思想道德素質為直接目的。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內的各類教育,都以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最高目標,并從不同的側面服務于這一目標。而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門塑造人的靈魂的獨立學科,直接關注人的思想道德素質的提升。傳統思想政治教育雖堅持以此為己任,但由于抹殺了教育對象的主體地位而最終偏離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最高目標。今天,我們倡導以人為本,強調教育對象的綜合素質和能力的自由全面發展;同時,也不能因此而忽視由思想政治教育的學科特點所決定的直接目的,必須堅持最高訴求與直接目的的統一。幾千年前的先秦儒家倡導人自身以德為統帥的綜合素質的全面協調發展,凸顯德在人格完善中的統帥地位和導向作用,這一點同樣是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應著力體現的。
其二,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應立足于教育對象的個體生活實踐,在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動態統一中給人以植根于現實的終極關懷。對于如何提升人的思想道德素質,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單向灌輸,試圖以宏大抽象的理論宣講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結果卻自排于人的生命活動之外,使人久而生厭。先秦儒家在其理想人格模式中所表達的致思趨向,為我們解決這一痼疾提供了有益借鑒。先秦儒家認為人具有合群的社會性,群體作為個體生存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具有高于個體的普遍價值。所以個體必須由內而外、由己而人,將自身的內圣品性外化于群體性的社會事功。這個外化過程,也就是個體以各自的方式投入到治國安民的社會實踐中去,與個體當下的現實生活并無二致。誠然,先秦儒家所謂“群”在宗法等級制社會中也不可避免具有“虛幻”性,但其將人安身立命的終極問題落實于個體以群體價值為指向的社會生活實踐,這一致思趨向無疑是可取的。它告訴我們,人精神境界的提升既不可閉門冥思,也不能靠純粹灌輸,只能實現于人自身的社會生活實踐。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必須立足于教育對象的個體生活實踐;同時以社會價值引導個人價值,使教育對象在個體生活實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逐漸融和中,實現思想道德素質與精神境界的自我提升。
三、先秦儒家人學的成人之道與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選擇
沿著內圣外王之理想人格的致思趨向,先秦儒家進一步探討了改造人的現存狀態,實現理想人格的具體舉措,由此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成人之道,同時也為今天思想政治教育具體實施中的方法選擇提供了有益借鑒。
其一,克己復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20]體現群體意志和社會普遍價值的禮作為一種修養方法,首先是“自外作”的,具有一定的強制性、他律性。但久而久之,“禮”會逐漸內化為個體的意志和德性。此時,個體雖仍是循禮而行,但已有了質的飛躍,實現了“從心所欲不逾矩”[21]的道德自律。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施中,同樣存在一個由他律走向自律的過程。自覺自律無疑是我們致力實現的理想境界,而教育對象主體的不成熟性決定了他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古人以“禮”實現他律,今天我們則需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武裝人的頭腦、規范人的行為,這也體現了“灌輸”的必要性。近年來,傳統的“灌輸”法已成為眾矢之的,但我們真正要做的不是拋棄它,而是要改造它。改抽象空洞、居高臨下、外在于人的“灌輸”為緊跟個人生活實際和時代步伐的、生動活潑的“灌輸”。只有這樣的“灌輸”,才能使所講之“禮”真正為教育對象所接受,最終為由他律走向自律創造條件。
其二,為仁由己。先秦儒家在強調禮對人由外而內的他律作用的同時,特別凸顯了主體能動性的自覺發揮。“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于今而志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22]心固然是人能動性的根源,但關鍵在于下足促進道德主體自覺的存心養性的功夫。一方面,“心”如“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23]必須經常用之、操之,從而使善心不斷得到滋養以存之。另一方面,如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放心”,就必須“求放心”,反省內求。“愛人不親,反其仁;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24]所有這些,對于我們今天促進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的能動性的發揮,無疑具有重要啟示。就教育者而言,應注重與教育對象之間的平等交流、雙向互動,為教育對象的積極參與創造有利的平臺和路徑;就教育對象而言,既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和實踐活動的積極參與中培養鍛煉自己的主體能動性,又要隨時反省自己思想變化的心路歷程,以促遷善改過,實現真正的自律自覺、自我提升。
其三,學以致道。人心向善之能動性的發揮離不開“學”。“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25]“學”首先是指讀書,誦五經以知仁義禮法;其次還指“就有道而正焉”,[26]師從有道之人以明道解惑,甚至于向一切人學習,“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27]孔子學無常師,為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的參與者,尤其是教育者,樹立了很好的榜樣。盡管教育者屬于成熟主體,但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施者,能否真正發揮其主導作用、示范作用,關鍵在于提高自身素質,所以學對于教育者來說更重要,學的任務也更繁重。今天,思想政治教育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不僅有自己的特有規律,還有廣泛的學科依托,涉及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等多門學科;教學內容和方式也緊扣時代脈搏,常講常新。這就對教育者的自身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教育者必須時刻注意努力學習,通過繼續深造學,在教學實踐中學,在與教育對象的互動交流中學,千方百計提高自身素質,將自己努力塑造成為既博學多才,又有所專攻,既有才華,又有人格魅力的可愛之人。
其四,躬行踐履。學而知之固然重要,但僅停留于學的層面,并不能真正獲得內化于身的道德品性,故必須將所學知識落實于行動。具體如何行?首先要“近取譬”[28]、“強恕而行”,[29]從自己身邊周圍的小事做起,主要體現為血緣人倫關系中的人倫踐履,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家庭鄰里和睦。然后按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30]的原則,推己及人,由近及遠,在更廣闊的宗法政治關系中從事政治實踐及其他社會實踐,廣布仁道于萬民,做到君仁、臣忠、國治、民安、社會和諧。躬行踐履在諸多成人之道中最重要、最根本。理想人格的成就本身就表現為一個于人倫日用之間躬行不已的過程。
在此,先秦儒家人學彰顯出了強烈的于現世實踐中尋求自我超越的實踐精神,這種精神同樣是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所必需的。傳統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缺乏實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重理論輕實踐。理論的宣講學習固然重要,但親身實踐中對真、善、美的真實感受更有利于高尚人格的形成。所以,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應繼續宏揚先秦儒家的實踐精神,切實加強實踐教學。教育者在關注教育對象個人生活實踐的同時,應采取參觀訪問、社會調查、社會公益等多種形式,盡可能為教育對象開拓、探索更廣闊的社會實踐空間。教育對象應在強化主體意識的前提下,結合個人的生活、工作實踐,積極參與各種教學實踐,在實踐中鍛煉、完善自己,從而推進思想政治教育最終目標的逐步實現。
[1][2][5][7][13][14][16][19][23][24][29]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60.244,244,244,237,244,276,334,303,300,154,302.
[3][4][6][8][9][11][12][17][22]楊柳橋.荀子詁譯[M].濟南:齊魯書社,1985:81,641,594,663,240,215,215,214,454.
[10][15][18][20][21][25][26][27][28][30]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194, 149,140,123,12,184,9,72,65,65.
劉 琰/山東大學機械工程學院副教授,管理學碩士 于 欣/聊城大學思政與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
(責任編輯:劉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