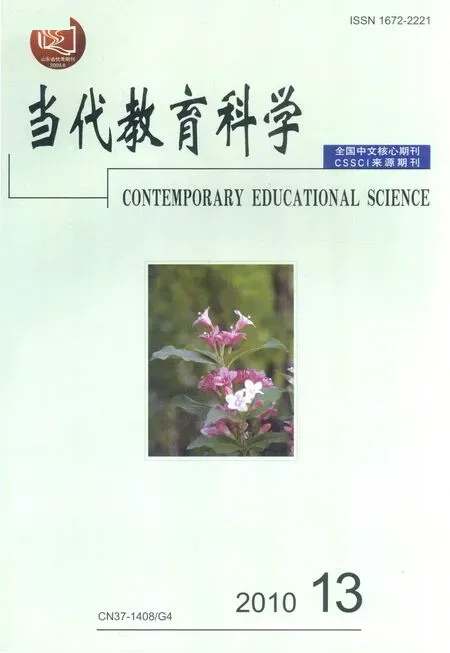關于課堂教學中師生關系的哲學思考
●劉 建
關于課堂教學中師生關系的哲學思考
●劉 建
課堂教學的良善發展依賴于良好的師生關系。從哲學的視角看,實在論強調師生關系的科學性,現象學倡導師生關系的民主性,批判論則著重于師生關系的反思性。當下課堂教學中的師生關系大多秉持唯科學主義,有著強烈的經濟主義與權力主義的利害性質,忽略了民主、平等、自我反思與批判的特質。因此,整合科學、民主與反思,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應該是課堂教學中師生關系的理想訴求。
課堂教學;師生關系;和諧
師生關系是課堂教學中最重要的人際關系,它是教師與學生心智機構相互作用的產物。學校課堂教學質量的良善發展依賴于良好的師生關系,建立科學民主的師生關系,對于提高課堂教學質量有著不可或缺的價值與意義。然而,在當下學校課堂教學過程中,師生關系日益異化為物的利害關系,民主、平等、批判反思意識在課堂中日益消解。因此,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是課堂教學中師生關系的理想訴求。
一、科學:實在論的師生關系
實在論的根本宗旨是“認識”,對客觀、可知的現實世界存在的強調,對經驗證據和中立立場的強調。在課堂教學中,堅持師生關系的實在論,就是強調關系理性,強調師生關系的科學性、原則性、規范性。這種興趣類似哈貝馬斯(J.Habermas)的技術興趣,哈貝馬斯認為,技術興趣帶有其特殊的利益取向,就是控制生存世界的“技術”利益。表現在課堂教學中,其所孜孜追求的就是師生關系的效益最大化。
如果教師堅持師生關系的實在論,那么,其對待課堂中的學生則比較嚴肅、工整,富于理性、原則,倡導建立科學、標準、規范的師生關系。在處理與學生的關系時,重視運用課堂教學的制度規章及教師權威對學生進行制約,重視教師在課堂教學與促進學生發展過程中的主導作用,重視課堂教學中的邏輯性與教學控制。在教師眼中,課堂中的師生關系是科學理性的一維之物。因為囿于事實與價值二分的前設,所以“按章辦事”是處理師生關系的有效規則。
但是,在師生關系上,如果教師秉持著唯科學主義,那么,在這一思想主導下的課堂教學中,教師則會將師生關系視為課堂教學中“可以操縱的東西、事件和環境”,課堂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作為具有固定功能的“兩種人”,而不是具有主觀能動性、富有生命意義的“兩個人”的關系。師與生的關系就是“我與它”的純粹工具關系,學生只是教師的物質、利益或工具而已,師生關系便成為無人的師生關系,無主體的師生關系。伴隨這種利害關系而來的就是課堂霸權主義、家長式作風與獨裁式教學。
唯科學主義的師生關系視課堂中的師生關系為固化之網,處理師生關系不過是攀緣這張事先編織好的結構關系網而已。其本質上是反師生關系的。表現在教學行為上,鑒于教師的經濟主義與權力主義假設,師生關系的維持在于“胡蘿卜加大棒”政策的有效實施。學生之于教師而言類似于斯金納箱子中的鴿子,良好的師生關系緣于不停地給“鴿子們”投送食物,用以交換他們對于自己的理解與信任,并屈服于自己意志。在課堂教學中,教師可能堅持馬基雅維利主義,他們認為與學生關系的好壞并非取決于雙方的人格、能力與性情傾向,也不取決于教學環境與背景,而是在于權威與命令的方式,師生關系的好壞在于命令方式的選擇或者這些命令的上行下達是否通暢。在教師看來,學生們不過是完成教學任務的工具而已,就像木工手中的刨子與斧頭,良好的師生關系在于這樣刨子斧頭是否得心應手。而學生們同樣認為,與教師保持良好關系僅僅通過心靈相通,心心相印,相互理解是不夠的,關鍵在于按教師的意圖行事,不能違背教師的意圖與指令,而從不關心這些意圖與指令本身的正當與否。教師與學生的關系取決于學生是否全然接受教師的訓斥與告誡。在唯科學主義思想的控制下,權力、權威、機制、規章、傳統等成為課堂教學中的無人身操縱,操縱并控制了師生關系的一切。
二、民主:現象學的師生關系
現象學的要旨是“理解”,世界是主體的世界,一旦脫離了主體,世界就成為了非存在。胡塞爾(E.Husserl)認為,有什么樣的主觀結構就有什么樣的客觀結構,客觀的東西就是主觀的東西。他認為現代科學一旦失去活生生的人的意義,排斥了一切主觀的東西和價值的觀點,就勢必引發科學的危機。[1]哈貝馬斯的歷史釋義性知識的對象范圍就是 “說話和行動主體”,它的正確性標準是對話處境中意義的會通,這種知識下的行為是交際行為,它的目的不是操縱擺布別人,也不是千方百計使別人按我的意愿行事,這種交往理性是交際行為者通過與別人共同分有對共同處境的理解,來協調自己和別人可能不同的計劃。可以看出,自由、民主與平等,真誠與關愛,溝通與互動是現象學哲學所秉持之要義,這也是課堂教學中師生關系所應秉持之要義。
布貝爾(Bubel)認為,個人與他人之間的關系是“我與你”而不是“我與它”的關系。我與你的關系真誠地體現在兩個具有主體性的人之間,雙方都不把對方作為實現自己目的的手段,而是真誠地賞識對方,歡迎對方,肯定對方,同時也受到對方的賞識、歡迎和肯定,布貝爾把這種關系叫做“對話”或“交流”。[2]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要建立這樣的師生關系首先要尊重與信任學生。信任是對話的基礎,尊重是交流的前提。教師要取得學生的信任,需要的是教師真誠而坦率地參與學生的日常生活學習,擔負起相應的責任,妥善處理好雙方之間的沖突。教師必須專心致志地運用他的洞察力和見識,既不能采用詭辯的技巧為“自己的真理”進行辯護,也不能采用強制的手段迫使學生就范。
也就是說,課堂教學中的人際生活的基礎是非壓制、非強迫、無暴力的社會關系。課堂教學是教師與學生雙方作為平等主體共同參與、影響和分享的一種活動,并不是教師單方面的控制活動。現象學的師生關系反映的是教學雙方的平等主體地位,而不是以教師為中心或以學生為中心的二元對立的關系。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設身處地的為學生著想,理解對方,關愛對方,平等對待,民主相處。教師要認識和了解學生的思想觀念與行為習慣,了解學生如何思,如何言,如何行。理解學生的人格特質,尊重學生的學習與生活習慣,尊重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激發學生的創造性,為學生實現自身價值做好教育與服務工作。教學過程就是雙方人格與精神的相遇、碰撞、感染和交流的過程。這對于增強雙方信任感,提高雙方滿意度,建立相互支持、互相促進的良好關系有著重要的意義。
當然,如果我們一味強調師生關系的理解性,那就容易陷入相對主義的誤區,避免不了“怎么都行”的課堂無政府主義。教師便會高度重視課堂教學的相對“和平”,樂于做一個“老好人”,重視師生關系的社會性,輕視師生關系的科學性;或者倡導絕對的課堂平等與自由,輕視效益與制度約束;重視師生關系的相對性,輕視人際關系最優化的追求等等。如此一來,它在批判唯科學論的同時,又不可避免地走向另一個極端,這是值得我們警醒的。
三、反思:批判論的師生關系
批判論的要旨是“反思”。康德說:“我們的時代在特別程度上是一個批判的時代,一切都必須受到批判……,因為只有受得起自由和公開的考查與考驗的東西,理性才給以真誠的尊敬。”[3]馬爾庫塞(H.Marcuse)也說:“社會規律就是否定的規律,社會理論必然是否定的理論,如果沒有這種辯證法不能容忍的‘矛盾精神’,社會批判理論就必然會變成一種中立的與實證的社會學”。[4]哈貝馬斯的自我反思性知識的對象就是那些需要進一步說明和解釋的話語和行為,它的正確性標準是能否用批判眼光來進行自我審視,它的利益是從自設的和它設的壓制關系中得到“解放”。批判哲學的追求是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一個擺脫了內外限制的自由關系和達成一種普遍的、沒有壓制的共識。這也應是處理課堂教學中師生關系必須堅持的基本理念。
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要建立反思性實踐觀,努力使課堂教學重新獲致它本應具有的那種批判性力量,以實現課堂教學的正義與平等。教師首先面對自身,才能面對他人,只有先解決自身的問題,才能解決他人的問題。反思批判,辯證分析,理性思考。反思人際問題,總結人際經驗,探求人際規律。反思與學生的關系時,應以“客觀化”的眼光看待所見所聞,以“旁觀者”的心態行言行事,才能擺脫自身與他人的約束限制。例如,教師堅持師生關系的反思與批判性,就要經常思考:在課堂教學中,與學生的關系和諧嗎?是不是過分強調課堂紀律?教學的平等原則貫徹了嗎?教學中的教育正義得到聲張了嗎?師生關系的前設是基于對對象的認同,還是基于利用?師生上下相孚是基于我們的才德稱位,還是基于我們的權威權力?我們對自己的人際效益能夠正確評價嗎?能不能得到學生的認可呢?如此等等。
教師們要在課堂教學實踐中不斷反思,還要學會甄別各類信息,時刻保持教學警醒。例如,教師要認識到,課堂教學中師生關系的和諧可能是假象,學生在某些問題上與教師保持一致的真正目的可能是緣由利害關系,這可能帶來師生關系的暫時穩定,卻只會在和諧的表面下掩蓋種種危機。另外,從學生的角度來看,學生可能是因為種種利害關系而聽話,他們只知道“聽老師的話,按老師的指示辦事”是爭取自己利益的保證,而不論這些“指示”的正確與否,所以從不對教師們的所作所為予以質疑、反思、修正。如果那樣,他們可能認為對教師構成侵犯,破壞了他們之間關系的平衡。所以,教師在處理課堂中的師生關系時,必須重視批判與反思,沒有形成批判與反思的慣習,教師是不可能取得良好的人際關系的。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唯批判主義容易造成的課堂教學師生關系的虛無主義傾向,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正如根德林(G.Gendlin)所說:“我們不再需要僅僅用否定的方式講話”,“應終結要么是確定的基礎、要么什么也不是的抉擇”。[5]“批判一切”,“質疑一切”,認為課堂教學中師生關系什么都不是,藉以逃避責任,為種種師生關系“不作為”尋找借口,這只能是消解課堂、消解關系的絕對否定論,是我們在課堂中應該力避的。
四、和諧:整合論的師生關系
與上述三種哲學觀點不同,整合論的師生關系哲學追求的是“中庸之道”,“統籌兼顧”,“恰如其分”。當下,哲學家們在論述當今哲學走向時堅持“多重真理的復合”,他們認為背景的多樣性避免了非此即彼的選擇,應當容忍、甚至提倡各種不同的道路與模式的共同發展,相互溝通與借鑒。吉登斯(A.Giddens)在談到社會學發展趨勢時說,伴隨著社會學爭論而來的是將出現新的理論綜合,一個允許各種觀點和生活方式共存的社會,其社會學以及其它社會科學在本質上也必將是多樣化的。[6]傅偉勛提出“整全的多重遠近觀”,這與“多重真理的復合”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認為研究者應站在“中道”立場,從各種高低不同的角度設法如實知見諸法實相,盡量避免任何偏約化的過失。[7]如此看來,在課堂教學中,師生關系哲學的合理選擇應是兼容各種不同的取徑和視角,使之互補和融通,以便涵蓋豐富多樣的層面和向度。
提倡實在論的師生關系,是因為它基于理性與邏輯,使課堂教學中的人際發展更為有效,反對唯科學主義,是因為它將師生關系異化為物的利害關系;提倡現象學的師生關系,是因為它富有人情味,彰顯人的自由、平等與價值,反對唯現象學主義,是因為它將我們引向關系相對論的誤區;提倡批判主義關系論,是因為它讓我們不斷反思與批評,保持清醒的頭腦,不會迷失方向,反對唯批判主義,是因為它將帶來虛無主義的師生關系論。而整合論的師生關系力求構建整合實在、理解、批判于一體的關系哲學,這種關系的知識絕不像實在主義所宣稱的那樣僅僅是反映、描述性或技術性的,而且也不僅僅是滲透和嵌入在人身體之中的建構性的知識,當然也不僅僅是重視反思的純粹批判性知識。而是三位一體,既注重處理課堂教學中師生關系的科學、邏輯、技術、策略等實在的因素,人的意志、情感、價值等主體性、能動性因素,還注重批評、自我批評與反思等因素。
布迪厄指出,根據場域進行思考就是從關系的角度進行思考。人是復雜的關系有機體,處于復雜的關系場域之中。教師在處理課堂教學中的師生關系時,要認識到隱身于各種師生關系現象背后的玄機,絕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既要宏觀統籌,全面分析,又要細致入微,個別對待。以整全的觀點來構建課堂和諧的師生關系。堅持師生關系整合論,就是要堅持教學效益與人際和諧的整合,促使課堂教學又好又快發展,實現教師主導與學生主體的統一,即講原則,按章辦事,嚴格制度管理,又富人情味,心系學生生活,關心學生成長,又不斷自我反思與不斷提升。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要講科學、講規律、講原則,構建合理的師生關系;講理解、講尊重與講平等,構建合情的師生關系;講反思、講批判與講發展,做到合法的師生關系。
總之,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與學生之間應趨向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8]注重課堂生態和諧,建立整合的師生關系觀念,實現由異化的物的關系向和諧的人的關系的本真回歸,這既是提高課堂教學效益的要求,又是我們創建和諧課堂的共同愿景。
[1][德]胡塞爾.張慶熊譯.歐洲科學的危機和超驗現象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6.
[2][德]布貝爾.陳維剛譯.我與你[M].上海:三聯書店,1986.51.
[3][德]康德.韋卓民譯.純粹理性批判[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5.664.
[4][德]馬爾庫塞.程志民譯.理性與革命-黑格爾和社會理論的興起[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321.362.
[5]劉放桐.現代西方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43.
[6][美]吉登斯.文軍等譯.社會理論與現代社會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31.
[7]傅偉勛.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M].上海:三聯書店,1989.19.
[8]費孝通.學術自述與反思[M].上海:三聯書店,1996.142.
劉 建/南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教育管理學與教師教育研究
(責任編輯:劉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