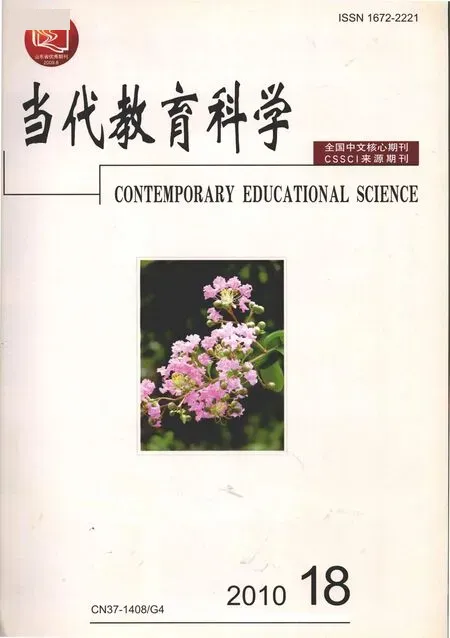臺灣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基本特色及走向
● 鄭 芳
臺灣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基本特色及走向
● 鄭 芳
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臺灣基礎教育課程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經歷了從改造、移植,再到創新的漸次發展歷程。以臺灣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為主要線索,分析了臺灣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基本歷程、特點及未來走向,從中總結經驗教訓,以資借鑒。
臺灣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歷程;啟示
我國臺灣地區基礎教育課程發展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分界線,戰前的日據時期實行日本課程,戰后在沿用大陸課程的基礎上,移植美國的課程模式,再根據不同時期社會發展的需要對課程進行總體改革,綜觀臺灣基礎教育課程的歷次改革及其社會背景,可以說臺灣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都是為了適應經濟發展需要而進行的,體現了不斷適應經濟發展、不斷調整規范體系、不斷融合中西文化、不斷調整價值取向的發展態勢及多元發展的時代特點。
一、臺灣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基本特色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幾十年來臺灣根據不同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對基礎教育課程進行了6次總體改革,其中小學6次,初中9次,高中8次。[1]以此為主要線索和重要標志,綜觀臺灣基礎教育課程的歷次改革及其經濟社會背景,從中大致看出臺灣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基本特色。
突出學科中心的課程改造。1953年,在開始實施第一個“四年經建計劃”時,臺灣將補習教育納入了正規教育體系。[2]50年代后期,隨著勞動密集型的進口替代工業的迅速發展,為適應加強工業的實際需要,臺灣于1955年對中學課程進行修訂,在減少課時計劃、強化政治教育的同時,突出了學科及專業教學。1962年2月,為了適應經濟結構從“農業為主”向“工業為主”的調整,臺灣召開了首次教育大會,研討配合經濟建設的教育方案和教育發展規劃,隨后開始實施第三次全面的中小學課程改革,一是為適應普及小學階段義務教育的要求,首次劃分初中與高中課程;二是強化道德與政治教育,把軍訓納入中學課程體系;三是強調職業技術教育,強化應用與技術學科教學。[3]
注重學科滲透。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后期,隨著部分重點科技產業的發展, 臺灣對教育在經濟發展中重要地位的認識日益加深,將教育作為衡量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的重要指標,并將“國民教育”作為“百年大計”。基礎教育則以強化“國民教育”為重點,并以中等教育為主,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新政策,實施中學課程改革。1979年,臺灣出臺了《國民教育法》,并進一步健全教育改革的領導機構。由“國科會”和“教育部”分別負責科學教育的基礎研究和推廣實施,在“教育部”成立“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加強和協調中小學的科學教育工作,成立“科技顧問室”配合“中教司”承擔教育改革的領導職能。之后又制定了《強迫入學條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將“九年國民教育”從法律上固定下來。同時,開始實施《改進“國民教育”六年計劃》,要求各級“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共同促進“國民教育”的發展。1983年和1985年先后兩次修訂頒布 “中學課程標準”,多次實施課程改革。1988年12月,為應對社會病態加劇對教育的嚴重影響,臺灣召開了第三次教育大會,著力加強中小學生的生活與道德教育,以“培養健全之國民”;改革教育制度,實現學制彈性化;充實教育經費,改善教育環境;提高師資素質,促進教育正常發展,并對課程體系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課程內容上,強調把公民教育滲透到各學科教學之中,注重各學科之間的相互滲透,促進學科教學與實際應用的聯系,要求加強科際課程的教學合作。在課程結構上,大力推進彈性課程,增設了選修課程,加強中小學課程之間的銜接,注重發展學生的能力。在課程實施上,為保證課程理念和改革思路的貫徹落實,將“教學通則”改為“實施通則”,從課程目標設置、結構以及評價等方面提出具體的要求。[4]
推進課程整合。2001年,頒布實施了新的《國民教育九年一貫制課程暫行綱要》,從真正意義上推進課程的整合。同年12月,臺灣“教育部”專門召開“教改檢討及改進會”,督促和落實教改計劃,提出教改推進時間表,繼續推動教育改革。一是按照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三維框架,整合以往以學科為中心的課程體系,把所有課程劃分為語文、健康與體能、社會、藝術與人文素養,數學、自然與科技及綜合活動等七大學習領域,強調中小學課程設置的銜接;二是擬訂十種基本能力作為課程發展目標,以能力本位取代知識本位,促進課程、教學與評價的有機整合,著重培養學生具備人文關懷,民主素養,統整能力、鄉土與國際意識,并有助于終身學習等方面的健全國民;三是改革課程標準為課程綱要,注重學校的彈性課程,突出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減輕學生的課業負擔。[5]另外,還實行了“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實施計劃”,對中等職業學校提出了改革要求。推動建立圖書館、博物館、音樂廳等縣市文化中心,繼續發展社會教育。
二、臺灣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未來走向
《國民教育九年一貫制課程暫行綱要》的頒布實施,反映著臺灣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基本趨勢,從可分析出臺灣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特征及未來走向。
課程目標的人本走向。在臺灣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發展過程中,始終伴隨著臺灣當局、社會團體以及人民大眾之間的利益調和,并根據經濟發展所產生的社會結構的演變,逐漸從強調政治意識、國家本位走向社會主導、以人為本,呈現出由傳統特征向時代趨向發展的特點。在課程改革上不斷彰顯社會主導和人本取向的特征。在課程目標上,經歷了從突出意識形態、注重政治教育,到強化社會主導、注重經社教育,再到強調以人為本、突出“五育并重”的均衡發展。
課程理念的中西融合。近百年來,臺灣獨特的發展道路使其一直處于文化沖突與交融的前沿地帶。國民黨政權遷臺后,為維護政局穩定,把中華傳統文化上升到意識形態,致使中華文化的強制性蛻變。而對于西方文化,不僅是“文化適應”的問題,更是“政治安全”的問題,所以臺灣當局對其采取了一定的抑制政策。經過持續的社會轉型與文化交融,特別是隨著持續工業化的進程,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文化對臺灣的影響不斷加深,臺灣試圖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保持中西文化之間的平衡,逐步形成了一種與大陸文化血脈相連,同時又具有地域特色的多元開放的文化形態。臺灣基礎教育課程的演進歷程始終在中西文化的沖撞之中進行,既具有較強的西方色彩,又都浸潤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臺灣光復初期,所沿用的中國大陸早期課程實際上就是移植西方課程的產物,具有中西文化結合的特點。
課程管理與評價的多元化趨向。經過歷次的改革,基礎教育課程管理開始呈現出“一統特征”和“多元趨向”消長并行的發展格局。課程管理改變了由最高教育主管部門設置統一課程綱要或教學計劃進行集中管理和推進的辦法,重新整合管理機制,逐步形成分層管理的模式,實行“國家”、地方和學校的三級課程管理。由臺灣“教育部”編制綱要,統領課程改革;地方教育部門負責實施,開發地方課程,培訓師資;學校具體落實,開發校本課程,預留更多的課程空白,倡導多開選修課,甚至倡導把課程自主權下放到教師。在課程評價上,臺灣歷來重視資格考試、選拔考試和學業考試,并將其作為學業評價和課程管理的重要方式,建立起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統一考試制度。小學考試形式很多,主要以考查學生的學業成績為主。中學每學期考查3次,還有日常表現四項綜合評定,以及大學入學聯考。20世紀80年代,臺灣省及臺北市分別成立命題改進專案小組及入學方式改進小組,分別從命題技術與入學考試方式上改進高中階段的入學考試;并由臺灣各大學校院聯合設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長期研究改進大學入學考試制度,提出具體可行的改革方案。90年代以后,臺灣掀起改革統一考試制度的風潮,力圖轉變唯分數的教育弊端;1995年,臺北市就開始實施高中免試入學。近年來,臺灣極力改革考試、淡化統一考試的功能,通過實施多元化評價方式,倡導免試入學、推薦甄選、預修甄選、改良式聯考等方式,以期促進創新型人才的成長。[6]2002年,臺灣廢除了實施近半個世紀的大學聯考制度,把聯考一試定終身的單一篩選模式改為推薦甄選、申請入學和考試分發的多種渠道入學模式,全面實行“多元入學方案”。
三、臺灣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啟示
經濟社會的轉型是臺灣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原動力。臺灣基礎教育之所以獲得較快發展,重要的原因就是社會和經濟的持續發展對教育不斷提出新的要求;而臺灣基礎教育課程的歷次政策調整和改革都是為了適應經濟發展需要而進行。臺灣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過程中所積累的豐富經驗,有許多值得借鑒的成功做法。
首先, 淡化對知識的注意力,將傳統的知識教育轉變為人的基本素質教育,注意培養學生的文化素養和身心發展。例如,在“人與自我”的教育活動中,要求促進個體身心的發展,培養學生了解自我、發展潛能、終身學習、審美及創作的能力;在“人與社會”的教育活動中,要增進社會與文化的結合,培養學生尊重他人、關懷社會、促進文化學習和國際了解的能力;在“人與自然”教育活動中,要求認識自然與環境的互動,培養學生主動探索和研究的精神,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此外,臺灣中小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頗具特色,學校的校徽、校歌、校史、雕塑、匾牌、標語等,大多內容精辟,含義深刻,積極向上。學校一般都重視國文課,不少學校還開設書法、古詩詞鑒賞等課程,回歸中國傳統文化,培養學生對民族和中華文化的情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臺灣的很多私立學校是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宗旨的一貫制學校,從幼兒園到高中整體安排傳統文化課程,并以此為特色形成了獨特的辦學競爭力。
其次,注重從人的發展需要和社會的需要出發整合課程門類。它要求每一階段的學校(小學初中、高中)或每一年級的教育課程一貫性的縱的配合,避免不必要的重復或銜接上的不良,也要求同一階段同年級各科課程內容的橫的聯系,使課程的架構周延完整,對內容難易多寡相稱合理,對學生的整體學習能提供更有效的幫助。例如,為培養學生應具備的十項基本能力,其教育課程按個體發展、社會文化及自然環境三個方面,提供語文、健康與體能、社會、藝術與人文素養、數學、自然與科技及綜合活動等七大學習領域。[7]同時,隨著文理科相互滲透日益深入,邊緣學科的產生和發展,也強調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整合,注重通識教育,使學生具備文理科知識學習的基本能力;此外,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學科課程與活動課程,顯性課程與隱性課程(或潛在課程)也在整合之列,提倡兩者要相互兼顧,不能偏廢。
最后,強調發揮學生學習的自主權和主動性,課程的彈性化就是為提高學生自主性而提出來的,它主張課程的實施要留有伸縮余地,使教師和學生有自主教學的機會。例如,在語文、數學、健康與體育、社會、自然與科技、藝術與人文和綜合活動七個領域中,語文占20-30%,其余各占10-15%,各校在此范圍內彈性安排。在課程計劃中,分兩類教學節數,基本教學節數占80%,彈性教學節數占20%,在授完最低教學節數外,學校和班級可實行“彈性教學節數”,開展全校性活動或教學輔導。此外,一至六年級選修節數占10-20%,七至九年級選修節數占20-30%,[8]在此原則下,學生能夠自主挑選或參與挑選選修科目和學習內容,選擇學習方法,評價或參與評價學習過程與學習結果。
[1][3][4][6]馮增俊.中國臺灣中小學課程世紀變革探析[J].教育科學,2005(4).
[2]莊明水等.臺灣教育簡史[M].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234-239.
[5]邱兆偉、張雅雯.試辦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之評估:課程模式與實施結果[J].教育學刊(臺灣),2001(17).
[7]九年一貫課程:http://www.meps.tp.edu.tw/www/study/frame2.htm.
[8]李春芳.臺灣中小學課程改革與學生創造能力培養之探究[A].載馮增俊,李忠俊.教育創新與建構中國現代教育體系[C].四川文藝出版社,2001.
鄭 芳/福建省教育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責任編輯:張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