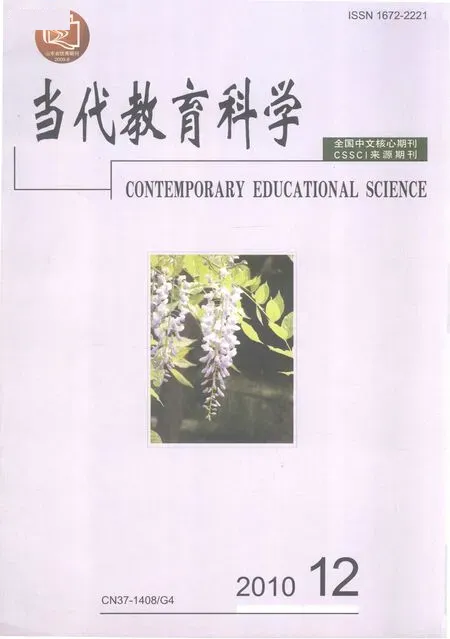戶外教育課程研究
●朱偉強
戶外教育課程研究
●朱偉強
旨在打破教室束縛,拓展學生學習空間的綜合實踐活動課程,鼓勵學生走出學校,走向社會,通過創(chuàng)設真實、開放的學習環(huán)境,來豐富學生的學習經(jīng)歷與生活體驗。這樣的課程如何開發(fā)?本文提出戶外教育課程模式,主要圍繞戶外教育的意涵、戶外教育課程的理論基礎、開發(fā)原則和教學實施展開討論,為教師開發(fā)戶外教育課程提供建議。
戶外教育;課程模式;實施建議
新課程設置了綜合實踐活動課程,旨在打破教室、學校的束縛,拓展學生的學習空間,豐富學生的學習經(jīng)歷與生活體驗,實現(xiàn)學生整體、和諧的發(fā)展。研究性學習活動、社會實踐、校外考察、生存鍛煉等,這些都屬于戶外教育范疇,其課程內(nèi)容以廣泛的社會資源為背景,強調(diào)與社區(qū)、社會、自然界多層面、多維度的接觸與聯(lián)系,著意于構建一個更為真實、開放的學習環(huán)境,以此來保持學生獨立、持續(xù)的探究興趣,獲得社會實踐的體驗,發(fā)展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學會分享、尊重與合作,培養(yǎng)關注自然與社會的責任心和使命感。那么,何謂戶外教育?其建基的理論基礎是什么?如何開發(fā)這樣的課程,來達成過程與方法、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這些維度上的課程目標?本文就這些問題展開討論。
一、戶外教育的意涵
戶外是一個動態(tài)的概念,相對于室內(nèi),走出房間就是戶外;相對于校內(nèi),走出校門就是戶外;相對于城市,走出鋼筋水泥混合物組成的環(huán)境,走進自然就是戶外。
古人云:“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戶外教育是最根本的學習活動,學生得到的是最原始的體驗、感受與發(fā)現(xiàn)。孔子周游列國時,經(jīng)常與弟子就地取材進行對話,即具有今日戶外教育的精神。早在1950年之前,美國自然研究學會將學校露營發(fā)展為戶外教學,史密斯博士(Julian W.Smith)成功地推動戶外教育普及美國各地。美國戶外教育學者George Donaldson曾提出:“戶外教育就是戶外教學,包含有關戶外的教學以及為戶外而教學。”[1]美國國家教育協(xié)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定義戶外教育是所有學校科目、知識與技能的結合,由教師運用環(huán)境資源去幫助學生了解各學科、環(huán)境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協(xié)助藝術、科學、社會研究的教學活動。[2]戶外教育之父L.B.Sharp則說:“戶外教育是指不論任何年級、任何學科課程,若能在戶外獲得最佳學習效果,便在戶外進行的教學活動。”[3]
學生的發(fā)展是個體與教育環(huán)境相互作用的結果。但一個學生的健康成長,僅有良好的學校和家庭教育環(huán)境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計劃、有目的地引導學生去接觸自然和社會。在接觸自然和社會的過程中積累經(jīng)驗,逐步豐富自己的認知,認識自我、認識自然、認識社會,形成健全的人格。在這方面,許多教育家亦有明確的論述。蘇格拉底認為受教育是要發(fā)展每個人的自我并實現(xiàn)自我,換言之,即發(fā)展受教育者的“主體性”。夸美紐斯認為兒童所要學習的事情,實物經(jīng)驗應先于書籍閱讀。盧梭則認為教導孩子最重要的內(nèi)容應該是體能訓練,為了滿足兒童的好奇心,激發(fā)其潛能,從經(jīng)驗中得到的會比間接學自書本的多得多。裴斯泰洛齊亦主張善用直接、第一手經(jīng)驗和實物學習的教育方法,鼓勵老師帶著學生走出教室,走進自然和社會。我國著名教育家陳鶴琴主張“活教育”,把大自然和大社會作為出發(fā)點,讓學生直接向自然和社會學習。他指出,大自然、大社會是知識的主要源泉,“從書本上能吸收的知識是死的、間接的,而從大自然與大社會獲得的知識是活的、直接的。不言而喻,在各個方面,后者大大優(yōu)于前者。”陶行知主張“社會即學校”,強調(diào)教、學、做合一的思想,非常重視社會生活對兒童潛移默化的影響,讓兒童參與社會生活,有利于他們更快地從幼稚走向成熟。
戶外教育有別于其它課程的一個特色是它的教學方式。基于杜威一個多世紀前的信念——所有真正的教育都源于經(jīng)驗,很多發(fā)生在戶外環(huán)境中的學習都是經(jīng)驗性的,其中的活動(學習中“做”的方面)支持更多正式的教學,這樣的課程和教學必然是以學生為中心的、自主的、探究的、合作的。戶外教育的另一個特色是它在培養(yǎng)學生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方面的特殊價值。自然、真實的學習環(huán)境為鑒別和解決真實的生活問題(如背后說壞話、不尊重同學、逃避工作、給所做事情找借口、抱怨別人等)提供了有價值的背景。同樣,把學生帶入戶外環(huán)境也提供了大量的機會,鼓勵學生改變他們對待環(huán)境的態(tài)度和行為。學生在戶外活動中必須特別注意,減小他們對脆弱的動植物生長環(huán)境的影響;教師也可以幫助學生懂得對自然環(huán)境的欣賞和關愛,樹立自身行為會影響他人和環(huán)境的意識,同時增強他們對這種意識的敏感性。
盡管如此,戶外教育中的戶外活動發(fā)生在自然的環(huán)境中,這些環(huán)境中幾乎沒有人為的控制,有時會有參與者無法控制的危險存在。這些危險可能包括復雜的社會環(huán)境、繁忙的交通、不利的天氣、野生動物、蚊蟲叮咬、污染的飲用水以及崎嶇或潮濕的地理環(huán)境。因此,教師和學生必須理解在自然環(huán)境中可能存在的危險,并且他們必須練習并學會做出正確的判斷以使這些危害最小化。
二、戶外教育課程的理論基礎
戶外教育課程既是綜合課程,也是經(jīng)驗課程。作為課程的一種模式,其深厚的理論基礎除了經(jīng)驗教育理論和存在心理學理論以外[4],主要還有人本主義的情意教育論、超越課程論以及生態(tài)后現(xiàn)代主義的整體教育論。[5]
(一)情意教育論
人不僅是思維的存在,同時也是情感的存在。從人本主義教育看,脫離了感情的智慧是空虛的,無意義的。因此,人本主義情意教育強調(diào),必須充分注意防止兒童在學習中的身體活動、感知活動、語言活動的強制性抑制。人是作為一個整體的人格而成長的。教育既然是把人作為整體的人的存在,那么,它所追求的就是學生的全面發(fā)展。為了全人格的發(fā)展,認知學習必須同情意、情感相結合,心智發(fā)展必須同情緒發(fā)展相結合。人本主義課程的情意教育論,目的是要把人培養(yǎng)成“自由的個人”,或者說是達到“自我實現(xiàn)”、“個人的實現(xiàn)”。這個自由的個人的實質(zhì)意味著人格的其他重要部分(情意、情緒、感情)的發(fā)展成長,同卓越的智力同等重要。這是情意與認知、感情與知性、情緒與行為統(tǒng)整的“個人”或“整體的學生”。這種人格的中心課題是“情意發(fā)展”(情緒、感情、態(tài)度、價值)和“認知發(fā)展”(理智、知識、理解)的統(tǒng)一。惟有借助這種統(tǒng)一,整體的人格成長才有可能。
(二)超越課程論
人本主義教育的目標著眼于人的全部能力的發(fā)展。福謝依(A.W.Foshay)列舉了人的全部能力領域:理智、情緒、社會、身體、審美、靈性。為了全面發(fā)展上述六個方面的能力,他提出了課程I(正規(guī)的“學術性課程”及有計劃的課外活動)、課程Ⅱ(突出“參與集體與人際關系”的“社會實驗課程”)、課程Ⅲ(旨在喚起兒童對于人生意義的探求的“自我覺醒和自我發(fā)展的課程”)。學校課程要使“生物的人培養(yǎng)成歷史的、社會的存在——自我實現(xiàn)的人”,就得考慮由知識課程、情意課程及體驗課程組成。“知識課程”是指理解和掌握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的學術(科學)知識的課程。“情意課程”是指健康、倫理及游戲這一類旨在發(fā)展非認知領域的能力的課程。“體驗課程”,是借助知識課程與情意課程的統(tǒng)整,即認知與情意的統(tǒng)整,旨在實現(xiàn)整體人格的課程。[6]
體驗課程之“體驗”是一種“超越經(jīng)驗”。道德價值和精神價值即是“體驗”或“超越經(jīng)驗”的有機構成。“超越”(transcendence),亦可稱為“超驗”、“先驗”,是指“對任何給定狀態(tài)或現(xiàn)實存在的無限超出的經(jīng)驗”。[7]“超越”是人的“精神存在”或“意識存在”的內(nèi)在屬性。“超越”是人的本質(zhì)的深層顯現(xiàn),是人之為人的根本。費尼克斯(P.H.Phenix)說,“人類的意識是植根于超越的”。而智力的功能則在于以有限的范疇,構筑經(jīng)驗的合理秩序。然而,靈性是不會滿足于這種智力的有限世界的解釋與結論的。它覺悟到經(jīng)驗的整合構造的有限性,要揭示其限度。靈性,只要是人類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那么,人總是面臨著不可回避的課題——企求無限的“超越”的。這便是“超越課程論”。
(三)整體教育論
“整體主義”源于斯馬茨(J.C.Smuys)的著作《整體主義與進化》,整體遠大于部分之和。自然、社會、個人是有機統(tǒng)一的完整的連續(xù)體。整體主義(holism)認為部分與部分之間、部分與整體之間擁有內(nèi)在聯(lián)系。具體說來,自然、社會、個人是具有內(nèi)在聯(lián)系的整體,任何一部分如若從整體中剝離出來,其本真將不復存在。因此,只有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其自身之有機關系(動態(tài)生成關系)的背景中探究人的主體性,才能把握主體性的實質(zhì),進而返歸個人主體的本真狀態(tài)。
基于這樣的哲學思考,整體教育力圖根治“病態(tài)的教育”,促進個人接觸生命的多樣領域,通過體驗,充實、形成個人的生命,以培養(yǎng)學生形成一種實感——周圍的人們、地球、個人自身,無時無刻不在相互關聯(lián)之中的實感;并且通過這種實感,培養(yǎng)一種責任感——對自己、對他人以及對地球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不是外加的沉重的包袱,而是自身從這種關聯(lián)的感受之中獲得力量,并且由此自然地升騰起來的。[8]在整體教育論看來,人類這一存在不僅是追求知識與技術,而且是尋求意義的存在。人類必須在健全地成長和成熟之中尋求人生的真諦。恐怕惟有充分領悟人生真諦的人,才能創(chuàng)造出健全的社會。整體主義教育就是旨在哺育和發(fā)展擁有人類精神的最重要的憧憬。[9]
教育作為完善人性的活動,是一種復雜性現(xiàn)象,具有非線性、混沌、突現(xiàn)、非還原性等基本屬性。整體教育思潮對學校教育進行的“復雜性”探討,亦即突出非線性思維、混沌思維、突現(xiàn)思維和非還原性思維的教育研究,正是克服原子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局限性,洞察教育的真諦所需要的。整體教育思潮是生態(tài)后現(xiàn)代主義的典型代表,是對當代人文主義教育的超越,它突出“以人為本”,突出“人文關懷”,突出“人文”、“科學”與“創(chuàng)造”的和諧統(tǒng)一。
三、戶外教育課程的開發(fā)建議
體現(xiàn)生態(tài)后現(xiàn)代主義思想的整體教育論是戶外教育課程的理論基礎,它呈現(xiàn)了對未來教育睿智的憧憬,戶外教育課程的開發(fā)可以作為這一課程范式的典范。整體教育強調(diào)基礎教育的課程必須促進學生的情感、體質(zhì)、審美、精神、智力的和諧發(fā)展。在社會層面,要求從“生產(chǎn)率、勞動”中心的社會轉向“有意義人生”中心的社會,強調(diào)自我實現(xiàn)需求的滿足和有別于他人的差異;在學習層面,從“目標達成型”學習轉向“目標探究型”學習,這種學習是“自我探究”,它不是達到給定目標的學習,而是作為自己探究目標的過程的學習。基于此,米勒(J.P.Miller)在《整體教育》一書中提出“整體課程”編制的三原則:“關聯(lián)”、“包容”、“和諧”。[10]因此,筆者認為,整體主義教育所倡導的學習是作為“自我之旅”的自我學習,是真實的學習,是對未知的探索。學生的教育經(jīng)驗應當被組織在有目的的探究、發(fā)現(xiàn)和行動的探索之中,被設計成用以促進自我發(fā)現(xiàn)和知識的獲得,多樣性、包容性、與自然世界的關聯(lián)和學習的責任是用于設計這種課程的若干原則,而這樣的原則在戶外教育課程中能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
雖然可能不像其它課程模式那么普遍,但戶外教育課程模式可以越來越多地進入城市、鄉(xiāng)村、山區(qū)的學校課程。相對于審慎地選擇戶外教育活動并整合進整個學校整體課程方案而言,一個純粹由戶外教育課程模式構成的學校課程方案是不多見的。因為戶外教育活動受到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的重要影響,自然地理環(huán)境和社會資源是戶外教育重要的課程資源。不同的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可以形成不同內(nèi)容的戶外教育課程方案。在調(diào)查哪些戶外教育活動最能適合學校所處的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能滿足學生的需要之后,教師可把一至幾項戶外教育活動整合進現(xiàn)有的學校課程方案中。基于和新課程三維課程目標關聯(lián)程度的思考,設計戶外教育課程可以從以下問題開始:
——在我們的課程中什么樣的預期目標是合理的、可達成的?這些戶外教育活動能達成那些預期目標嗎?
——我們需要什么資源(如預算;設備和物質(zhì)條件;交通;保險;空間和活動場所)來啟動并維持這一活動?
——我們需要什么新技能?該如何發(fā)展這些技能(如果自己不會,如何獲得具備這些技能的人的幫助)?
——為了完成我們的評價責任,為我們提供教學方向,需要什么樣的評價標準和策略?
通過檢驗并回答了以上的問題,就整體學校課程方案中的戶外教育課程成分而言,可以設計成幾個課時的單項戶外教育活動小單元,也可以設計成由不同主題活動構成的為期18周的大單元戶外教育活動計劃。
四、開展戶外教育活動需要考慮的因素
戶外教育活動環(huán)境中,交通、天氣、地形、經(jīng)費、師生比例、團隊構成等因素要求戶外活動有詳細的計劃、交流和團隊合作。教師和學生在戶外環(huán)境中必須是安全的、能勝任的、有責任的參與者。無效的判斷、糟糕的計劃、不充分的專業(yè)技能和急救技能,都會使戶外教育活動變成冒險。
對于開發(fā)戶外教育課程的教師來說,一些重要的教學因素必須反復思考。依照戶外教育經(jīng)驗的程度和背景,除了具有通常所要求的教學技能之外,教師還需要額外的訓練和專門的知識,要有豐富的經(jīng)驗和教學管理能力,還要有堅定的自信和勇敢的冒險精神。考慮以下這些技能和能力,有助于教師確保戶外教育課程的教學質(zhì)量和課程目標的達成。
●野外生活技能和能力(如打包;選擇營地;生火和照看爐火;煮烤食物;找路;改善衛(wèi)生等);
●安全技能和能力(如檢修設備;水處理;天氣說明;野外急救與求救;危機管理和突發(fā)事件處理程序;提防動物侵襲等);
●環(huán)境類技能和能力(如減小途中對環(huán)境的影響;行進規(guī)則;露營不留垃圾等);
●組織類技能和能力(如設計活動方案;協(xié)商和取得許可;安排交通和設備;計劃飲食和營養(yǎng)等);
●教學類技能和能力(如開發(fā)教學的進程;任務分析;根據(jù)學生的特點安排教學策略;選擇教學場所和教學方式,如示范、講座、討論、短劇、可視輔助手段、日記;認清和有效地利用“可教育時機”等);
●指導、促進的技能和能力(如培養(yǎng)有效的團隊動力;解決爭端;培養(yǎng)個人信任和團隊合作;提供個人和集體決策的機會;進行有效的活動前指導和活動后反思等);
●領導的技能和能力(如決策分享;建立清晰的決策程序;利用一種民主的或獨裁的方式去適應一種情境或團隊的發(fā)展階段;提供運用正確判斷的機會等);
●環(huán)境倫理(如開發(fā)和利用適當?shù)膽敉饣顒觽惱順藴剩ū3忠粋€干凈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環(huán)境;喚起公眾關注土地和其他生命形式;更多依靠我們的行動和節(jié)約的能力,而不是花費、消耗的能力等)。
除了這些能力,一位教師擁有生態(tài)學、物種學、星象學和有用的天文學、氣象學、地質(zhì)學方面的知識也能夠極大地提高學生戶外活動的經(jīng)驗。
戶外教育以其獨特的魅力對學生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能滿足學生超越書本知識和傳統(tǒng)的教育環(huán)境而提供真實的情境學習。戶外教育課程可以給許多喜歡刺激、挑戰(zhàn)、有時是一定程度冒險(真實的和所理解的)的學生帶來教育上的巨大意義。認識自然、認識自我、認識社會,以及挑戰(zhàn)自然、挑戰(zhàn)自我、挑戰(zhàn)極限需要特殊的技能、知識、個人責任、社會交往能力和理智的冒險精神,而這些可能是傳統(tǒng)的學校教育環(huán)境中所沒有的。雖然很多戶外教育課程對教師的專業(yè)技能和教育經(jīng)驗要求較高,但這不是一個基于標準的課程忽視戶外教育活動的理由,課程變革給教師提供了專業(yè)發(fā)展的機會,更何況有些戶外教育活動既不要求專門的訓練,也不要求大量的資金和器材,只要周密的策劃和組織,新課程提出的三維課程目標都能通過學生積極地參與戶外教育活動來達成。
[1]李昆山.國民小學戶外教學理論與實務初探[J].環(huán)境教育.1996 (29):62-69.
[2]王佩蓮.知性兼具休閑的自然體驗活動[J].教師天地.1998(93):28-34.
[3]周儒.戶外教育真義[J].環(huán)境教育季刊.1994(20):52-63.
[4]張華.經(jīng)驗課程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5][8][9][10]鐘啟泉,現(xiàn)代課程論(新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58-222.
[6]信州大學學科教育研究會.學科教育學的構想(上卷)[M].1986 (日文版).121.
[7]Philip H.Phenix.Transcendence and the Curriculum[J].Teachers College Record.December 1971(73-2):272.
(責任編輯:張斌)
book=0,ebook=1
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課題《課程標準的分解和轉化——設計基于標準的教學》(09YJC880032)的研究成果之一;2008年度上海市教委科研創(chuàng)新項目《基于標準的課程設計研究》(08ZS28)的研究成果之一。
朱偉強/華東師范大學體育與健康學院副教授,教育學博士,研究方向:課程與教學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