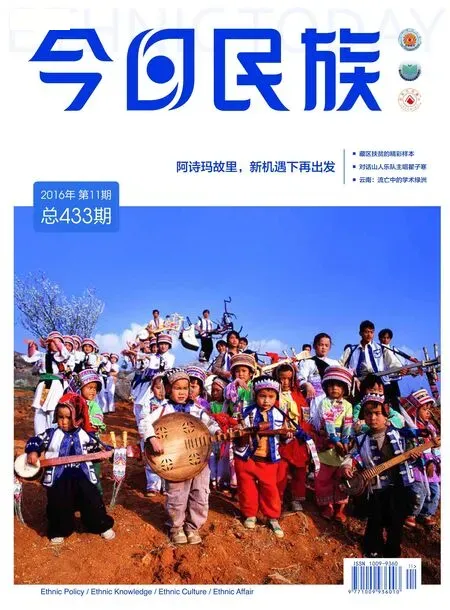省內信息
省內信息
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珍品暨保護成果展在云南舉辦11月1日,“民族遺珍 書香中國——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珍品暨保護成果展”全國巡展活動(云南站)在云南民族博物館開幕。國家民委副主任李昌平宣布展覽開幕。云南省副省長高峰出席開幕式并致辭。據悉,云南站是全國巡展的第3站,將持續至11月30日。展品包括書籍、銘刻、文書、講唱等四大類古籍,涵蓋東巴文、彝文、藏文、西夏文、毛南文、察合臺文等17種少數民族文種。來自全國20多個省區市的民族宗教事務部門、民族古籍機構、民族宗教研究機構的200余人參加開幕式并參觀展覽。
(省民族宗教委文宣處)
三峽集團幫扶云南省怒族普米族景頗族脫貧攻堅推進會在昆舉行 10月19日,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幫扶云南省怒族、普米族、景頗族脫貧攻堅推進會在昆明舉行。三峽集團董事長盧純、云南省委副書記鐘勉出席會議并講話。三峽集團移民工作局,省扶貧辦和怒江州等4州市分別匯報了幫扶工作推進及落實情況,三峽集團捐贈了支持怒族、普米族、景頗族脫貧攻堅資金20億元。
(云南網)
國家民委副主任李昌平赴云南調研民族文化工作10月31日至11月4日,國家民委副主任李昌平赴云南,就貫徹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加強少數民族文化保護與傳承工作進行調研。李昌平一行先后來到昆明市、普洱市和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參觀了云南民族博物館、西雙版納州民族博物館、少數民族文化展示園、少數民族古籍展、少數民族特色村寨。調研中,李昌平對近年來云南省民族文化工作取得的成績給予高度評價。國家民委文化宣傳司、輿情中心、云南省民族宗教委和普洱市、西雙版納州有關負責同志陪同調研。
(省民族宗教委文宣處)
云南省舉辦全國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互觀互檢10月10日至14日,由國家民委組織開展,云南省民族宗教委承辦的“全國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互觀互檢”在云南成功開展。創建活動圍繞昆明市、大理州和昆明鐵路局貫徹落實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精神,推進創建活動制度化、常態化,以及以“六進”為基礎,推進示范州(市)創建的經驗做法,相繼考察了石林縣圭山鎮糯黑民族特色村等11個示范創建點。來自內蒙古、黑龍江、四川等省區的相關領導和民委主任,以及我省部分州市縣民族工作部門負責同志40余人參加了此次活動。省民族宗教委副主任陸永耀主持總結座談會,國家民委監督檢查司副司長李鐘協講話,對云南的創建工作給予了高度肯定,并就如何做好“十三五”時期全國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作了總體部署。
(省民族宗教委督查處)
首屆全國民族檔案學研究會在云南召開 近日,首屆全國民族檔案學研討會在云南大學召開。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等30多個高校和研究機構的60多名學者參加會議。研討主題為“檔案與少數民族社會記憶”,主要圍繞“少數民族檔案學基礎理論”“少數民族檔案學學科體系建設”“少數民族檔案資源建設、保護與開發利用”等課題展開。省檔案局(館)負責人介紹了云南民族檔案保護的經驗。
(本刊訊)
中國民族學會2016年學術年會在雙江縣召開 11月6日至8日,由中國民族學會主辦,云南民族大學、滇西科技師范學院、雙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縣聯合承辦的中國民族學會2016年學術年會在雙江縣召開。會議以“一帶一路視野下民族文化國家”為主題,來自國內外近300名專家學者就新形勢下民族學界如何更好地配合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推動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展開學術交流。
(新華網)
黃毅調研中國巴利語系高級佛學院項目建設工作 11月8日,省委常委、省委統戰部部長黃毅到西雙版納州調研中國巴利語系高級佛學院規劃設計方案及項目進展情況并聽取匯報。州政協、州佛協等部門參加匯報會。黃毅對西雙版納州委、州政府和景洪市委、市政府前期所做的各項工作給予肯定,并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西雙版納州民宗局)
我省首屆伊斯蘭教經文學校文化活動周舉行 10月17日至21日,由省民族宗教委、省伊協主辦,大理州伊協、大理市伊協、南五里橋清真寺、南五里橋清真寺經文學校承辦的首屆云南省伊斯蘭教經文學校文化活動周在大理市舉行。來自昆明、文山、紅河、大理、昭通5個州市的8所伊斯蘭教經學院和經文學校代表隊約230人參加活動。省政協副主席、省伊斯蘭教協會會長馬開賢出席開幕式并講話。期間,舉辦了體育比賽、辯論賽和經文學校教學研討、文藝表演等。
(本刊訊)
清真寺管委會主任培訓班在大理舉行 10月16日至21日,省伊斯蘭教清真寺管委會主任培訓班在大理舉行。省政協副主席、省伊協會長馬開賢大阿訇出席開班儀式,并作伊斯蘭教中道思想的專題講座。省民族宗教委相關負責人出席開班儀式。培訓班安排了專題講座、現場教學、觀摩伊斯蘭教經文學校文化活動周等內容。全省約100所清真寺的管委會主任參加培訓。
(省民族宗教委宗教業務三處)
省民族宗教委傳達學習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 10月29日,省民族宗教委召開黨組擴大會議,傳達學習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和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精神,研究部署貫徹落實六中全會精神的初步意見及近期有關工作。會議強調,要以學習貫徹全會精神為契機,結合職責任務和工作安排,推動全年工作目標的圓滿完成;要按工作實際,精心謀劃好明年的工作目標,做到學習全會精神與推動工作兩不誤、兩促進。省民族宗教委黨組成員、副巡視員、機關各處室、委屬各單位主要負責人、駐委紀檢組副組長、離退休黨總支負責人參加會議。
(省民族宗教信息中心)
云南省2016年宗教院校科普骨干人才能力提升培訓班在大理州舉辦 近日,省民族宗教委和省科協聯合舉辦的2016年全省宗教院校科普骨干人才能力提升培訓班在大理州賓川縣開班。省民族宗教委教科處、省科協科普部相關負責人,省社科院專家等近40人出席開班儀式。培訓班采取專家講授、經驗交流、現場教學的綜合方式。
(大理州民宗委)
省民族宗教委做客“金色熱線” 10月20日,省民族宗教委黨組書記、主任李四明率隊做客“金色熱線”,就云南省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建設的進展如何、云南省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幫扶直過民族和人口較少民族的發展、云南省怎樣保護與傳承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等群眾關心、社會關切的問題做出解答、回應。
(本刊訊)
云南省2015至2016年學校民族團結教育征文評審會召開 11月3日,由省民族宗教委、省教育廳主辦,今日民族雜志社承辦的云南省2015—2016年學校民族團結教育征文評審會舉行。全體評委按照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評出了38篇優秀征文和11個優秀組織獎。其中,教師優秀作品12篇,學生優秀作品20篇,優秀通訊員作品6篇。據悉,本屆征文活動開展一年來,得到了全省各地、各學校領導和師生的積極響應,共收到師生投稿400余篇(幅)。
(本刊訊)
李四明到文山州調研沿邊三年行動計劃推進工作10月25日至27日,省民族宗教委主任李四明到文山州對沿邊三年行動計劃推進情況和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創建工作進行調研,副主任徐暢江、文山州副州長周家寶參加調研。李四明主任對文山州沿邊三年行動計劃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同時要求文山州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全面推進沿邊三年行動計劃落實,確保完成“五通、八有、三達到”的目標;要籌備好現場推進會;要謀劃好產業布局和發展,做好產村融合這篇文章。
(省民族宗教委經濟處)
《中國民族年鑒》云南部分(2016卷)編撰工作圓滿完成 《中國民族年鑒》云南部分(2016卷)歷時半年多時間,完成了征稿、組稿、審核、修改、校對、完善等工作,《年鑒》匯集了全省全年出臺的有關民族文件、各級民族工作部門的工作情況、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經濟社會各領域的發展情況、少數民族各項社會事業發展信息和統計資料。
(省民族宗教工作隊)
“千戶企業萬個崗位進藏區”就業援藏活動啟動11月9日,省人社廳“千戶企業萬個崗位進藏區”就業援藏活動啟動儀式在香格里拉市舉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湯濤出席啟動儀式,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崔茂虎和迪慶州委書記顧琨分別在啟動儀式上講話。當天,共有180家省內外有招聘用人意向的企事業單位、民營企業到現場招聘人才。共發放政策宣傳冊2000余份。
(迪慶州民宗委)
曲靖市伊斯蘭教協會組織開展“宗教慈善周”活動 10月28日,曲靖市伊斯蘭教協會在西門街清真寺組織城區穆斯林群眾開展了“宗教慈善活動周”捐贈儀式。曲靖市伊協駐會領導、協會機關工作人員、清真寺管事、阿訇等帶頭捐款,參加“集禮”的穆斯林群眾紛紛響應,共收到捐款近5000元,衣服600余件。
(曲靖市伊協)
玉溪市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惠及人口較少民族近日,玉溪市制定出臺《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實施辦法》,將少數民族人口低于1萬人的苗族、拉祜族、蒙古族和具有“直過區”特征的彝族山蘇支系、仆拉支系及哈尼族布孔支系聚居的284個村民小組、5萬農民確定為幫扶對象,切實解決他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
(玉溪市民宗局)
保山市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創建工作成效明顯 保山市自2013年啟動少數民族特色村寨保護與發展試點工作以來,共爭取民族專項資金2100萬元,整合各級各部門資金8000多萬元,因地制宜,從改善基礎設施,挖掘和保護民族傳統文化,培育特色產業和民族團結示范創建等方面推進特色村建設,完成16個少數民族特色村試點村的創建工作,涉及全市7個世居少數民族。
(保山市民宗局)
綠春縣民宗局舉辦“沿邊三年行動計劃”實用技術培訓 10月23日,綠春縣民宗局深入騎馬壩鄉舉辦“沿邊三年行動計劃”暨精準脫貧農村實用技術培訓,縣民宗局聘請縣農業局高級農技師全程授課。杯倮村委會“兩委”班子成員等74人參加培訓。
(綠春縣民宗局)
金平縣民宗局十件惠民實事贏民心 近期,金平縣民宗局爭取民族宗教專項資金項目18個,投入資金1192.8萬元,抓實“十百千萬”工程示范創建、扶持民貿民品生產企業、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綜合保險及學生助學補助、世居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搶救保護、創建和諧宗教場所、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特殊困難及產業發展補助、宣傳民族宗教政策法規、民族文化研究和保護、少數民族特困大學生救助等10項工作。
(繆汶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