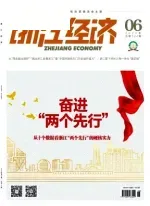讓生態(tài)環(huán)境價值化
文/柳博雋
自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建設生態(tài)文明,基本形成節(jié)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以來,“建設生態(tài)文明”遂公認為十七大報告的一大亮點。因為它不僅使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愈加清晰、完善,也體現(xiàn)了當代中國對世界和未來發(fā)展所作出的莊重承諾和擔當。
回顧過往,我國對生態(tài)保護的呼聲和努力其實一直沒有停止過。“十一五”規(guī)劃中更是將“節(jié)能減排”作為約束性指標,實施保障的力度可謂空前。然而,環(huán)顧大江南北、長城內(nèi)外,生態(tài)的破壞、環(huán)境的惡化迄今并未得到根本性扭轉(zhuǎn)。更讓人為之揪心的是,沿海發(fā)達地區(qū)所淘汰的一大批高污染制造企業(yè),正“大舉”向經(jīng)濟落后但生態(tài)環(huán)境尚且完好的內(nèi)陸山區(qū)遷移。那些最后的“桃花源”,正在難以避免地遭受著“黑色文明”的侵蝕。
問題的關鍵在哪里呢?
竊以為,當前市場經(jīng)濟大行其道,如果對生態(tài)文明的小心維護僅僅依靠個人良知、道德自律、政策宣導和文化教化所筑起的柵欄,那么在經(jīng)濟人的逐利沖動下,勢必會被摧枯拉朽般地沖毀。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想要建設生態(tài)文明,所執(zhí)牛耳,應該是讓生態(tài)環(huán)境價值化,讓原本無價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變得高價、天價。
要讓生態(tài)環(huán)境價值化,首先要明確并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產(chǎn)權歸屬。必須確認每個中國公民都有享用純凈飲用水、新鮮空氣和藍色天空的天賦權力,且這一權力也賦予了子子孫孫。任何一個企業(yè)或者利益群體都不能損害公民的這一“天賦人權”。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不僅要發(fā)揮監(jiān)督和裁判的功能,還要大力鼓勵公民的維權行動,并培育和壯大相應的NGO。
其次,要讓損壞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行為付出足夠的代價。用經(jīng)濟學術語來說,就是要將污染環(huán)境的外部成本內(nèi)在化,這也是“庇古稅”的由來。長期來,我國都沒有將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失所導致的成本,體現(xiàn)到企業(yè)的收益表里,表現(xiàn)在我國制造品的價格表中。要建設生態(tài)文明,首先要讓生態(tài)環(huán)境價值化、貨幣化、資本化,對高污染行業(yè)、企業(yè)課以重稅。對玩“貓捉老鼠”游戲的偷排企業(yè),一旦抓住則開出天價的罰單,使得其被抓的概率乘以高額罰款,要大大高出其偷排的收益,如此才有足夠的威懾力。還應穩(wěn)步推進資源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探索排污權交易、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等制度創(chuàng)新。
最后,要讓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行為獲得足夠的收益。為什么一些水源保護區(qū)、生態(tài)敏感區(qū),依然義無反顧地鐵了心要發(fā)展工業(yè)?這背后有著一定的體制因素,也是現(xiàn)行行政管理和財稅體制下的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現(xiàn)在的地方財政是“分灶吃飯”,主要的稅收又來源于流轉(zhuǎn)稅,導致地方政府不搞工業(yè)就沒有多少稅源。原本充當著整個區(qū)域重要生態(tài)保護功能的一些地區(qū),在生態(tài)補償和轉(zhuǎn)移支付難以真正落實到位的當下,只能拋棄全局和長遠的生態(tài)效益,不管有沒有條件也一窩蜂地跟風去搞大規(guī)模的工業(yè)化開發(fā)。某種意義上,也正是制度缺失,導致了地方政府必然的行為扭曲。亡羊補牢之舉,還是盡快建立有效和有份量的生態(tài)補償和財政轉(zhuǎn)移支付機制,真正落實“誰保護、誰受益”的原則。具體到地方政府的“指揮棒”激勵上,還應在領導干部考核評價機制中,不斷凸顯對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成效的權重。

讓生態(tài)環(huán)境價值化,就是要在全社會牢固確立生態(tài)環(huán)境也是有價值的這一基本認識,并在制度安排和戰(zhàn)略舉措上,全力保障這一認識的價值實現(xiàn)。這其實正好吻合我們對生態(tài)環(huán)境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從原來“只要金山銀山,不要綠水青山”到后來提出“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而如今要想最終解決問題,還是要建立和完善“綠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的體制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