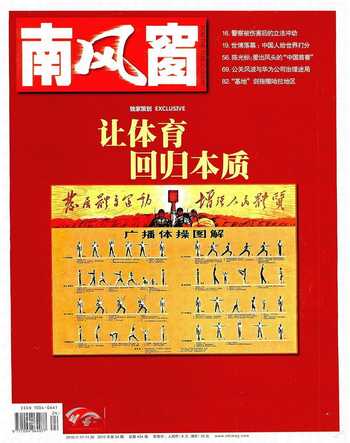房產稅劍指何方?
邢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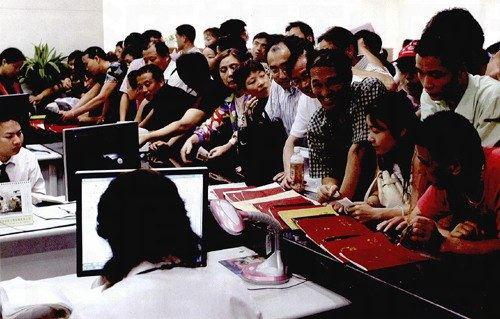


在目前這種高投入、參與投資的發展模式下,房產稅是解決不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沖動的。而一個現實的難題是,在目前財政預算透明度不強的情況下,如何確保稅收返還于比如廉租房、醫療、教育建設等公共利益支出?
進入10月以來,關于房產稅的討論再度喧囂。
事實上,作為一種財產稅稅種,房產稅曾在舊條文里休眠了24年,曾經熱議的合并稅種物業稅也在一些試點城市空轉了7年。
此番中央部委及地方政府再度釋放房產稅信息,所引發的爭論之激烈,足以說明今時社會矛盾之尖銳及利益沖突之復雜。
但來自國家部委的表態是紛紜的,而來自試點城市流傳的試點方案也差異頗大,這足以說明這一稅種開征的真實出發點及目標之模糊與搖擺。
征稅出發點
目前,財政部已將“完善房產稅制度”列入其2010年工作要點,而發改委在其2010年度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中也提及“逐步推進房產稅改革”。上海、重慶、深圳等城市也傳出將出臺試點方案的消息。
在目前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舉措不斷的背景之下,房產稅信息釋放的真實意圖究竟何在?
“開征房產稅的目的無非是兩個,一個是解決地方財政收入問題,一個是調控房地產市場。”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對本刊記者說。
2004~2005年,劉桓在北京市稅務局掛職副局長,其時北京正在進行物業稅空轉試點。“但那時候房地產價格尚沒有暴漲,所以當時出臺物業稅的目的是要解決土地財政的問題,因此決策層并未有決心要推進這一稅種的開征。”劉說。
現時追尋土地財政的問題,矛頭似乎都指向了1994年分稅制改革,但實際上,是自2004年8月31日之后,土地協議出讓被叫停,政府壟斷土地出讓渠道之后,才開始了一輪土地財政的突飆猛進。按照設想,物業稅作為一項財產稅,將為地方政府提供穩定的地方稅收來源,減少對土地財政的過分依賴。
而追尋房產稅的起源,則要歸結到1956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房產稅暫行條例》(下稱《暫行條例》)。1950年1月,當時的政務院公布《全國稅政實施要則》,規定全國統一征收房產稅、地產稅兩個稅種。同年6月調整稅收,將房產稅和地產稅合并為房地產稅。上世紀80年代,鑒于城鎮土地屬于國家所有,使用者沒有土地所有權,我國將城市房地產稅分為房產稅和城鎮土地稅兩個稅種,并于1986年頒布了《暫行條例》。在這個暫行條例中,“房產稅由產權所有人繳納”。
但與物業稅改革的基本框架是將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土地增值稅以及土地出讓金等稅費合并,轉化為房產保有階段統一收取,其額度及操作難度大大超于房產稅不同,房產稅的征收則看上去相對容易一些,因此在兩年前關于房產稅的討論亦開始出現。
真正到了1998年住房市場化改革之后,高房價問題逐漸成為城鎮居民的心頭之患,并伴隨其泡沫化,成為了一個社會矛盾集合體。在一些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結成牢固利益聯盟之后,房地產保有環節的稅收開始被賦予了解決地方財政收入和調控市場的作用。
但在國務院公布的《關于2009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中,對于住房保有環節的稅收的表述還是“深化房地產稅制改革,研究開征物業稅”。直到今年4月,新一輪房地產宏觀調控舉措“國十條”出臺,但仍未能遏制重點城市房價的快速攀升,“開征房產稅”開始頻頻亮相。
重拾一項只需國務院修改便可出臺的《暫行條例》,在劉桓看來一方面是應對宏觀調控之“失效”,同時又能給地方政府“開源”。一方面要穩定住房價格,一方面要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房產稅的開征似乎正好承受了這兩樣功能。
如果穩定房地產銷售價格,則可能出現的局面是土地成交量或成交金額下降,鑒于宏觀調控“打壓”的大環境,地方政府對土地出讓金收入的愿景也將有所下降。在未來城市化飽和,土地出讓金逐漸下降的情況下,從土地出讓收入轉向房屋保有環節稅收收入,亦是趨勢之一。
在這次積極申報房產稅試點的城市中,重慶目前的試點方案已上報至三部委會簽。而根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的報告,2010年1~9月,重慶土地出讓成交總價為286億元,同比下降9%。
現實矛盾
在劉桓看來,房產稅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完善財稅體系,作為房產保有環節的稅收,在過去是缺失的,這并不利于地產的調控,最明顯的是對住房空置率的調控,這一稅種對房地產市場上的投資、投機者具有擠出效應。
我國房地產市場現有主要稅費項目中,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土地增值稅、交易契稅等都集中在開發流通環節,而保有環節的稅種僅有城鎮土地使用稅和房產稅兩個稅種。
10月中旬,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對個人所有的住房恢復征收房產稅是必要的,“既有利于調節居民收入和財富分配,也有利于健全地方稅體系,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及土地節約集約利用,引導個人合理住房消費。”
“具體的征稅方案制定,將涉及房產稅可能發揮的功能不一。”北京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中國房地產學會副會長陳國強則對記者說。
“解決土地財政問題的一個前提是房產稅具有替代作用,房產稅作為一項財產稅,成為地方政府的穩定收入之后,將土地出讓金降下來,將交易環節的稅種合并,總體稅負降低。但這涉及的并非一項房產稅所能解決,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涉及的是事權和財權的分配,地方政府目前這種高投入、參與投資的發展模式下,一項稅收是解決不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沖動的。”陳國強認為。
這可能意味著,在土地財政無法改變的情況下,房產稅又作為一項額外的稅收,成為市場經濟體和購買者的另外一項稅負。
我國近年來的宏觀稅負一直呈現上升比例,以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來計算,我國近3年的宏觀稅負均超過30%,這一水平已經向工業化國家看齊,甚至有國外研究機構聲稱中國的稅負痛苦指數全球第二。
而中國的房產稅與歐美等土地私有制國家的房產稅之區別在于,中國城鎮土地為國有,消費者購房獲得房屋所有權70年,已攤分了土地出讓金,相當于攤分了房屋70年的租金。如果購房者已經支付了70年的土地租金,再支付土地持有環節的房產稅,則相當于重復征稅。
另一方面,“調節居民收入和財富分配,放在房產稅的身上,顯得有點大了。財富分配體系目前存在的問題,就像靠個人所得稅來調劑一樣,作用是有限的。財富分配體系的不合理目前主要在于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過重,初次分配不合理的問題最為突出,灰色收入和腐敗問題,這不僅僅是靠一項稅收就能解決得了的。”北大地產基金中心主任、北京國際發展投資有限公司CEO杜猛則對記者說。
“在這里面,官員的多套房產數據,要不要披露?怎么披露?”杜猛說。此外還有諸如福利分房、集資房等認定和估值技術難題的背后,實質又是利益群體的阻障。
陳國強同時認為,依靠房產稅來打擊目前的房產價格,這樣的期望太大,房產稅并非“核武器”,而是一個長效機制,立竿見影的效果是不太可能的,只會針對少部分的投資投機者征收。但改變不了中國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商品房住宅的供不應求的大格局。
“稅基過窄,稅率過低,調控的作用微少,稅基過寬,稅率過高,增加的稅負過重,要衡量具體的設計方案。”杜猛認為。
而在更多的人看來,開征一項新稅種所可能遇到的最大反對意見在于,稅負在增加,但稅收去向在目前財政預算透明度不強的情況下,如何返還于比如廉租房、醫療、教育建設等公共利益支出?這是一個現實的難題。
在種種爭議尚未厘清的情況下,據媒體報道,重慶市目前上報至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房產稅試點方案,采用了按“套數越多、面積越大”——稅率逐級提高的累進計稅方式,其原理與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稅率相同。而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已經啟動了對房地產稅的會簽程序,其中就包含采用累進計稅方式的“重慶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