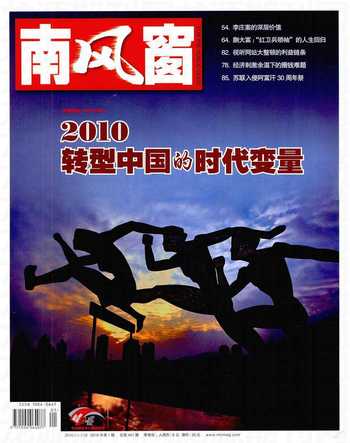普京這10年的思想軌跡
方 亮
隨著普京逐漸擺脫“強力集團”,俄羅斯社會在從1990年代的自由擺向普京時代的保守后,有望再次以稍小的幅度向自由方向擺動。只是,普京可以輕易地控制這種擺動的幅度。
1999年12月31日,葉利欽出人意料地宣布將總統職位交給弗拉基米爾·普京時,普京進入莫斯科權力圈剛滿40個月,出任總理則只有4個多月。但就在不到5個月的總理任期內,普京的支持率從2%拉抬到45%上下,原因不外乎他打贏了第二次車臣戰爭和克服了199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
普京在車臣戰爭中表現出的決斷力固然是戰爭勝利的關鍵,但克服1998年經濟危機,軍功章的一半應該分給危機頂峰時臨危受命的前總理普里馬科夫。而且,俄經濟1999和2000年分別實現3.2%和7.5%的增長,這實際上是拜1998年俄經濟降入谷底后的自然反彈所賜。在經濟問題上,普京是幸運的。
第二次車臣戰爭勝利后,普京乘坐蘇27戰機視察車臣首府格羅茲尼的舉動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讓普京“強人”、“鐵血”和“可以依靠的兄長”的形象深入人心。這樣,在2003年的總統選舉中,普京成功收獲了超過半數選民的支持,并在此后的幾年內保持著這樣的支持率,直到2007年前后其支持率開始在70%-80%的高位浮動。
“反叛”,“剝奪”與俄版“天鵝絨革命”
對1990年代失敗政策的反叛,構成了普京施政的第一條主線。不僅僅是在第二次車臣戰爭、莫斯科劇院人質事件以及別斯蘭事件中對車臣匪徒“以血還血”,包括媒體大亨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的出逃、尤科斯集團的倒掉、州長直選制度的廢除,所有這些無不是對1990年代自由化改革“反叛”后的結果。在這些行動中,普京“革”了那些在私有化過程中暴富的寡頭的“命”,在削弱了“反普”勢力的同時,“挺普”勢力接管了“反普”勢力曾經掌握的媒體、能源等關鍵產業集團,為普京勢力集團的壯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此時,剩下的寡頭集團由阿布拉莫維奇和杰里帕斯卡這樣的忠于克里姆林宮的商人組成,普京對他們的予奪可以十分自由地進行。2008年的經濟危機中,普京將寡頭集團徹底埋人了歷史的墳場。可以看出,普京在敵我之間游刃有余,的確是一位高明的權術大師。
縱容“強力集團”對寡頭的“剝奪”,是普京施政的第二條主線。在2002年發生莫斯科劇院人質劫持事件之后,普京推動杜馬提高了國家安全部門和軍隊的待遇水平。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此后,前蘇聯克格勃的特工和軍隊軍官以極大的規模滲入國家各級管理機關,慢慢地其人數在官僚機構中占到相當的比例,人稱“強力集團”。1996年俄羅斯第一輪大選中,軍人、警察以及安全部門人士將選票投給了列別德將軍,在第二輪中,他們中相當數量的人將選票投給了俄共主席久加諾夫。而在2000年選舉中,他們幾乎全都支持普京。
至于原因,除了同為克格勃特工的普京打贏了戰爭,為軍人、警察和特工們爭得了榮譽并讓他們受惠于政策傾斜外,普京政治中獨特的一面格外吸引這些“強力人士”——“剝奪”。就像斯大林上臺后剝奪教會和農民一樣,普京的“剝奪”體現在對寡頭的生殺予奪上。而要完成這種“剝奪”,非具有鋼鐵般意志的“強力集團”不能勝任。待到“強力集團”成功完成了“剝奪”,其中表現突出的分子直接被委任為“剝奪戰果”的管理者。謝欽,普京的一號心腹、“俄羅斯石油公司”管理人、除普京之外俄能源產業的頭號管理者,此人的“事跡”正是一個標準的“剝奪”版本。謝欽也曾是克格勃探員,從普京在圣彼得堡擔任副市長以來就一直擔任其助手,直到跟隨普京人住克里姆林宮。對尤科斯集團的拆解由謝欽親自操刀,至今俄羅斯網上還流傳著謝欽和人密謀如何對尤科斯下手的錄音片段。待得尤科斯“人頭落地”,謝欽分得了最大的一塊肥肉,成立了“俄羅斯石油公司”,并親自管理。現在,每當中國要從俄羅斯買油,都要同謝欽的公司談判。
就是這樣的“強力集團”成為普京施政的最有力保障。這個集團也因此而愈發壯大。慢慢地,“強力集團”與俄第一大黨統一俄羅斯黨有了某種交叉互融態勢。當普京于2008年擔任了“統俄黨”主席后,“強力集團”幾乎完成了對該黨的“靈魂附體”。這一過程以及“強力集團”控制俄羅斯的過程,被西方稱為一場俄羅斯本土的“天鵝絨革命”。“強力集團”的發跡使得俄羅斯政治充滿了保守特性,其對外表現尤其強烈,在“俄氣”集團針對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幾次“斷氣”行動中,這種戾氣表露無遺。
紅線內扶持“體制內自由派”上位
這場“天鵝絨革命”的結果是俄羅斯政策相對于1990年代的全面轉向以及政權精英的全面換血。當這場革命勝利的時候,普京和“強力集團”都登上了巔峰,其標志是2007年“統俄黨”在杜馬選舉中的大勝以及2008年梅德韋杰夫成功地被普京“授予”總統職位。在這兩次選舉中,“普京計劃”橫空出世,俄羅斯民眾對普京的崇拜幾乎達到頂峰,其支持率超過80%。
普京選擇梅德韋杰夫,而放棄也曾是特工的“強力集團”代表謝爾蓋·伊萬諾夫,標志著一個被稱為“體制內自由派”的群體浮出了水面。這群自由派已經遠不是1990年代幫助葉利欽設計“私有化”改革的那群人,甚至與他們有很大的距離。這群人多是技術型官僚。重視市場,支持自由媒體,主張在“強力集團”強加給俄羅斯的保守政治中加入自由成分。但他們也是民族主義者,支持除了社會和經濟政策以外普京幾乎所有的政策。他們主張加快俄羅斯現代化的腳步,并減少國家對石油天然氣出口收入的依賴。梅德韋杰夫正是這群人的代表,這也是現在梅德韋杰夫屢屢公開批評普京的深層原因。
“體制內自由派”的出現實際上是又一次“反叛”,是對保守政策的“反叛”。這群人同樣誕生于普京政權內,但他們遺傳了1990年代的自由思維。梅德韋杰夫的勝利讓“體制內自由派”歡欣鼓舞,總統職位的獲得至少說明普京希望在體制內保留自由主義成分。而如果再考慮到另外一個事實,那么“體制內自由派”在“總統爭奪戰”中的勝利則讓人們看到俄羅斯社會轉型的契機。長期研究俄羅斯精英的莫斯科大學教授克雷施坦諾夫斯卡婭公布了一份意義重大的研究成果,“強力集團”人士在俄羅斯官僚體系中所占比例已經從2007年的頂峰——2/3下降至了2009年的1/2,且這一下降趨勢仍在進行。
僅僅兩年時間,“強力集團”就從其巔峰跌落,與其同時發生的是梅德韋杰夫這一“體制內自由派”的“登頂”。如何解釋這一現象?梅氏上臺后對地方領導人的一系列更換是問題的一方面,這些新的地方領導人帶來新的技術型官僚。同時,梅氏上臺后又高擎反腐大旗,箭頭直指以“強力集團”為代表的
官僚階層。通過“剝奪”上位的“強力集團”血管中流著貪婪的血,這個群體在扮演普京整肅國家和扭轉國家發展方向工具的時候,自身的貪婪屬性得到空前的滿足。所以,當梅氏開始反腐時,“強力集團”將開始跌落。
另一方面是普京的態度。在自己曾經倚重的勢力跌落的時候,普京沒有對梅氏的做法“橫插一杠”,而是做出了支持梅氏反腐的決定,并帶頭公布了自己的個人收入。與此同時,“強力集團”人數上的下降說明了有一種意志在抑制其發展,而能夠擁有這種意志的唯有普京。
換句話說,普京在有意地擺脫“強力集團”。這群人只是普京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使用的工具,就像普京也曾使用寡頭一樣。與此對應的是,普京和梅氏在早些時候都公布了自己的所謂“黃金100”和“黃金1000”的人才儲備庫名單,這些名單中技術型官僚占絕大部分。盡管不能直接稱這些人是“體制內自由派”,但他們與“強力集團”的保守思維拉開了距離則是不爭的事實。這也說明了普京希望官僚機構的血統朝哪個方向轉變。當然,“強力集團”不可能一下子完全退出,他們仍掌握著俄政治中的許多命脈,其退出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由此看來,俄羅斯社會的指針在從1990年代的自由擺向普京時代的保守后,有望再次以稍小的幅度向自由方向擺動。只是,普京的權威意味著他可以輕易地控制這種擺動的幅度,甚至可以終止這種擺動。2008年金融危機來襲是對普京的一種考驗,事實證明,即使在危機最深重的時刻,普京支持率仍然排在第一位。這種態勢是建立在反對派被廣泛打壓無法伸展的基礎上,人們面臨著“沒有人可選,只能選普京”的境況。
任何一次成功的社會蛻變都離不開上層的思想解放和能夠承載這種思想解放的市民社會。俄羅斯上層的思想解放將隨著精英“換血”的過程逐漸展開。此時,俄政治出現了一條紅線,當跨過這條紅線的時候,“體制內自由派”以及技術官僚的勢力將一發不可收拾地壯大起來,那么何時將跨過這條紅線呢?普京有著無可比擬的裁量權。
目前俄政壇經常上演的橋段是梅氏和普京的“雙頭政治”大戲。梅氏如同祭出自己2012年競選口號一樣地到處宣揚“俄羅斯的現代化”,而普京卻在“統俄黨”代表大會上宣布俄羅斯將學習日本等國家,進行“保守的現代化”,也就是由一黨統領發展過程的“現代化”。正如西方媒體評論的那樣,兩人似乎越來越多地表現出競爭性。
但是,梅普關系到底如何?普京究竟如何看待“體制內自由派”?這是到目前為止尚未完全明朗的問題。這一切只能等待2012年總統大選的結果。屆時。普京和梅氏的去留將成為俄羅斯國家發展的最強烈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