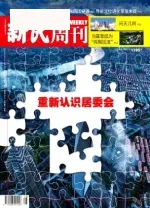嚴歌苓:只在文字的世界里“緊張”
何映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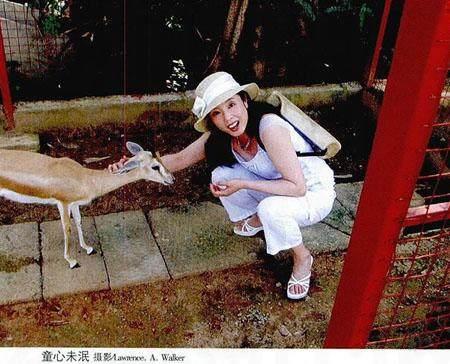

怎么寫?都是特立獨行的嚴氏風格說了算。
寒風中,嚴歌苓來到上海。此行的目的,既不是為新書簽售,也不是為寫作搜集素材,而是走秀。
你沒有聽錯。她和《我的青春我做主》中走紅的趙子琪搭檔,身著來自好萊塢著名設計師莊司正精心設計的晚裝,為某國際著名品牌腕表助陣。在中國,請一個作家來為商家吆喝,在嚴歌苓之前,似乎尚無先例。
53歲了,可是嚴歌苓在旁人看來,年齡似乎已定格,永遠是美麗中略帶憂郁的少女模樣,將人生悲喜,藏在心中。
年容未老,心已滄桑。
嚴歌苓當然是個“有故事的人”,否則,怎么能將那么多人世間的男女、生死、人性的掙扎、蒼涼與繁華寫得入木三分?
“大概因為我善于講故事,也喜歡刻畫人物吧。”她淡淡地說。生于上海,在安徽長大,12歲當兵學舞蹈,20歲做中越戰爭前線的戰地記者,從軍13年。進入魯迅文學院作家研究生班時,和莫言、余華是同班同學。1989年,一場不圓滿的婚姻之后,赴美學習,攻讀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文學寫作系的研究生,那一年,她已經32歲。一邊刷盤子,學叉子、西餐和咖啡,捋順了舌頭學英語單詞,敏感而痛苦的年代。這些經歷,從她的小說中一眼就看得出來,《穗子物語》、《一個女人的史詩》等作品都是軍隊題材的作品,《少女小漁》中剛到美國、像顆小小臺球感受著中西兩種文化碰撞的小漁,何嘗不是她當年苦苦奮斗的淚水化成?
也許是太有故事性的緣故,她的小說似乎特別容易改成影視作品并大獲成功。
她的閨蜜陳沖身為國際影星,也是位才華橫溢的導演,一出手就拿了臺灣金馬獎。她的處女作改編的,就是嚴歌苓的小說《天浴》,順便還捧紅在《奮斗》里喜歡吹口哨的李小璐。
還有《少女小漁》讓當時還頂著“陳升女弟子”頭銜的劉若英一舉登上亞太影后的寶座。雖然那是李安和張艾嘉改編的劇本,讓人感動的好電影,還是因為有嚴歌苓的小說作為堅強的支撐。爛片無數的年代,找一部好劇本,真如大海撈針,有劇本圣手在這里,何必舍近求遠?陳凱歌就特別喜歡她的作品,他說:“她的小說中潛在的,或是隱形的一個關于自由的概念,特別引人注目,我覺得,那就是個人自由。”于是,請她出山。
2009年,根據嚴歌苓小說改編的《小姨多鶴》在各地方臺熱播,之前更火的一部戲無疑是她編劇的《梅蘭芳》(其實是她和陳國富、張家魯共同編劇),雖然爭議不斷,但這并沒有影響張藝謀將嚴歌苓小說《金陵》改編成《金陵十三釵》。《三槍拍案驚奇》遭遇網民阻擊之后,老謀子在狂掙鈔票的同時,還是要考慮考慮自己的清譽,再如此一意孤行的結果恐怕就要人財兩空了。想來,張導是聰明人,自然也會考慮一下民意,摘掉“雷人張”的高帽子,這就需要張嚴的親密合作了。
看一看嚴歌苓未來的影視計劃:黃建新要導她的《赴宴者》、陳沖計劃將《小姨多鶴》和《第九個寡婦》搬上銀幕,姜文購買了她中篇小說《灰舞鞋》的電影版權……嚴歌苓的小說絕對是當下中國電影界最熱的香餑餑。她說自己寫小說和劇本很快,已根本不需再為發表和收入發愁。現在的嚴歌苓,和美國外交官勞倫斯結婚后,在伯克萊的海灣有一套漂亮的房子,2006年后,又常住臺灣,北京的房子,回大陸的時候才住著,生活優渥亦閑適,只有在小說或劇本的世界里,她才突然變得“緊張”起來,讓戲劇性的沖突和人性的善與惡控制著主人公的命運,寫,怎么寫?都是特立獨行的嚴氏風格說了算。
金牌編劇和導演
《新民周刊》:大家都知道,陳沖和你是特別好的朋友,我想知道最初和陳沖是怎么結識的?據說和陳沖一碰到就整天黏在一起玩,吃飯、逛街、買衣服?真的好到這樣的程度?
嚴歌苓:說起來,和陳沖的最初結識是因為我父親和我繼母的關系。那時候陳沖的哥哥陳川和畫家陳逸飛常到我爸爸住的賓館去玩,有幾次就把陳沖帶來了。你們可能不知道,陳沖的第一部電影《青春》恰巧是和我繼母俞平一塊演的,這樣一來二去,我們就認識了,而且很快就成了非常要好投緣的朋友。
以前我們在一起確實常去逛街,但現在我和陳沖已經不怎么逛街買衣服了。在美國大家都是牛仔褲T恤衫,穿得太漂亮像是挑釁大眾似的,現在的話,我們在一塊的時候其實是燒菜比較多呢。
《新民周刊》:我知道你有一篇小說《灰舞鞋》已經被姜文購買了版權,一個拍攝了《鬼子來了》這樣粗礪的、有力量的電影的導演,你會不會擔心他把《灰舞鞋》拍得太硬了?會不會有些問題?
嚴歌苓:姜文是個很有天才的導演,我不擔心他會拍不好任何風格的戲,我只擔心他的激情持續多久。對于一個作品的激情不可能永遠維持,這不是姜文一個人的問題,我自己也有這樣的問題。
《新民周刊》:2008年你擔任陳凱歌電影《梅蘭芳》的編劇,這部戲出來后褒貶不一,特別是對于其中對齊如山的描寫引起了齊家后人的很大不滿,你是故意要加入虛構的成分,還是覺得你寫的就是真實的齊如山?
嚴歌苓:我說過不止一遍了,那個人物又不是齊如山,梅蘭芳的班底又不止齊如山一個人!我在幾次采訪中說過,這是綜合了一些梅黨人物創作出來的人物。寫傳記難,因為永遠擺脫不了有人要對號入座的糾葛。
《新民周刊》:寫《梅蘭芳》之前,看過梅蘭芳的京劇嗎?對他熟悉嗎?后來《梅蘭芳》電影放映之后,你看完對這部電影還滿意嗎?
嚴歌苓:我只看過梅蘭芳在錄像帶上唱的戲。非常精彩。對于他的了解一部分也來自于我的外婆和祖母,他們都看過梅蘭芳的戲,都對他頂禮膜拜。但我自己對于京劇是完全的門外漢,那點知識都是樣板戲給的,假如還能叫它們京劇的話。現在的電影,尤其像《梅蘭芳》這樣嚴肅的電影,缺乏的是理論性、美學性高的嚴肅的影評。網上不負責任的發言成了大家給一個電影打分的依據,這是非常悲哀的事。
《新民周刊》:好像《白蛇》是陳凱歌下一部要拍的電影嗎?什么時候可以開拍?
嚴歌苓:凱歌導演下一步要拍的不是《白蛇》。下面我們還會合作一個電影,但不是《白蛇》。《白蛇》這樣的題材,你覺得它能通過電影審查嗎?
《新民周刊》:你是好萊塢編劇協會會員,前段時間國內的編劇因薪酬問題而鬧得沸沸揚揚,不知道美國的編劇薪酬情況是怎么樣的?
嚴歌苓:好萊塢的編劇協會每一次罷工,都會把協會會員的最低稿酬鬧得高一些。但中國編劇的稿酬也在上升中。國內沒有這個協會,所以編劇的權益沒有受到保護。其他電影行當也一樣,沒有業內人自己的組織來保護自己的權益。
《新民周刊》:據說《金陵十三釵》的劇本是因為《南京,南京》而擱置,你有沒有看過陸川導演的《南京,南京》這部電影?
嚴歌苓:我一直在國外,所以沒有看到《南京,南京》。
寫作:“我是個圖痛快的人”
《新民周刊》:你曾經說過:“我喜歡寫女人,就像世界上所有漂亮的衣服、首飾都是給女人的一樣,寫她們很過癮。”比如你的小說《一個女人的史詩》這個題目基本上可以視作是你的小說寫作的一個宗旨:為女性立傳,從一個女性的人生歷程來折射歷史的變遷。對你來說,什么時候開始有一種獨立的女性意識來創作小說?有沒有考慮過以男性視角來寫作一部小說?
嚴歌苓:豈只是我愛寫女性!不說國外的和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家,光看國內當代的男作家,包括蘇童、莫言、畢飛宇等等,他們筆下的女人比男人更難忘。尤其是蘇童。其實我寫過男性為主角的小說。比方我的中篇小說《倒淌河》、《拉斯維加斯的謎語》、英語小說《赴宴者》等等。但是因為自己是女人,寫女人對于我更加自然。另外就是我的女朋友很多,女朋友告訴我她們的女朋友的故事,有寫不盡的題材。我覺得有趣的是:女人們似乎更愿意談論女人,而不是男性。這樣我得到有關女人的素材就比得到男人的要多。不過我冷不防就會寫一本以男性為主人公的小說,也說不定呢。
《新民周刊》:《有個女孩叫穗子》是你的中短篇小說集,其中的小說可以獨立成章,但是串在一起的就是叫穗子的女孩子,這個女孩子的身上是否也有你本人的很多影子?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穗子這個形象其實是很接近你本人的?
嚴歌苓:是有一點我自己的影子,她是比較接近我,每一篇都有我的經歷,然后發酵后變成小說。童年時候有一些故事是聽來的,有一些是看來的,但都只是一點因子,被想象力發酵,補充,完整了。參軍后的故事里面,我們確實有過那么一只狗,許多細節也是真的。還有那個西藏女孩,很多細節是真的。我多次說過,細節很難編。我的美國教授說,寫什么不重要,怎樣寫就是小說的一切。我還要加一點:一篇小說“說”的是什么,也非常重要。這個“說”就是英語所指的小說家通過小說發送的“message”,是字面下的訊息。一篇小說怎樣寫是文字的問題,而“說”什么往往是一個小說家的全部素質決定的。國內好故事漫天飛,但不是每一個好故事都能被寫成一個好小說。這要看小說家們怎樣說這些故事,以及用這些小說“說”什么。
《新民周刊》:談到“怎么寫”的問題,我記得李黎對我說過,你為寫小說搜集了很多檔案,其中有沒有《寄居者》中那位上世紀40年代在上海呼風喚雨的猶太大亨的原型?
嚴歌苓:史料里沒有杰克布這個人物的原型,這是我虛構的人物,除了小說的戲劇構架,小說里的所有人物都是虛構的。這是一部純粹虛構的小說。就像我的絕大部分作品和絕大部分作品中人物一樣,都是我虛構的,只不過虛構的成分有多有少而已。有些小說我也會做歷史資料的搜集和調查,但是我要強調的是:無論調查得多么細致,得到的資料多么真實豐富,目的都不是為了省去虛構這一小說創作這第一重要手段啊。
《新民周刊》:你說寫小說“我也算是快刀手”,寫一部《寄居者》這樣的長篇需要多少時間?哈金說,他的小說反復修改多遍,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是要字斟句酌?
嚴歌苓:我寫東西是很快,做其他事情我也一樣快。我是個圖痛快的人。任何事情有激情就一氣呵成地做。所以寫小說就是這樣,抓住一種感覺,找到一種語氣,對于一篇小說的創作非常重要,假如感覺和語氣斷了,再重新找,很困難,有時干脆就找不著了。我的一些小說流產,就是因為感覺和語氣斷了。我覺得現在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說擱下一篇小說就要擱下,我就特別怕這樣把一篇原來能寫得很好的小說感覺、語氣給丟了,所以有一段相對集中穩定的時間就爭取一口氣寫完,這就是我為什么顯得寫得那么快。但我做一篇小說的準備工作是非常長時間的,有時候需要十來年。我讀D.H.勞倫斯的傳記時,發現他寫小說也很快,所以就對自己的創作習慣放心了。一個人有一個人創作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