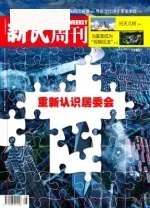編與讀
回憶裘沛然
裘沛然先生一生心系中醫的現代化問題,隨著他這一代著名中醫師逐漸凋零,這個問題會不會越來越無解呢?
我一向認為,近現代中醫行業的被迫轉型是和中國整個社會被迫轉型是一致的。只要打開國門,人的頭腦西化,新生代自從出生起,就有“西方月亮比中國圓”的潛意識,“科學”(西方的分解還原論)慣了,對于中國固有的東西也就當作垃圾去丟了,中醫也就遇到這種境地。民國也好,新中國也好,中醫行業一直在遭受痛苦。
在西方醫學(西醫,現在中國叫它“現代醫學”,也就是說言下之意,中國固有醫學是“古代醫學”)進入中國之前,并沒有中醫一詞;中國的近代歷史就是一本內力、外力作用下向西方社會形態轉型的歷史,這個轉型是充滿屈辱、充滿痛苦、不得不進行的一個過程。
中醫歷來有兩大學派,也就是原來處于主導地位的辨證論治派和處于劣勢的辨病論治派(與現在西醫比較一致)。中醫歷來有辨證結合辨病的傳統。現在辨病儼然成了主導,并且不用原來的中藥,用到西藥去了,這就丟掉了中醫的辨病學派,而且就成了西醫;再加上現在的辨證論治學派在“市場經濟”(實際上是西藥的回扣)和學生腦子西化、政策西化的多重打擊下,實在是岌岌可危。但是,有關部門的政策西化也是有原因的,現代民眾和西醫已經是應用西方的思維模式,中醫應用中醫藥是應該同民眾接軌,也就是我常說的中醫必須用西醫的語言去翻譯中醫,主動接觸——民眾、政府官員和西醫,這條路也是必須走的。多數的中青年中醫感到彷徨,要說他們都不會用中醫看病,我想不是事實;但又有多少真正下功夫用中醫看病的,要問一問中醫們自己。現在似乎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現在現代化比較熱鬧的是中藥專病化,因為藥廠要有利益,利用中藥發財,資本擴張,摧殘了中醫的辨證施治。中醫行業看上去選擇了“適應”社會,選擇了所謂的中西醫結合,但是正在逐步喪失自己的優勢,不知道大多數中醫師意識到沒有。
美國華盛頓 樊鎣
編輯:
上海世博開幕三周,由于一直是晚上入園,沒能領到預約票參觀中國館。5月17日,我第五次進入園區。為了拿到預約券,我早上6點多就起來,趕到了9點開門前第一批接受安檢,幸運的在2號門入口處領到了晚上8點半到9點的預約券。由于浦西最佳案例區和幾個企業館區感到頗多意外驚喜,服務人員也很熱情,于是一口氣逛到晚上8點,興沖沖地等待進入中國館。
排隊等到8點半,順利搭乘扶梯進入中國館內場一層后,我發現回形的等待區還有300名左右的游客在排隊搭乘電梯。很多人都和我一樣,是專程來看中國館的。排隊期間不斷的有焦急的團隊游客插隊到我前面,身著綠色制服的工作人員無奈中卻并未制止。我們等了一個多小時,沒有任何工作人員通過廣播或擴音器為我們介紹場館,或者提醒我們應該等待的時間。
9點40分,我們終于通過電梯進入中國館第12層。剛出電梯,工作人員拿著擴音器高聲快速地說:“馬上就要閉館了,請大家快速參觀《清明上河圖》”。游客開始小跑。所有工作人員開始催促游客往前走,盡快離開12層。
我參觀世博園5天,幾乎所有場館的工作人員都是等最后一批游客參觀完,講解完再等待游客離開的。恰好,我進入比利時館時也是最后一批,工作人員依舊耐心講解,熱情招呼。我想,作為主辦國的主館,即便是在快到下班時間,也應該滿足從世界各地趕來的游客們一飽中國風采的心愿。端莊的儀態,和藹的態度,熱情的講解,應該是場館工作人員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客人在進行了一天的等待后,觀看《清明上河圖》僅僅不到5分鐘,即被急躁地勸離場館,這實在是太遺憾了。
陳靜茜
(對本刊刊登的任何文章有批評或建議,請致信xmletters@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