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復原本》與中國之謎
○張遠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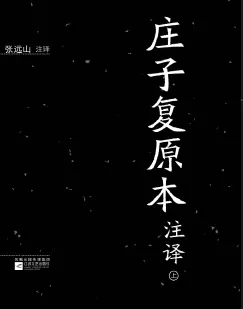
《莊子復原本注譯》,張遠山著,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8月版,98.00元
中國之謎的謎底,蘊含于如下謎面之中:唐宋以前一千年,是古典中國興盛期,也是魏牟版、劉安版真《莊子》的流傳期。唐宋以后一千年,是古典中國衰退期,也是郭象版偽《莊子》的流傳期。古典中國的兩千年興衰,與真偽《莊子》的兩千年流變同步,決非偶然。
從“五四”到“文革”,古典中國被批倒批臭。余生也晚,未及“五四”,僅歷“文革”。其時年幼無知,仍有莫大疑惑:古典中國的登峰造極,究竟是真實存在的歷史圖景,還是向壁虛構的鏡花水月?為了探究這一中國之謎,1980年我由理科改考文科,進大學后直奔先秦,開始了終生系之的漫長求索。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相互競爭于廟堂、江湖,大師云集,精彩紛呈。儒道兩家最后勝出,瓜分了此后兩千年的勢力范圍:儒家經典成了政治圣經,建構了當時全球范圍之內最為嚴密完備的廟堂悖道政治,搭建了古典中國的唯一政治舞臺。道家經典成了文化圣經,創造了當時全球范圍之內最為美妙完善的江湖順道文化,提供了古典中國的無數文化劇目。雖然儒道兩家的思想張力始終大于思想合力,然而兩家共同創造了兩千年燦爛文明。
儒家主宰的廟堂政治與道家左右的江湖文化,具有悖道、順道的巨大張力,緩解這一巨大張力遂成古典中國不可懈怠的最大難題。由于現代中國與古典中國剪不斷理還亂、既斷裂又延續的特殊關系,廟堂悖道政治與江湖順道文化的巨大張力,時至今日有些仍未消除。古典中國以及現代中國的權力格局,則決定了對峙雙方緩解張力的不同因應方式。
江湖達人,陸沉間世
江湖順道文化的傳承者緩解巨大張力的基本因應方式是,自隱江湖,遠離廟堂。莊門弟子所撰《則陽》,把向往天賦自由、反抗廟堂奴役的自隱不彰,稱為“陸沉”,其義源于莊子親撰的《大宗師》:“泉涸,魚相與處于陸。與其相哐句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莊子認為,君主專制的悖道政治,導致全體臣民“役人之役,適人之適”(《大宗師》),失去了“以德為循,自適其適”(《大宗師》)的天賦自由,如同魚處于陸。因此“陸沉”之義,就是自隱于廟堂悖道政治造成的無水之陸,自隱于廟堂悖道政治造成的險惡外境。“陸沉”自隱的變文,遍布于莊子親撰的內七篇,《齊物論》稱為“不用而寓諸庸”,《養生主》稱為“善刀而藏之”、“不祈畜乎樊中”,《德充符》稱為“才全而德不形,內葆之而外不蕩”,《人間世》稱為“間世”。逍遙江湖、反抗廟堂的“間世”方式,莊子不僅反復表述,而且終身踐行,成為后世追慕仿效的不朽典范,深深融入長期處于悖道政治外境的中華民族骨髓之中。
遠離廟堂的江湖達人,遍布古典中國的一切時空,成為陰暗的廟堂政治之外最為耀眼的文化景觀,故有所謂“小隱隱于鄉,中隱隱于市,大隱隱于朝”。江湖達人的文學象征,就是超越廟堂、傲視帝王的“仙人”。美妙無比的文學表述,連不幸生于帝王之家、不得不倚待廟堂的帝王將相也心馳神往。因為帝王將相雖是特權自由的享有者和獨霸者,仍是天賦自由的匱乏者和向往者。特權自由如同包辦婚姻娶來的絕世佳人,天賦自由如同自由戀愛贏得的小家碧玉,哪怕后者稍遜前者,也因兩者獲得方式之不同,決定了自由芬芳之有無。人無我有的特權自由,僅是倚待廟堂的古代臣民的肉身放縱。人我同享的天賦自由,才是笑傲江湖的現代公民的精神狂歡。
每一朝代的同時代人,對于本朝的江湖達人都知之甚少。但是每一后續朝代,都把前一朝代鮮為人知的江湖達人,視為前一朝代的精神標高。后一朝代為前一朝代所修正史,常常特辟無關廟堂大局的《隱逸傳》。修史之朝表彰遠離前朝廟堂的江湖達人,意在譴責前朝廟堂之悖道,自詡本朝廟堂之順道。殊不知后一朝代為本朝修史,仍有《隱逸傳》,其意仍同。因此字面不通、蘊含中國之謎的“著名隱士”,貫穿于兩千年中國史。
正是高蹈自隱于悖道廟堂之外的無數江湖達人,創造了中華順道文化,其成果遍及衣食住行等一切物質生活領域,遍及琴棋書畫等一切精神生活領域,因此帝王將相與普通民眾一樣,其個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受惠于江湖順道文化。不僅如此,悖道廟堂又把順道江湖的輝煌成果,作為傲視萬邦的理由,自詡順道的借口。其實中華順道文化的一切成果,都與儒家思想無關,僅受道家思想滋養,尤其與《莊子》息息相關。所以廟堂衰微的亂世,都是江湖輝煌的盛世。戰國、魏晉、六朝、五代、南宋、晚明、清末、民初,無一例外。個體亦然,士人倚待廟堂之時,假裝信奉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廟堂意識形態;士人遠離廟堂之時,大多信仰以道家思想為核心的江湖順道文化。假裝信奉儒家、真正信仰道家之人,都被稱為“性情中人”,業已蘊含中國之謎的謎底。
廟堂君子,篡改曲解
廟堂悖道政治的代言人緩解巨大張力的基本因應方式是,篡改曲解乃至篡改反注道家經典,主要集中于《老子》、《莊子》。
著力于《老子》的廟堂政治代言人,舉其要者,先秦有韓非的《解老》、《喻老》,漢代有嚴遵、河上公的《老子注》,集大成于魏晉儒生王弼的《老子注》。后世老學家對王弼毀譽參半,不奉王弼為老學至高權威。原因是王弼以儒解老,篡改曲解《老子》,動作幅度甚小。王弼曲注與《老子》原文的牾,始終未能徹底消除,因此后世老學家不斷反詰王弼。近年又不斷出土戰國秦漢的《老子》簡帛,王弼的老學權威遭到進一步削弱,僅僅淪為曾有重大歷史影響的一家之言。
著力于《莊子》的廟堂政治代言人,舉其要者,先秦有呂不韋、荀況、韓非,西漢有賈誼、司馬遷、劉向、揚雄,東漢有桓譚、班固,魏晉有司馬彪、崔撰言、向秀等,集大成于西晉儒生郭象的《莊子注》。后世莊學家多奉郭象為莊學至高權威,認為郭象“獨會莊生之旨”(唐陸德明《莊子釋文序錄》)。原因是郭象以儒解莊,篡改反注《莊子》,動作幅度極大。郭象對著錄于正史的《莊子》大全本“五十二篇”(《漢書》)、“十余萬言”(《史記》),刪去十九篇、四五萬言,變成郭象版《莊子》刪改本三十三篇、六萬六千言,又對刪存的三十三篇,再予裁剪拼接、移外入雜、增刪改字、妄斷反注。郭象反注與郭象版《莊子》偽原文的牾,在郭象手里已經基本消除,因此后世莊學家極少反詰郭象。
顧頡剛探究中華上古史,結論是“層累造偽”。我探究《莊子》流變史,結論同樣是“層累造偽”。郭象及其追隨者一千七百年的層累造偽,使郭象版《莊子》成了面目全非的偽《莊子》;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的莊子,改造成了“役人之役,適人之適”的“天之戮民”,把“息黥補劓”、“攖而后成”的《莊子》,改造成了黥劓民眾、攖擾天下的偽《莊子》;把真《莊子》的宗旨“天道人道兩行”,改造成了偽《莊子》的宗旨“名教即自然”。概而言之,郭象及其追隨者把古典中國的頭號自由宗師,改造成了古典中國的頭號專制幫閑,把弘揚江湖順道文化的道家真經,改造成了鼓吹廟堂悖道政治的儒家偽經。
鳥盡弓藏,兔死狗烹
不宜認為王弼更有學術操守,郭象更無學術操守,因為王弼治老,郭象治莊,均非學術行為,均屬政治行為,正如“文革”時期“評法批儒”、“批林批孔”,都是政治行為。郭象篡改《莊子》之所以比王弼篡改《老子》動作更大,首先是客觀原因,即《莊子》比《老子》反廟堂更甚。其次才是主觀原因,即郭象比王弼人格卑劣。郭象官至黃門侍郎、太傅主簿,“任職當權,熏灼內外”(《晉書·郭象傳》),剽竊向秀《莊子注》。王弼則無劣跡,僅是出身門閥世家,天然維護廟堂。
“獨尊儒術”的兩漢之解體,導致魏晉廟堂深陷意識形態危機。為了挽救廟堂意識形態危機,王弼、郭象不得不事急從權地大搞統戰,對《老子》、《莊子》進行創造性篡改,把廟堂悖道政治的終極天敵,暫時整容為廟堂悖道政治的統戰諍友。
王弼無須大量篡改《老子》原文,其統戰式曲注就能輕易成功。因為《老子》僅是低調規勸“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三十七章),“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七十八章),其與廟堂悖道政治的張力較小,極易調和。早在戰國之時,老學即已融入當時最大的御用學術中心、齊國稷下學宮的主流學派“黃老之學”。悖道最甚的秦朝短命速亡以后,黃老之學一度成為西漢初年的廟堂官學,直到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才被黜退。黜退以后,喜愛《老子》者并不限于江湖達人,廟堂君子仍然視若拱璧。三位截然不同的帝王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均為《老子》親自撰寫御注。近年不斷有《老子》簡帛出土于王侯之墓,同樣證明老學易被廟堂改造利用。
郭象只有大量篡改《莊子》原文,其統戰式反注方能勉強成功。因為《莊子》高調宣布“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人間世》),“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讓王》),其與廟堂悖道政治的張力極大,極難調和。早在戰國之時,孟軻、荀況、宋開、尹文、慎到、田駢、鄒衍等倚待廟堂的絕大多數諸子大佬,紛紛趨赴稷下學宮,唯有公然挑戰廟堂、痛斥“昏上亂相”(《山木》)的莊子例外。三為稷下祭酒的大儒荀況,妄詆“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鐘情老學的荀況弟子韓非,則對早已死去的莊子發出死亡威脅:“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以莊子為師”、“非湯武,薄周孔”的嵇康被魏晉廟堂誅殺,為恨不得對莊子開棺鞭尸的韓非之專制叫囂,追加了血腥注腳。“以莊周為模則”、撰寫《達莊論》的阮籍,協助嵇康把《莊子》的重要性提升至超越《老子》之上。于是竹林七賢以后,“老莊”變成“莊老”,《莊子》成為魏晉以后江湖順道文化挑戰廟堂悖道政治的首要旗幟。
王弼《老子注》和郭象《莊子注》,都是魏晉時期冒充道家、實為儒家的“玄學”代表作,共同特征是以儒解道,共同宗旨是挽救廟堂意識形態危機。偽道家王弼、郭象與真道家嵇康、阮籍原本不屬同一量級,僅因悖道廟堂以權力介入學術,結果“至言不出,俗言勝也”(《莊子復原本·泰初》)。道家兩大經典均被廟堂代言人運用統戰策略反向消解,成為唐宋廟堂憑空虛構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奠基石。
唐宋廟堂成功虛構“三教合一”,廟堂意識形態危機業已安然度過。儒學也蛻變為理學,又重新站穩腳跟,于是理學代表人物拋棄統戰策略,再次劃清敵友。程頤曰:“莊子叛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于圣人乎?”(《二程遺書》卷二十五)朱熹曰:“自晉以來,解經者卻改變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舍經而自作文。”(《朱子語類》卷六十七)
程、朱之言,再次證實了道家對廟堂悖道政治的洞見“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王弼、郭象挽救廟堂意識形態危機,事急從權地大搞統戰,假裝認敵為友,僅是魏晉時期的“政治正確”。程頤對前統戰對象莊子重算老賬,朱熹對前統戰功臣王弼、郭象過河拆橋,則是唐宋以后的“政治正確”。既然江湖之鳥已盡,江湖之兔已死,那么廟堂之弓和廟堂之狗,就會因為“政治正確”的時移世易,而被廟堂秋后算賬。其實廟堂代言人為了貪戀及身小年的廟堂富貴,也無暇顧及千秋大年的江湖清譽。
復原《莊子》,破解謎底
《莊子》的反廟堂本質永遠不變,正如司馬遷早已明言的“莊子詆詈孔子之徒”、“是以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所以古代王侯之墓頗多《老子》簡帛,極少《莊子》簡帛。然而反廟堂的先秦之書無數,《墨子》、《關尹子》、《子華子》、《惠子》、《公孫龍子》、《公子牟》等,或殘滅于秦始皇之焚書,或殘滅于漢武帝之罷黜,唯有挑戰廟堂的最大反書《莊子》,任何專制帝王都難以徹底剿滅。盡管魏牟版《莊子》初始本被劉安版《莊子》大全本正淘汰,劉安版《莊子》大全本又被郭象版《莊子》刪改本逆淘汰,然而亡佚之前,仍有向往天賦自由、反抗廟堂奴役的無數士人,大量引用魏牟版、劉安版《莊子》,許多引言不在郭象版《莊子》之內。因此魏牟版、劉安版《莊子》盡管亡佚千年,奢望其簡帛出土于王侯之墓又屬枉然,葬入普通士人之墓的簡帛也早已爛光,但是散見于正史、類書、筆記的大量《莊子》佚文,仍為集腋成裘地復原魏牟版、劉安版《莊子》留下了微弱可能。
無數酷愛《莊子》的學者,曾經搜羅《莊子》佚文,考訂《莊子》原貌,舉其要者有南宋王應麟,明人閻若璩,近人馬敘倫、劉文典、王叔岷等。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充分吸納前賢成果,終于在今年初完成了《莊子復原本》。
拙著《莊子復原本注譯》,正編復原的是成書于戰國的魏牟版《莊子》初始本,附編的是復原成書于西漢的劉安版《莊子》大全本。雖然無法恢復全貌,只能恢復概貌,然而有助于重新認識這一古典中國的文化圣經,有助于重新探究古典中國的不解之謎。
中國之謎的謎底,蘊含于如下謎面之中:唐宋以前一千年,是古典中國興盛期,也是魏牟版、劉安版真《莊子》的流傳期。唐宋以后一千年,是古典中國衰退期,也是郭象版偽《莊子》的流傳期。古典中國的兩千年興衰,與真偽《莊子》的兩千年流變同步,決非偶然。
雖然五四時期對古典中國的批判有偏激化傾向,“文革”時期對古典中國的批判有政治化傾向,然而兩者的批判矛頭共同指向廟堂政治,并非全無準星。但是僅因古典中國的廟堂悖道政治已不適應現代世界,就全盤否定古典中國的江湖順道文化,乃至無視滋養、催生了一切江湖順道文化的《莊子》,那么古典中國的登峰造極,就無從索解,廟堂亂世均為江湖盛世的中國之謎,就難覓謎底。
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古典中國之陳舊政治舞臺,必須轉型重建。以道家思想為核心的古典中國之優秀文化劇目,必須發揚光大。中華順道文化曾經賜福古典中國,仍在賜福今日中國,還將在嶄新的現代政治舞臺上賜福未來中國,進而賜福人類全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