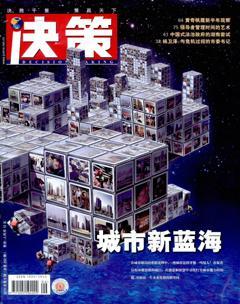中國式法治政府的湖南嘗試
劉湘琛

自由裁量權不應是專制的、含糊不清的、捉摸不定的權力,而應是法定的、遵循一定規范的權力。
——[英]科克大法官
權力到底應多大
“收”、“放”之間的世界級難題
2010年4月17日,關于規范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全國首部地方性規章——《湖南省規范行政裁量權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生效。一個星期后,推動該《辦法》的核心人物——湖南省省長周強被正式任命為中共湖南省委書記。
在中央醞釀《關于規范行政裁量權工作的指導意見》的背景下,這個被媒體稱為“關于行政裁量權規范的全方位改革”的《辦法》,與此前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配套,是湖南大膽破解中國式法治政府難題的有益嘗試,亦得到了中央的首肯。而湖南之所以敢于率先破題,無疑得益于周強系統的法學科班教育背景。
行政裁量權,是指行政機關在法定權限和法定職責范圍內,自主決定處理行政事務的權力。它不是一種獨立的行政權,而是寓于其他行政權力之中,包括行政決策裁量權、行政執法裁量權和行政監督裁量權。
對行政裁量權的規范,難就難在需要在“自由”與“控制”之間尋求合理的平衡。平常在人們的印象中,所謂好的單位就是行政處罰多,單位有實惠,個人又有油水,其實真正原因是自由裁量大,自由裁量權很容易使權力被尋租,導致腐敗。
同時,面對這一難題的絕不僅僅只有中國政府,只要有政府的管理行為,就會存在行政自由裁量權,世界各國政府均需在“收”、“放”之間進行權衡與選擇。當前,對政府行政執法詬病最多的一點,就是政府的行政自由裁量權過大,比如道路交通法第99條規定,機動車行駛超速的罰款從200元到2000元。再如按照有關法律,水利局可處1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但罰多罰少由執法人員“視具體情況”自由裁量。最低幅度與最高幅度的比例達20倍之多,這往往為執法人員權力濫用和權力尋租提供了空間。
如何更好把握“收”、“放”的尺度?世界諸多國家都進行了長期探索。以美國為例,1977年至今,國會通過立法,在民用航空、地面交通、長途電話、銀行、天然氣等行業徹底廢除或大大降低了行政管制,自由裁量權的空間大為縮小。而在繼續保留行政裁量權的領域,如美國的環境監管領域,也改變了傳統的以強制、處罰為主的剛性行政執法模式,轉變為行政合同、行政指導、行政調解等方式,利用價格等經濟機制的傳導作用,實現社會整體福利的最大化。
由此可見,盡管行政裁量權在美國經歷了由單純的行政管理上升為追求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共贏,但它始終圍繞一個不變的基點——正當程序原則,即行政行為必須符合程序正當性的三個核心要素——通知,評論或聽證,以及陳述理由。而當行政行為已成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項重要內容時,引導政府朝著“小政府”、“有效政府”和“法治政府”的方向發展,以法律明確行政裁量權的程序和界限,不失為美國實踐的成功經驗。
把權力關進籠子里以程序為核心的法治約束
《湖南省規范行政裁量權辦法》的最大亮點在于對于規范行政裁量權的世界級難題,給出了一種中國式的解讀。在這個意義上,規范行政裁量權并不是消極的廢棄,抑或單純的控制,而是將行政裁量權置于法治框架之內進行疏導,使之有序、合理,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雙贏。
圍繞著這一思路,此次湖南改革立足于行政機關自身對行政裁量權的自控,構建起以五項制度融為一體的規范機制,利用五個步驟將權力關進籠子里。
首當其中的是源頭控制制度。其目的是為了清晰界定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之間的范圍,厘清行政職能的界限,以便從宏觀上進行整體性的規范與把握。
在以往的操作中,行政審批、行政確認、行政處罰、行政強制、行政檢查、行政征收是行政職權的具體實施手段,內含大量的行政自由裁量權。改革開放以來,行政機關承擔了大量管理市場與社會事務的職能,法律授予行政機關行政裁量權時,往往范圍較廣、權限較大。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約和管理,極易導致行政裁量權的濫用。
為正本清源,《辦法》第七條規定,行政機關在法定權限內起草地方性法規草案、制定政府規章和規范性政府文件時,應當嚴格控制和合理設定行政職權;對已經設定的行政職權,必須定期清理,及時修改或廢止。第八條進一步規定,行政機關在立法授予行政職權時,應對行政權力的行使主體、條件、種類、幅度等要素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盡可能減少行政裁量權的空間。
控制源頭之后,改革所邁出的第二步則是建立規則。湖南立規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濫用現象“釣魚執法”“以罰代管”“多頭檢查”等行政頑疾將被終結。作出這樣的規定,是為了讓行政機關在執法過程中杜絕“釣魚執法”,嚴禁行政機關設置“執法陷阱”,從而充分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建立規則解決了是否合法的困擾,而接下來的程序控制則為了確保行政機關的高效運轉。各國法治政府的實踐證明,加強對行政權力的程序控制,不僅能有效防止權力濫用,同時可以繼續保持行政機關的高效運作。而湖南出臺的改革,采取了實體法與程序法相結合的方式規范行政裁量權。
利用這種辦法,將行政裁量權程序控制分為外部程序控制和內部程序控制。其中外部程序包括回避制度、公開制度、告知制度、聽證制度、證據制度、期限制度和說明理由制度。而內部程序制度指的是行政機構內設機構之間辦理某一行政事務的職責分工和具體步驟、方式、時限等制度,包括行政機構的內部職責分工和內部行政程序。
建立規則之后的第四步為行政裁量基準制度,目的在于有效防范行政機關的恣意,保障行政裁量權的合理性。基準制度可以使行政機關依據立法者意圖以及比例原則等要求并結合執行經驗,按照裁量涉及的各種不同事實情節,將法律規范預先規定的裁量范圍加以細化,并設以相對固定的具體判斷標準。這一制度的建立,能夠明確執法的標準,細化法律條文,使相關行政管理行為具有可預測性,并為司法審查提供有益的參考。
五項制度的最后一步是裁量權案例指導制度,其遵循的先例是英美法系,此舉借鑒了國外的先進經驗。其基本含義為,在以前判決中的法律原則對以后同類案件有約束力,具體表現為上級法院的判決對下級法院的案件、同級法院以前的判決對以后的案件有約束力。
案例指導制度的公正公平性表現即為同等情況同樣處理,因此,行政機關理應遵循自己先前做出的行政決定。而之前,我國行政法領域尚未確立先例原則,也沒有仿照英美法系建立案例指導制度。為解決實踐中“同案不同罰”、“同事不同辦”等行政不公現象,湖南所推行的辦法積極探索,大膽創新,確立了這一案例指導制度,也是改革的巨大亮點。
規范行政裁量權《行政程序規定》的助推器
湖南省政府發布了《規范行政裁量權辦法》,這雖然只是一部地方規章,卻引起了國內外輿論的密切關注。人們注意到,兩年之前,也是在湖南,省政府出臺了中國第一個地方性行政程序規定,它在我國《行政程序法》由于各種利益阻撓而千呼萬喚難出來的社會背景下勇猛破殼,堪稱經典。
這部規定以“公民享有更多程序權利,政府承擔更多權利義務”為立法思路,目的在于依法行政,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外界普遍認為,該規定強化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在本質上是對政府公權力的約束,并由此提高政府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與公信力。
以“程序正當”的要求為例,實踐中由于缺乏統一的行政程序法,近年來包括上海的“釣魚執法”事件,受到公眾普遍質疑。輿論認為,很大原因在于沒有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對非法證據予以排除。此外,學術界也認為,各類腐敗案件頻發,與正當法律程序的缺失密切相關。
北京大學法學院姜明安教授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局長鄭筱萸受賄案為例指出,在近10年的時間內,鄭利用職務便利,為藥企在藥品、醫療器械審批謀取利益,實質上是與正當法律程序缺位相關。姜明安在不同場合指出,如果這些審批、許可的項目必須程序公開,經過聽證或者論證,聽取相對人(其他申請的藥企)的意見,而一旦項目與鄭筱萸有利害關系時,他必須回避,則如此嚴重的腐敗案或可避免。
湖南省首開全國先河,全方位推進行政裁量權規范改革,主動為自己的權力設限,標志著湖南在推進法治政府上邁出了新步伐,意義重大。
正如專家學者和觀察家們所認識到的那樣,《湖南省規范行政裁量權辦法》,和此前已經順利實施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相結合,構成了湖南省地方各級政府體系自我規范、自我約束、自我加壓、依法行政的兩座基石。以它們為標志,一個權力清晰、程序規范、行事透明、監督有力的地方政府展現在面前。
在這個意義上,《湖南省規范行政裁量權辦法》正是《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的一個配套性規定。因為隨著現代社會經濟和技術的迅速發展,政府組織調整社會生活的功能和權限不斷擴大,行政機關享有的自由裁量權也隨之增加。甚至可以說,現代行政主要表現為“自由裁量”行政。而《湖南省規范行政裁量權辦法》正是與《湖南省規范性文件管理辦法》和《湖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辦法》一起,成為對《行政程序規定》起支架性作用的三部重要政府規章。
三位一體模式的湖南行政改革的最大的亮點,是改革通過各種配套規章予以具體規定,并環環相扣。在序上設卡,從源頭上收權,行政裁量權的自由空間壓縮到了最低,既保證了依法行政,又體現了一視同仁,公平合理。
湖南之所以能率先走一步,妙招頻出,正是政府和主要領導的高度重視,敢于“縛住自己的手腳”,主動為自己的權力設限。首次“吃螃蟹”的湖南省,將自由裁量權納入統一、法治的軌道,為全國規范容易被濫用的行政裁量權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