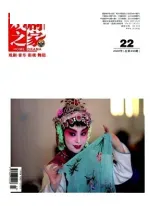淺談中國民間舞之現代走向
□王 靚
輝煌的中國歷史文明中,舞蹈作為物質文明的反映形式,依其較為獨立的方式,以各種地域性、民族性、時代性比較強的禮儀、風俗等慶典、娛樂活動為載體,沿襲了幾千年,乃至最終走出民間,邁向藝術殿堂,沖出“廣場”奔上舞臺。
縱觀其發展史,舞蹈自產出之日起,無論素材的來源或表現的形式,都源于當時當地的生產、生活等物質活動。這里已初現其地域性、民族性之端倪,更道出了民間舞蹈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從來都是客觀存在的物質文明史的藝術化了的必然反應,這一根本特征。
民間舞每發展一步,其原動力都是物質社會的不斷發展,都源于人們審美欲望的不斷增長和審美層次的不斷提高。從某種角度講“社會需要”恰恰具有極強的時代性。
以此觀點看中國民間舞蹈,我們就會得出結論:時代性是其生存發展必須依賴和具備的根本特性。
任何一種形式的藝術都不是給古人或未來人欣賞的,而是為活著的人服務的。也就是說,在研究一種藝術的走向時,不能僅僅考慮到它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其時代特色所延伸出來的親近性。
中國民間舞從廣場進化到舞臺,的確是一種質的發展,但是這只是與過去的歷史相對而言。看看今日的中國舞臺,民間舞雖然仍占據著舞蹈領域的主導地位,但已開始出現危機,當它獨立呈現于舞臺上、銀屏時觀眾便出現眾多的離座現象,使得民間舞不得不依賴于其它藝術形式而茍存。究其原因,一個時期以來,民間舞或停留在展示風土人情,或拘泥于無主題的肢體美的展示,或服從于簡單的、淺層次的唱喜歌的需要上。這些在一定時期內、一定的地方曾經滿足過人們的審美需要。而當今社會的飛速發展所引起的觀念變遷和人們文化層次、審美層次的提高,客觀上已經提出民間舞蹈必須緊緊跟上時代腳步的要求,再繼續搞“翻版博物館”式的藝術將被拋棄。
那么,中國民間舞究竟如何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找到適合自身生存發展的道路?筆者認為,首先要解決的應該是編舞者的觀念問題。如今許多編舞者的所謂創作活動,還常常停留在對民族性、民間文化的挖掘、整理和再現上,其體驗生活,多流于對風土人情的體察上。應該說,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但僅僅停留再這一步上就顯得有些不適時了。所創作的舞蹈,“創”的內容就顯得少些,也很難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突破。
筆者愚見,一個能夠把握時代脈絡的編舞者,應該在現代意識的關照下去從事舞蹈創作活動。近年來,西方的現代舞流入我國,對傳統的舞者產生很大震撼。沖擊之下,有的盲目追隨,有的則斷然排斥,這樣的做法都不是科學的。每一種舞蹈(包括勁舞)的存在與發展都有其內在的合理性,編舞者應善于借鑒其它舞種之長為我所用。例如,現代舞長于表現人的內心情感,舞蹈有較強的啟迪性,能夠制造比較抽象、令人產生充分聯想的氛圍。這些恰恰是現代人渴望得到的一種超越形式的深刻思想美。而民間舞蹈在這方面往往是力不從心。如果能夠借鑒現代舞甚至芭蕾舞等舞種之長為我所用,那豈不是一種極好的改良。
所謂改良,還不僅僅是停留在以上所述的“軟件”上,包括對現代舞等在結構方式,服飾、道具的運用,舞蹈語匯甚至肢體訓練方面的借鑒。
當然,并不是說借鑒了其他種類舞蹈的長處,便具有了有時代性。關鍵的問題是,編舞者或舞蹈者要具備極強的現代意識,不斷地研究現代人的心理要求、審美趨向和樂于接受的最佳形式。而閉門造車,鉆到歷史中去“找寶”,顯然是越走路越窄。
談了這些后還必須指明,我們所談的借鑒和改良,并不是要全盤否定民間舞之本體而強調完全“外化”。我們在強調時代性的重要性的同時,還必須注意到,不論哪個時代的人,其審美意識都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征。失掉了這一點,也就失去了藝術存在的根基。而且,人們已經注意到,越是民族性強的東西就越是具有世界性。我們所借鑒的東西無論多么好,那只是民間舞借以發展、騰飛的階梯和工具,都是外部力量,最終要通過內因來發展路子。
在這方面,我們做了一些嘗試。如現代中國舞劇《夢姐》,其內容來自民間故事“王二姐思夫”。我們采用了東北民間秧歌舞蹈素材,借用了秧歌中的“手絹”舞動作的變化來表現主人公的各種心態變化。在創作中,時時把握現代人的審美需要。在結構上采用了意識流的結構方式,并大膽地運用寫意的手法去揭示主題。舞劇沖破了傳統戲劇式的敘事結構,發揮了舞蹈長于抒情的特點,把觀者帶入一個充滿感情色彩的思想境地,使其看到或者感受到了主人公王二姐與情郎心靈深處的對話所折射的具有現實意義的諸多啟示。舞劇演出后,受到國內外觀眾的普遍歡迎。
中國民間舞起源于民間,如今作為一種高級的藝術形式又要反過來服務民間。無論從舞蹈本身生存發展的需要,還是從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來看,都需要舞蹈工作者在牢牢地把握民族性、地域性甚至其商品性的同時,抓住其時代性。
社會生活的歷史是藝術的源泉,然而它并非藝術本身。藝術家在將生活升華為藝術的時候,切莫忘記其“產品”是否能適銷對路。
以上是筆者的幾許拙見,愿與同仁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