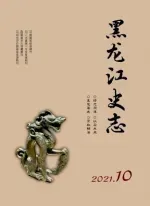哲學、藝術與人生——讀《福柯的生死愛欲》有感
湯燕芬
(杭州師范大學 浙江 杭州 310036)
一、福柯及其主要著作
福柯,即保羅—米歇爾·福柯,生于1926年10月15日,于1984年6月25日去世。作為20世紀法蘭西的尼采,福柯強調譜系學的研究,并認為其有三個領域:
1.有關我們自身與真理關系的歷史本體論,通過它,我們把自己當成知識主體。2.有關我們自身與權力領域關系的歷史主體論,通過它,我們把自己當成作用于他人的主體。3.有關論理學的歷史主體論,通過,它我們把自己當成道德代理人。在福柯的著作中《瘋癲與文明》強調以上三點,《臨床醫學的誕生》和《詞與物》主要強調第一點,《規訓與懲罰》著重強調第二點,《性史》則重強調第三點。
福柯的主要著作:福柯的一生(自上學以后)都與書本保持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在他強烈的求知欲下,在閱讀無數,讀書筆記亦是十分豐富,除此之外福柯主要有以下幾部著作:1954年出版的《精神疾病與人格》、1960年出版的《瘋癲與非理性:古典時期的瘋癲史》、1963年出版的《臨床醫學的誕生》《羅塞爾》、1966年出版的《詞與物》、1967年出版的《知識考古學》、1975年出版的《規訓與懲罰》、1976年出版的《知識的未來》,以及其后的《快感的享用》和未完成的《肉欲的告誡》共同組成了他的《性經驗史》
二、《福柯的生死愛欲》主要內容
對于福柯的認識,我以為自己是膚淺的,間接的,因而也是帶有極度主觀偏好的。因為到目前為止,我所接觸的福柯或福柯的作品都是出于他之手。原版文獻,一則看不懂,再則其實在罕見。就目前而言,詹姆斯·米勒的《福柯的生死愛欲》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權利的終結與福柯對話》是我閱讀的比較詳實的著作,對于福柯的感觸亦是深受其影響。《福柯的生死愛欲》一書大體上遵循了福柯的生命足跡,并且對福柯的大量作品做了詮釋,該書文字優美、內容豐富深刻,是對福柯的一生充滿想象力的大膽詮釋,而且將其對哲學的領悟、藝術的追尋自然穿插其間。
《福柯的生死愛欲》一書主要包括十一個篇章。第一章:作者之死。采用倒敘的手法,通過福柯死時所取得的成就,引起讀者閱讀的興趣。這一章將福柯生前的主要著作及各著作的主要思想進行了簡單介紹,同時也描述了福柯學說的影響。1968年后,福柯的哲學在整個世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德國和大不列顛,在日本和巴西,在美國都被大學師生奉為圭臬,他的聲望在死后一直呈上升勢頭。第二章:等待戈多。主要講述了福柯思想的淵源,包括哲學家薩特、黑格爾、馬克思、海德格爾等。等待戈多這一戲劇,使得福柯不得不去設計他自己的“合適出路”。為第三章“袒露的心”做了鋪墊,在第三章中福柯像一顆在沙粒的磨礪作用下成長的珍珠一樣,他的終身計劃開始形成了。該章提及了許多福柯的特殊生活經歷,使得一個豐富的人物形象和他錯綜復雜的內心思想躍然紙上。第四章主要面寫的是福柯的著作《瘋癲與文明》的主要思想以及該書在當時的影響。從本文的第五章開始,福柯的思想再次進入了“迷宮”,他對自身的定位與認識又有了新的方向,直到文章的第九章,福柯再一次確定了思考的方向,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吶喊”。文章的第十章主要寫了福柯在生命后期改寫自我,這方面主要體現在思想的轉變上,同時也不乏由于當時福柯聲名鵲起,而使福柯關心的問題產生轉變的方面。文章的最后一章,則記敘了一些作者認為對福柯思想產生影響的事件,有利于我們完整的了解福柯及其思想。
《福柯的生死愛欲》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講述福柯一生的傳記,它更是一部關于哲學、藝術、人生三位一體的思想性著作。米勒先生為我們描繪了一個活躍、熾熱、無畏而閃亮的心靈——誠然,它或許帶有些許自我解構的意味,而且都太人性,但它永遠不會被詬病為陳腐、平庸、無名和幼稚。它談論性、瘋癲、死亡、哲學、尼采和艾滋等話題,可能或有一些令人震驚,但正是通過這些看似懸殊的元素,它構建出了福柯的愛欲人生。總的來說《福柯的生死愛欲》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生活豐富多彩、思想深邃奇異的福柯圖,有許多章節都耐人回味,令我為之著迷。
三、讀該書有感
新康德主義社會學家韋伯認為,理性化或合理性是現代性的基本特征,理性化表現在文化、社會和個人三個方面,海德格爾認為現代性的本質是“主體性行而上學”,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性”是一種新的社會知識和時代,它用新的模式和標準來取代中世紀已經分崩離析的模式和標準,從以上幾位學者對于現代性的理解,我們不難發現現代性所專注的是主體的、合理性的、真理性的、知識性的,而較之“相對”的后現代性則在尼采的“上帝已經死了”到福柯的“人也已經死了”的主體之死,到對統一性真理的批判否定到對現代科學、技術座架、規章、制度等的一系列沖撞、批判,正從眾多方面思考,顯現著“現代性”的弊端。
作為一名哲學家、學者,福柯的思想火花所呈現的后現代性是十分明顯的。
存在于現代性環境下,福柯所接受的傳統、守舊的思想,普瓦蒂埃的牢籠、父親的牢籠,在福柯年少時留下了如此深刻的痕跡。福柯試圖改變,他后來將自己的名字中的保羅舍棄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現代性的規則在生活中隨處可見,對于“瘋子”的緘默,對于“性”的壓抑,對于“理性”的崇拜,使得在思想上擁有極大批判的福柯的人生呈現出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縱橫交錯,一方面,他強調感受、體驗,這正是現代性藝術所追求的,一方面,他又感受、體驗“異質”關注的是“身邊”“日常”的現象而非現代性的抽象。正如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glor)和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指出的,一種“日常觀念”開始日益取代更抽象的概念作為關注道德的哲學關注的焦點。按照列斐伏爾的觀念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到康德,哲學傾向于回避對日常問題的思考認為日常問題是粗俗的,代表的是完美真理的反面。但是,隨著馬克思的出現以及堅持工作、勞動和生產性勞動對于理解人類處境具有重要意義。一種日常觀念開始日益在現代哲學思考中占有中心位置。而福柯在思想上不僅曾追隨過馬克思、康德之類,也深受尼采的影響。兩顆擁有巨大力量的智慧之星相互碰撞后出現一種“奇跡”。福柯在思想上也歷經了奇跡,他說,“就我而言,是貝克特的《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的首次演出使我實現了突破——那真是一場特別激動人心的演出。[1]福柯在重新思考一種倫理行為,這種倫理行為避免了工具的合理性或者功利主義的邏輯。[2]
福柯關注“瘋子”攻擊現代性的文化。他對瘋癲的話語分析表明,對于瘋癲而言的理性統治地位并非如理性自己所言是“自然的”和“理所當然的”,他對知識話語的考察,為我們揭示了作為現代認識型的產物的“人”的暫時性(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沙地上的一張臉。[3]他用考古學方法分析的“無主體”的話語實踐,展示了話語的自我實踐圖景;他對監獄的誕生歷程的分析,是對規訓權力如何借助話語力量逐漸控制思想的過程,他對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性經驗的話語分析,則試圖風格化的生存藝術,導向自我確證和自我控制的真正主體。[4]
縱觀福柯的著作,他所關注的都是那些與個體、自我切實相關的范疇,他討論瘋癲的話語,討論人,討論肉體、權力、意志和種族戰爭還有性等等。福柯在重新思考一種倫理行為,這種倫理行為避免了工具的合理性或者功利主義的邏輯。他曾經強調:“人們不必一定追求一致性,但是人們必定反對不一致性。”[5]他在關注瑣碎中創造或企圖創造著另一個世界。而作為藝術創造,他的來源亦是生活本身。精神領域的大風起于輕貧之夢,最小的種子往往能長出最大的果實,精神的東西是最原始的東西,比如接觸我們生存的自然界。而福柯正是在“體驗”著人——這一自然的產物。藝術源于敏感的心和鐵一樣的意志,無論以何種形式表現的藝術作品,都是在巨大的刺激之中,智慧之花是由痛苦澆灌出來的,他追尋美、追尋超脫“時間性”的普遍性。正如福柯的思想和行為一樣。藝術走在否定與表現的路上,走在追尋美的路上,而福柯亦試圖將自己的事業作成美的事業,就像毛澤東同志領導的革命事業一樣,追求著藝術效果(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福柯作為一個“體驗”者,正如他在體驗后所總結的《性史》一樣,他以全然到達了超脫性而提煉性之美于藝術性的程度。這一點可以從豪放派詩人李白的創作中十分明顯的顯現出來,每每當其酩酊大醉的時候他才能或卻能揮灑自如的創作出行云流水般的詩文。
福柯,與任何一個平凡的人一樣,經歷時光的磨練與消逝,最后消失在這個世界上。但,福柯,是不平凡的,雖然他的肉體早已灰飛湮滅了,但他的思想,他所研究的獨特而深刻的領域,他的精辟而犀利的觀點,他的豐富而深邃的著作,他的執著,直至今日仍然存在著并活躍著,不僅是對于現在,甚至是未來,仍然是我們關注的焦點,令我們及后人在此期間停留、驚嘆、感嘆。我曾靜靜地聆聽他的述說,聽他講那些瘋人,囚徒和性錯亂的故事,對于福柯,我懷著一顆敬畏之心,是平視,更是瞻仰。
人生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方程?換句話說,人生的意義何在?是像風一樣輕飄,還是像雨一樣淅瀝?是想登高一樣喜樂還是想沐浴陽光一樣快樂?我們要解答這樣的問題,一定是困惑而苦惱的。實際上整個生活的意義全在于自我的一種感受。每天活出自己的感受,你就能得到五個字——“充實即快樂”。
為了果實的成熟,花瓣必須要凋謝,為了新樹的出生,果實必須凋落,嬰孩必須離開母親的胎房,才能在大自然的懷抱里獲得身心更進一步發展。靈魂必須走出自我的牢籠,才能獲得更充實的生命,而在各種不同的親和關系中,形成一種更大的形體,最后,當他心神交瘁,百感消馳之時,他才能安然地撒手西歸,我們的靈魂在歷經憂患之后,才能離開他的狹隘生活。而走向宇宙生命。
人生具有兩方面的完美性——存在的完美性以及行動的完美性。我們所要關切的其實是個人善行的內在真實性。外在成果雖然能功澤一世,但是具有無窮價值的都是人格的內在完美性,而這種價值乃是精神上的自由。善意意味著精神從自我中心的解脫;在善意中,我們才能與宇宙人道精神合二為一。它的價值不僅在于造福自己的同類,更在于我們實現自身的真理性,在于顯示人不象動物個體情欲與嗜欲限制,在于無限完善的精神實現。善意正如愛一樣,是自我在人群世界中的自由實現。我們對真理的體現,不能出于世俗的責任要求,而必須出自我們內在的誠意。須知,真理的最終實現實際孕于精神實現,孕于我們與永恒的結合及完美的和諧。否則的話,機械的完美性遠比精神的完美性更為高尚。為了實現個人與宇宙的和諧,個人必須過著一種完美的生活、藝術的生活。正如福柯一樣,我們必須學會內在的自我靈活的存在于現實的痛苦與快樂中。我們需要學習、總結、提煉、體驗和感受。
我覺得完美與藝術的人生的準則:
一、經歷過痛苦,并在無論是輕弱或是刻骨的痛苦中感受孕于其中的那份快樂;
二、經歷過愛,并在愛的過程中,享受尋找中的迷茫,等待中的焦灼;
三、經歷過失敗,并在注定或無意的失敗中感受著成功與超越;
四、經歷過追求,并在艱辛專注的追求中超越所謂的實用性與功利性;
五、經歷過渺小,并在渺小中感到不滿與渴望,在渴望中追求永恒中的意義;
六、經歷過罪與丑,并在罪惡與丑陋中追求心靈上的凈化,從感官上追求美與藝術,消除不安而進入更大的不安;
七、認識人生的有限性,以升級的游戲驅趕無聊、空虛,追逐永恒;
八、學會感受,在回首與愛中親證你的人生;
九、學會不畏懼死亡,在尋找無限中超越出有限,在死亡中感受、接觸無限與邊界;
十、達到瘋狂,從追求茫然、無所事從的道路中步入到追尋無限的瘋狂之路;
十一、歸于寧靜,將無限、有限、生活、欲望,一切的一切歸于寧靜,經歷完美的藝術人生之路。
[1][美]詹姆斯·米勒著 高毅譯《福柯的生死愛欲》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75頁
[2]福柯《政治學和倫理學:一次訪談》第379頁
[3]福柯語
[4]吳猛和新風著《文化權力的終結與福柯對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第3頁
[5]《政治學和倫理學:一次訪談》福柯第3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