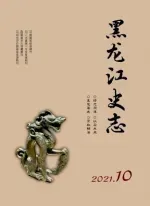“缶”的真意詮解
夏四海
(安徽大學 安徽 合肥 230039)
2008年8月8日晚上8點,當奧林匹克的圣火第一次古老的中華大地點燃時,在世人震撼于悠久文明的無窮韻味時,而一首氣勢恢宏的“擊缶而歌”帶著華夏禮樂的傳承,帶著炎黃子孫百年的夢想和期盼,奏響了開幕式的序曲時,關于“缶”便深深地印入了世人的腦海之中。
缶的傳統分類
“缶”乃何物?“缶”字怎解?從《說文解字》到《辭海》皆有不同注解,總結之,大概分為兩類:一類作量詞,一類作名詞。
首先“缶”作量詞時,它是一種古容量單位,約等于十六斗,又一說三十二斗。“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鐘”。還有“缶米”(即一缶的米,即十六斗米)之謂。
其次“,缶”作名詞時,有好幾種定義,略分之,如下:
一、象形。甲骨文字形。上面是“午”字,即“杵”。下面是“缶”的本體。“杵”是棒子,可用來制坯。“缶”又是秦樂器。“杵”可以敲擊成曲。(本義:瓦器,圓腹小口,用以盛酒漿等。)
二、盛酒漿的瓦器。大腹小口,有蓋。也有銅制的。“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象形。”。“盎謂之缶。”
三、樂器:“缶”亦作“缻”,按《說文解字》解釋:“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多次提到擊缶。如李斯《諫逐客令》有“擊甕叩缶、彈箏博髀”句。其義為,秦國飲宴時,貴族士大夫們往往在喝到半酣時,以擊瓦缶,拍大腿來打拍子而歌。所以“,擊甕叩缶、彈箏博髀”為說明秦人音樂古樸,沒有中原音樂先進。
缶,這種樂器,原來是古代一種陶器,類似瓦罐,形狀很像一個小缸或缽,是古代盛水或酒的器皿。圓腹,有蓋,肩上有環耳;也有方形的。盛行于春秋戰國。器身銘文稱為“缶”的,有春秋時期的“欒書缶”和安徽壽縣、湖北宜城出土的“蔡侯缶”。這種酒器能夠成為樂器是由于人們在盛大的宴會中,喝到興致處,便一邊敲打著盛滿酒的酒器,一邊大聲吟唱,頗像現代的卡拉,所以缶就演化成為土類樂器中的一種。《易?離》上有“不鼓缶而歌”句。然陶器易碎,今已不見,現存多為青銅器。關于中國古代八音和“擊缶”典故后文有敘述,此處不再贅述。
四、汲水的瓦器。《左傳·襄公九年》上有“具綆缶,備水器。”《易·比》中有“有孚盈缶”句,鄭玄注曰“:缶,汲器也。”
五、盛酒器。也用于盛流質食物,源自同形陶器。這里的缶是指尊缶,而不是浴缶。古人用缶多是陶質,考古發掘發現,只有較大的少數墓中才有青銅缶。《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節歌,象形。”可見,青銅缶的祖型當是陶器。
六、盛食物或飲料的器皿。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銅冰鑒缶,即曾侯乙銅鑒缶。此缶有夾層,夾層里面放冰,缶里面放食物飲料,這就是古代的冷藏設備。
總之,在我國歷史上,關于缶的記載并不是非常多,且用法與喻義大同小異,《詩經·陳風·宛丘》中“坎其擊缶,宛丘之道”乃是刺幽公“威儀無法”;而《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記載藺相如挾持秦王擊缶,更是明顯的羞辱。漢代以后擊缶或有之,但上層社會終是不屑。《淮南子》云:“夫窮鄉之社,扣甕、鼓缶,相和而歌,自以為樂,常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始知夫甕缶之足羞也。”其意乃彰。其中最有名的《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描述的原文如下: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于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這里秦王所擊的缶,就是窯字里面缶,它是古代的一種陶器,用來盛酒的。春秋戰國時候曾經拿它當作樂器。從此處亦可看出秦人不善器樂,難為高雅正統之聲,只會擊缶為娛。
另有,李斯在《諫逐客書》中提到:“夫擊甕叩缶,彈箏博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可見,在秦始皇那個年代,秦國風俗上已經認為擊甕叩缶俗氣了些,上不得臺面——不得不提的就是,當是箏也是很俗氣的東西,也是被淘汰的東西。
缶的傳統意義
我國古代“八音分類法”,按材質質地將樂器分類為所謂金、石、土、革、絲、竹、匏、木等“八音”。土就是陶類樂器,有塤、陶笛、陶鼓等,缶甚至都不能正式入其類,可見地位之低。長期以來,“擊缶”或者說“鼓盆”,一直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兩個主要涵義:一是下層人民最下等的娛樂,二是葬禮場合表示悲傷的禮節。
從第一個意思說,據《墨子·三辯》中記載:“昔諸侯倦于聽治,息于鐘鼓之樂;士大夫倦于聽治,息于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殮冬藏,息于瓴缶之樂。”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當時森嚴的等級制度,“擊缶”“鼓盆”只是出于社會底層的農民的娛樂。到漢代,恒寬
《鹽鐵論·散不足》載:“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
《淮南子·精神訓》載:“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后來隨著時代的發展,擊缶這種娛樂性是逐漸式微,大概只是叫花子要飯時的表演形式——敲缽,還能略見當年下層社會人民擊缶之遺韻了。
從第二個意思說,《周易·離》九三爻辭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耄之嗟,兇。”
意思是說,在太陽西沉的光輝下,不叩擊瓦器而歌唱,那么垂暮老人會嗟嘆的。這是一個兇兆。這反映了當時一個民間習俗:對即將去世的老人,人們要鼓缶歌唱,以安撫老人,祝愿將死者順風順路。戰國時的莊子,其妻死,鼓盆而歌,則進一步將鼓盆走向喪禮。這一習俗一直流傳下來,北齊顏子推在《顏氏家訓勉學》中說:“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宋代岳珂在《寶真齋法書贊》載:“聞有鼓盆之戚,不易派遣。”在元、明、清的文學作品中,“鼓盆歌”、“鼓盆悲”、“鼓盆之戚”之說,更為常見。這一習俗流傳至今,即今天許多農村的喪葬儀式中,那個孝子出殯時的摔瓦盆。
由于缶這個樂器具有上述兩個特點,因此它在中國歷史中扮演了很多政治角色,一些膾炙人口的也因此而流傳至今,其中以戰國時的“澠池會”最為有名,這個故事的政治要害是秦王強迫趙王為其彈瑟,并命史官記錄下來以辱趙王,藺相如遂以血濺五步逼趙王擊缶,相應地使秦王的身份更降一級,以回擊趙王鼓瑟辱之,取得政治上所謂的勝利。
關于缶的真正屬類
再說“八音”。所謂金、石、土、革、絲、竹、匏、木等“八音”中,“金”是青銅鐘、鐸之屬,“石”是磬,“土”是塤、缶一類,“革”是鼓之屬,“絲”為琴、瑟,“竹”為篪、簫管,“匏”指笙、竽,“木“為柷、敔。按這個分類,以蒙皮發音的“缶陣”之缶,是為“革”屬之鼓,而不是“土”屬之缶,進而言之,不僅在中國傳統的樂器分類法中“缶陣”之“缶”不屬于樂器之缶,在現代樂器分類法中,它與樂器之缶也有本質差異。
現代樂器分類法(薩克斯——霍恩博斯特爾分類法)是根據樂器的聲學振動體特征分成“弦鳴樂器”(Chordophones)、“氣鳴樂器”(Aerophones)、“體鳴樂器”(Idiophones)、“膜鳴樂器”(Membranophones)和“電鳴樂器”(Electronphones)五類,完全覆蓋了世界上任何樂器種類。樂器之缶和青銅鐘的發音原理都屬于體鳴樂器,“缶陣”之“缶”和鼓一樣顯然屬于膜鳴樂器。
最后說一下缶的演奏場合。先秦時期樂器的定型有漫長的過程。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陶缶、陶罐、陶盆因燒制溫度低,打擊時聲音沉悶容易破損,只有在新石器時代后期硬陶和原始瓷出現之后,才有可能出現陶缶一類打擊樂器。擊缶而歌目的是節奏,而不在于缶音。隨著體鳴樂器的鐘、膜鳴樂器的鼓出現,音響、音質始終有問題的缶就不可能像絲竹、金石、木匏類樂器那樣成為主流樂器,進入中原的禮樂序列。陶缶本為生活用品的大路貨,飯飽酒酣之余擊缶而歌多是率性而為,就像在食堂敲盤子打碗發泄情緒一樣,上不了臺面,其儀態雅俗、器物完損、聲音好壞都是無所謂的事情。因此,先秦時期的缶只是偶然作為樂器,不用于禮樂場合。
結語
喧囂過后,不禁捫心自問:“哪里有過方形的缶?”“哪里有過蒙皮的缶?”“哪里有過迎客的缶?”有人提出“批評”沒有被重視;更有人“解密”曰“缶陣”乃是張氏團隊“創意”之作,是新產品,是擺樣子,露一手罷了。可惜我都沒機會拜讀,實為憾事。這里請允許我再啰嗦幾句。
(一)“缶”,古作缻(音同),從字形上就知道它是陶土燒制而成的瓦器。各種字典上都說是小口大腹,用以盛酒漿的容器。最好的說明是李商隱《行次西郊作》詩中一句:“濁酒盈瓦缶。”
(二)因為是盛酒用的,所以飯飽酒酣之余,拿缶當樂器使用了。《漢書·楊惲傳》上說:“酒后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拊缶而歌,不是“雅樂”,也就是說不是標準音樂。在朝會宴享的正式場面上是看不見的。
(三)陶制的否,很早就有了。用作樂器,最早見于《呂氏春秋·古樂》的記載:“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大章》是堯部族的圖騰樂舞,缶是伴奏樂器,不是主樂。“百獸起舞”是古人夸大之辭,不可引為經典。
(四)“擊缶”在秦以前用于祭祀神靈,不用于迎賓。《禮記?樂記》引《詩經》云:“肅雍和鳴,先祖是明。”《史記?樂書》云:“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周易?豫?象》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史書告訴我們,古樂不是為了人自己的娛樂,而是感召祖考,和悅神靈,所以不適用于體育盛會。
(五)張氏團隊對打擊樂器“缶”,該怎么打,該怎么擊,都下了功夫,收到成效。可事實上,古樂“缶”是不打不擊的,而是用手掌撫,用手指叩的。更重要的是:“缶”不論是瓦是青銅,只要蒙上“皮”,就不是“缶”。八音有別,豈可混同?
(六)作為樂器的“缶”,不知道在什么時候,也不知道為什么原因,慢慢地演變成禮儀上用的祭器了!不但改變了制作原料,也改變了功能性質,失去了“樂”的作用。據猜測,是周末,禮與樂分家,歌與舞獨立,新石器時代的產品隨著社會的進步,就慢慢的變成青銅器時代的產品,體態模型都變了。《辭海》語詞分冊(下)2023頁上的圖“青銅缶”,不是“缻”。正如上文中所引《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上說的“擊缶”和李斯《諫逐客書》上說的“擊甕扣缶”等文章都充分說明,就是在秦政之初,擊缶已經不吃香了,缶樂已在淘汰消失之中。
(七)在三百零五篇的《詩經》中,寫到“擊缶”的只有《陳風·宛丘》一篇。這說明在周朝中葉,缶樂還有存在,可它不用于“迎客”之時。《宛丘》有三段:第一段講跳舞,第二段講擊鼓,第三段講擊缶。鼓在先,缶在后。鼓聲迎客,缶聲節歌止樂,要送客上路了。(《說文解字》有注:“瓦缶,秦人鼓之以節歌。”)所以《詩》云:“坎其擊缶,宛丘之道。”這么看來,“擊缶”是不適用于開幕式的。這么看來,“缶陣”不就是“缶樂”之否嗎?綜上所述,竊以為:無論是“誤讀”,還是新產品,“擊缶”并不太適合在百年奧運之上作為中華優秀文明介紹給外國朋友展現大國風范。歷史文化畢竟不是拍電影。
本文非考古角度考證“缶陣”之缶的辨真定名或淵源歷史,只是在文獻意義上討論“缶陣”之缶是對古代樂器之缶的錯用,僅希望借以反思今天人們繼承傳統文化的路徑和圖景。更無意去評價什么專家、權威之文化演變,及對傳統文化的繼承上“濡化”(enculturation)的局限性研究。所謂“文化”、所謂“傳統”、所謂“禮樂”,娛樂大眾,大家樂樂就是了。
[1]《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縮印版)第2107頁
[2]《說文解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頁
[3]《左傳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95頁
[4]《詩經全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頁
[5]《淮南子譯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頁
[6]《史記》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492頁
[7]《墨子白話今譯》中國書店1995年版第25頁
[8]《鹽鐵論譯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頁
[9]《周易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頁
[10]《漢書》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665頁
[11]《呂氏春秋譯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頁
[12]《詩經全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27頁
[13]《史記》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第134頁
[14]《周易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