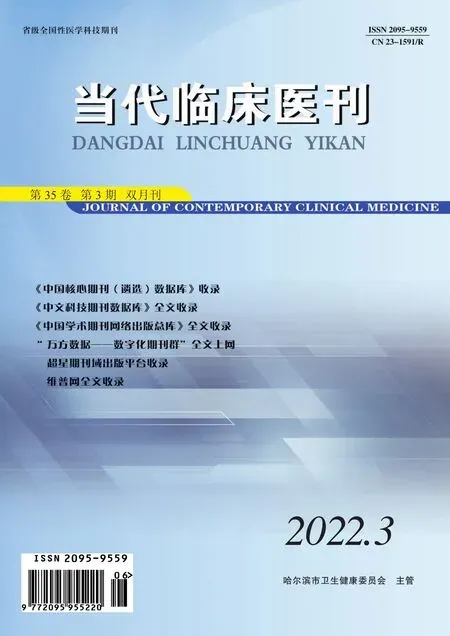早期少量飲水+基本口腔護(hù)理對全麻氣管插管病人術(shù)后不同時間段咽喉紅腫疼痛的影響
馬千里 王宜庭
(江蘇大學(xué)附屬醫(yī)院,江蘇 鎮(zhèn)江 212000)
氣管插管全身麻醉患者在術(shù)后一般需禁食6h,其原因在于麻醉藥物和手術(shù)刺激會影響患者胃腸道功能,如果早期飲水可能會出現(xiàn)明顯的胃腸道不良反應(yīng),甚至引起呼吸困難和肺部炎癥[1]。但圍術(shù)期長期禁飲也會帶來唇裂、口干等問題,會降低患者舒適度,影響其身體狀態(tài)的恢復(fù)[2]。近些年來,隨著醫(yī)療技術(shù)不斷進(jìn)步,氣管插管全身麻醉對患者胃腸道的影響也在逐步減小。因此,許多醫(yī)護(hù)人員都主張?jiān)诨颊咝g(shù)后初期給予少量飲水。本研究選取我院行氣管插管全身麻醉的手術(shù)患者100例為研究對象,就早期少量飲水聯(lián)合基本口腔護(hù)理對其術(shù)后咽喉紅腫疼痛和胃腸道功能的影響進(jìn)行具體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0年1月至12月在我院行氣管插管全身麻醉的手術(shù)患者100例為研究對象,隨機(jī)分為試驗(yàn)組(50例)與對照組(50例)。試驗(yàn)組男20例,女30例;年齡20~66歲,均值(44.21±3.66)歲;體重44~78kg,平均(52.23±3.41)kg;疾病類型:腹股溝疝18例,剖宮產(chǎn)10例,骨折14例,關(guān)節(jié)置換8例。對照組男22例,女28例;年齡22~67歲,均值(44.61±3.80)歲;體重42~81kg,平均(53.08±3.38)kg;疾病類型:腹股溝疝14例,剖宮產(chǎn)10例,骨折14例,關(guān)節(jié)置換12例。兩組患者上述基礎(chǔ)資料比較P>0.05,試驗(yàn)可行。納入標(biāo)準(zhǔn):入選病例均采取氣管插管全身麻醉,拔管時意識已經(jīng)恢復(fù),ASA分級為Ⅰ~Ⅲ級,患者自愿參與本研究,排除標(biāo)準(zhǔn):既往有消化道、口咽部手術(shù)史,且術(shù)后需長時間禁飲者;合并嚴(yán)重胃腸道疾病、吞咽功能障礙、溝通障礙、精神異常者;全麻誘導(dǎo)時出現(xiàn)插管困難、連續(xù)插管2次意識、插管時間≥6h者。本研究得到我院醫(yī)學(xué)倫理委員會的批準(zhǔn)。
1.2 方法 對照組采取基本口腔護(hù)理。術(shù)后指導(dǎo)患者選取合適的體位,為其清理口腔內(nèi)分泌物和痰液,定時用棉簽清潔口腔,并禁食禁飲6h。試驗(yàn)組在對照組基礎(chǔ)上于術(shù)后清醒狀態(tài)下給予早期少量飲水。在確認(rèn)患者無嘔吐情況后,以5mL無菌注射器向患者口腔緩慢注入38℃~40℃溫開水,注入過程中需觀察患者反應(yīng),如出現(xiàn)異常情況需停止注入;每半小時飲水5mL,如患者術(shù)后6h時仍無嘔吐現(xiàn)象,則可根據(jù)其需求給予適量飲水。
1.3 觀察指標(biāo) 比較兩組患者術(shù)后不同時間段咽喉紅腫疼痛發(fā)生率、術(shù)后胃腸道功能恢復(fù)情況(首次排氣時間、腸鳴音恢復(fù)時間、首次排便時間)、胃腸道不良反應(yīng)(惡心嘔吐、腹脹、誤吸等)發(fā)生率。
1.4 統(tǒng)計(jì)學(xué)方法 以SPSS19.0處理試驗(yàn)數(shù)據(jù),分別以χ2檢驗(yàn)和t檢驗(yàn)分析同類計(jì)數(shù)資料[n(%)]與計(jì)量資料(±s)的差異,當(dāng)P<0.05時,表示組間差異顯著。
2 結(jié)果
2.1 比較兩組患者術(shù)后咽喉部紅腫、疼痛發(fā)生率 試驗(yàn)組患者術(shù)后2h、12h、24h咽喉部紅腫發(fā)生率和疼痛發(fā)生率均顯著低于對照組,組間比較P<0.05。見表1

表1 比較兩組患者術(shù)后咽喉部紅腫、疼痛發(fā)生率[n(%)]
2.2 比較兩組患者術(shù)后胃腸道功能恢復(fù)情況 試驗(yàn)組、對照組患者術(shù)后首次排氣時間分別為(20.23±3.25)h、(24.88±4.20)h,t=6.191,P=0.000;腸鳴音恢復(fù)時間分別為(17.52±4.11)h、(22.88±4.52)h,t=6.204,P=0.000;首次排便時間分別為(46.65±10.02)h、(55.01±11.96)h,t=3.789,P=0.010。試驗(yàn)組均優(yōu)于對照組;P<0.05。
2.3 比較兩組患者胃腸道不良反應(yīng)發(fā)生率 試驗(yàn)組患者胃腸道不良反應(yīng)發(fā)生率為12.00%(6/50),其中:惡心嘔吐2例,腹脹2例,誤吸2例;對照組患者胃腸道不良反應(yīng)發(fā)生率為16.00%(8/50),其中:惡心嘔吐4例、腹脹2例、誤吸2例。組間比較χ2=0.166,P=0.684。
3 討論
手術(shù)患者已成為治療多種重大疾病的常用方法,而氣管插管全身麻醉為手術(shù)患者的常用麻醉方法,全身麻醉雖然有較好的麻醉效果,但也存在諸多問題。傳統(tǒng)理念認(rèn)為氣管插管全身麻醉患者術(shù)后需禁食禁飲一段時間,而臨床觀察發(fā)現(xiàn)禁食禁飲會引起咽喉紅腫疼痛現(xiàn)象。近些年來,隨著醫(yī)療技術(shù)不斷發(fā)展,人們思想觀念也在不斷更新,許多臨床實(shí)踐都證實(shí)對氣管插管全身麻醉患者在術(shù)后可給予少量飲水,少量飲水有助于降低患者咽喉紅腫疼痛發(fā)生率,促進(jìn)其胃腸道功能的恢復(fù),且不會引起明顯的胃腸道不良反應(yīng)[3]。氣管插管全身麻醉患者術(shù)后早期給予少量飲水,既符合保障患者自身健康的需要,也符合快速康復(fù)外科理念,能顯著提升患者術(shù)后舒適度,此干預(yù)方式得到眾多患者的認(rèn)可。諸多研究認(rèn)為,全麻患者術(shù)后早期飲水少量有助于減輕其口干、口腔異味等不適癥狀,能有效浸濕其咽喉部,刺激唾液的分泌,預(yù)防口咽部紅腫疼痛,還可抑制口腔內(nèi)細(xì)菌繁殖。代芳霞[4]的研究認(rèn)為,氣管插管全身麻醉患者在術(shù)后早期給予少量飲水非常有必要,而做好口腔護(hù)理也有助于保障其身心健康,在臨床中要高度關(guān)注對此類患者的護(hù)理服務(wù)。本研究結(jié)果顯示,早期少量飲水聯(lián)合基本口腔護(hù)理有助于降低全麻氣管插管病人術(shù)后不同時間段咽喉紅腫疼痛發(fā)生率,縮短其術(shù)后排氣時間、腸鳴音恢復(fù)時間、排便時間,且以上指標(biāo)均優(yōu)于單用基本口腔護(hù)理者(統(tǒng)計(jì)學(xué)分析顯示P<0.05);兩組患者不良反應(yīng)發(fā)生率均比較低(統(tǒng)計(jì)學(xué)分析顯示P>0.05)。與倪益益等[5]的研究結(jié)論與此相似。
經(jīng)以上分析可見,早期少量飲水聯(lián)合基本口腔護(hù)理對全麻氣管插管病人具有良好的應(yīng)用效果,此干預(yù)方式值得借鑒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