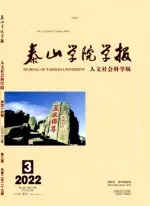趙沛霖《詩經》研究述評
林祥征
(泰山學院漢語言文學院山東泰安 271021)
趙沛霖(1938-),中國詩經學會副會長、原天津社科院文學所所長。有關《詩經》的專著有《興的源起——歷史積淀與詩歌藝術》(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詩經研究反思》(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20世紀詩經研究史》(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6年)。另有《八代三朝詩新選》、《追尋祖先的起源——漫話圖騰》、《屈賦研究論衡》、《先秦神話史論》等。他是當代先秦文學研究大家,《詩經》研究的成績更為卓著。21世紀《詩經》未來的發展方向在哪里?人們正在摸索與探討,趙氏的研究可提供有益的經驗。遺憾的是,當代學界“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對他的評論很少,形成《詩經》研究的一個盲點,本文希望對這種缺憾有所彌補。
一、對《詩經》學史建構模式的超越
具有一千多年歷史的《詩經》學進入 20世紀,實現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走上了現代《詩經》學的歷史新階段,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也存在著不足與問題。面對 20世紀《詩經》研究的反思與總結,就成為學界的重要課題,同時也是 21世紀《詩經》學的迫切要求。趙氏出于學術的責任感,及時推出《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20世紀詩經研究史》(以下簡稱《思潮與詩經》),率先從史的角度對 20世紀《詩經》研究進行全面科學地總結:該書由 1.緒論 2.《詩經》學的傳統與轉型3.疑古辨偽思潮與《詩經》研究 4.唯物史觀與《詩經》研究 5.極“左”思潮干擾下的《詩經》研究 6.文化意識與《詩經》研究 7.《詩經》學術史的勃興8.文化人類學與《詩經》研究 9.20世紀考古發現與《詩經》研究 10.現代學術意識與《詩經》傳注訓詁 11.大眾化意識與《詩經》白話文翻譯 12.開放意識與《詩經》的海內外學術交流 13.現代《詩經》學的學科建設等專題組成。英國作家福斯特有篇小說叫《帶風景的房間》,13個專題猶如 13個“帶風景的房間”,從中可以窺見 20世紀《詩經》學的不同的“景觀”及其發展脈絡,同時也可以看到對《詩經》學史建構模式的超越。
所謂傳統學術史的建構模式也稱“列傳式”建構模式,它以學者為基本單元,以學者的生平簡介,加論著分析評論為研究重點,以學者及其論著的時間順序排列形成學術史的歷程,并通過不同時代,不同學者學術觀點之間的淵源關系來梳理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由于這種模式如同古代史書中記敘人物行跡的列傳,因而可稱為“列傳式”的學術史建構模式。從現存學術史看,不論是古代、近代、還是現代,不論是研究對象、內容、性質和特征的不同,通通采用這種模式,導致研究模式的僵化,而且很難反映 20世紀《詩經》研究的特殊路程。20世紀的《詩經》學與傳統《詩經》學有著顯著的不同的特點,即它與時代學術文化思潮的聯系更加密切,我國現代歷史上出現的重要的學術文化思潮總是很快地被《詩經》學所采納,并在新的研究成果中表現出來,《詩經》學成為 20世紀古典文學研究中一個最為開放最為活躍的學科。趙氏正是根據這個新特點,在學術史的建構模式上采用新的開放的模式,與傳統模式區別開來。它在時代學術文化思潮的大視野下,把握《詩經》學在現代條件下的嬗變過程。“列傳式”模式所寫的只是一個個學者,即一個個的點。由點到點的跳躍的歷史難以連點成線,猶如詞條的解釋或內容提要,難以清理復雜的學術史的發展脈絡和內在理路。趙氏從學術傳統與時代學術文化思潮“對話”的視角,把握學術史的發展,可以抓住學術史的發展動力。例如 20世紀《詩經》研究的重擔為何落在顧頡剛為首的歷史家的肩上?離開當時的“疑古辨偽”思潮講不清;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詩經》研究造成數千年研究史上空前未有的學術墮落,正是由于極“左”思潮的嚴重干擾所造成的惡果。20世紀后期的《詩經》“文化熱”也與改革開放的“文化意識”有直接關系。唐人劉知幾論寫史要有“三才”,即史才、史學、史識。而“史識”是史書的靈魂,沒有靈魂只能是一堆材料的堆砌。趙氏正是憑借其“史識”完成其學術史建構的超越的。
如果說《思潮與詩經》是一部反映 20世紀的《詩經》學史,那么《詩經研究反思》則是一部從先秦到現代的《詩經》學史,論述自漢代至 20世紀80年代的《詩經》學術進程,論述各家對《詩經》各類作品(如祭祀詩、宴飲詩、史詩、農事詩、戰爭詩、怨刺詩和情詩等)和基本問題(如《詩經》分類,詩樂關系、《詩序》的作者、比興及藝術成就等)的觀點和見解,追蹤學術發展脈絡,評斷問題爭端,力求為《詩經》研究找出具有時代高度的新起點。這部對《詩經》進行文學分類基礎上的《詩經》文學學術史,從建構模式看,也與以學者為基點的“列傳式”學術史區別開來。英國著名哲學家培根談到學術史的重要時說,學術中如果沒有學術史,“那就如同波利菲穆 (獨眼巨怪)沒有眼睛一樣,這就缺乏那種最足以代表人類精神和生命的東西。”[1]趙氏的兩部《詩經》學術史也具有這樣的價值,他為《詩經》學帶來一雙雪亮的眼睛,更好地認識現實,更清楚地展望未來①。
二、《詩經》研究的深化與開拓
創新是學術的原動力、火車頭。在先秦文學研究領域,趙氏是一位富有創造力的學者,它不僅表現在學術史的建構上,也表現在諸多有創造性的學術成果上。《興的源起》——書從發生學的觀點研究“興”的起源與原始宗教的關系,及對我國詩歌藝術發展的影響。指出《詩經》中鳥的興象具有祖先觀念的意義;樹木興象具有宗族鄉里觀念的意義;龍、鳳、麒麟等興象具有國祚安危禍福等觀念意義。并在此基礎上,論證了作為形式范疇的“興”起源的本質。迄今為止,學者對《詩經》中的“比興”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從發生學的角度研究“興”的起源,始終無人問津,《興的源起》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白。詩歌的起源與發生學的研究屬于藝術起源的研究,是藝術學和美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西方自 19世紀以來即開始了艱苦的探索,卻很少有真正價值的研究成果。畢生從事于藝術起源研究的德國著名學者格羅塞曾把這一課題稱之為艱難的“遠征”。在這種情況下,利用《詩經》中的原始文化因素,和古代文獻進行詩歌藝術發生研究,比用當代的原始詩歌去以古證今的作法更為可靠,它對人類藝術史、美學史和原始文化研究都有重大意義。難怪該書被李澤厚收入《美學叢書》之中,同時也彰顯《詩經》作為民族文化原典的寶貴價值。
趙氏的學術目光明澈而深邃,善于在司空見慣的地方發現新的成長點。誰也沒能像他那樣發現屈原放逐江南,創作了宗教神話詩《九歌》,使他“于兩千多年前即已走上了現代學者引以自豪的文化人類學研究道路”,從而使屈原成為杰出的神話采集、保存和加工者的新結論。[2]在一般研究者的眼中,《詩經》屬于現實主義的作品,不可能有神話學的價值,但在他的《先秦神話思想史論》中,從《詩經》的神話學潛在價值、《詩經》的神話學文獻價值、《詩經》的神話思想價值等方面,論證了《詩經》神話學價值,有理有據,令人耳目一新。由于人們認識的片面性,以為極“左”思潮干擾下的《詩經》研究充滿著謬誤和荒誕,沒有學術價值可言,造成了學術界對這一段在《詩經》學術史上肆虐一時、危害巨大的錯誤觀點及其發展歷程始終保持緘默,趙氏指出“錯誤的東西有錯誤的價值,可以從反面為我們提供借鑒,把學術史上一切錯誤的東西都排除掉,學術史也就不成為學術史了。”由此他在《思潮與詩經》一書中列專章加以評析,收到好的效果。古人說,授人魚不如授之以漁。趙氏很注意科學研究方法的總結與推介,在《思潮與詩經》中,對王國維開創的“兩重證據法”的發生、發展及其價值作了深入的論述,對海外學者科學研究方法的總結也是該書又一個亮點,為我們送來一股清新的異域之風②。
三、可貴的學術品格
(一)嚴謹求真的現代科學精神
進入 20世紀,以科學觀念和科學精神為基礎的現代學術意識逐漸取代傳統學術意識而成為研究的主導,并使《詩經》研究發生了全面深刻變化。趙氏自覺地把現代學術意識貫徹于研究之中,首先表現著嚴謹求真的現代科學精神。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概括學術史的四個基本條件,其中第一條是:“敘一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時代重要各派全部網羅,不可愛憎去取”。在《思潮與詩經》一書中,不光把國內的相關資料全部網羅,而且把海外的有關著述也納入視野之中,而且列專章加以討論,并由此得出現代《詩經》學已是世界性學術的新結論。這使我們在看到趙氏成功的同時也看到一位求實的學者在資料搜集整理和分析上所付出的艱辛,以及開放的心態,世界的眼光。對胡適所提出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研究方法,向來多持批判態度,趙氏則認為“它實際是一種依據大量證據研究具體現象,并以求真為目的的實證研究方法”。他的說法不僅有理,而且讓我們看到不隨風轉舵,堅持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20世紀《詩經》白話文翻譯盛況空前,構成了 20世紀《詩經》學園地一道獨特的風景,然而由于學界對大眾化讀物重視不夠,使之邊緣化。趙氏慧眼獨具,列專章加以討論,填補了20世紀《詩經》學史的一段空白。正是得力于這種優良的學術品格,才使我們看到一部能夠反映20世紀《詩經》發展全貌的具有科學精神的學術史。
(二)真誠的理性的批判精神
一般說來,學術史的任務有三:1.揭示學術觀點的源流變化;2.總結學術研究的發展規律;3.對學術成果得失進行評估。趙氏的批判精神主要表現在第三方面,在《思潮與詩經》一書的每一章里,總有“存在問題與不足”這一欄。對研究的問題進行清理,對錯誤進行批判。在肯定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用唯物史觀觀照,才第一次發現這個世界(林按:指《詩經》的思想內容)如此豐富和廣大”之后,指出該書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把學術研究用于政治斗爭服務的始作俑者”,批評其“套用現成理論,忽視特殊性的研究”等缺點,提出了一個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研究對象如何“對話”的重大理論問題。在批判“四人幫”文化虛無主義和專制主義所造成的禍害時指出:“極左”思潮支配的《詩經》研究,目的就是要毀滅《詩經》及其研究!“文化”的存在竟以毀滅自己為目的,只能證明它本身就是人類文明的敵人。言辭不可謂不激烈,但很深刻。在中國歷史上,對當代的最高領袖的錯誤敢于直面批評的,除了司馬遷,很少有人敢于這樣做。在該書里,我們看到趙氏也是這樣做的,不為尊者諱,不為愛者諱,表現了極大的學術勇氣和鋒芒。趙氏的研究表明,有良知的學者是社會科學的批評家和領路人。在新世紀,應該強化批評意識,應該帶著一種覺醒的獨立人格和歷史感走進各自的領域,完成歷史賦予的使命。
(三)豐厚的理論素養
讀趙氏的書,就像聽一位睿智哲人的談話,他分析問題高屋建瓴而又鞭辟入里,又如小李飛刀,很少虛發,原因何在?早在“五四”時期,劉半農就指出:“處于現在的時代,非富于新知,具有遠大的眼光,斷斷沒有研究舊學的資格”。(《復王敬軒書》)所謂“遠大的眼光”,就是宏觀的視野,落實到趙氏就是具有世界的眼光,把《詩經》研究放到世界學術的體系中,從世界學術的高度認識《詩經》學的發展;所謂“新知”,就是新的科學理論知識。在趙氏的知識儲備庫里,哲學、史學、文學、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神話學等都相當豐厚,《思潮與詩經》里批評有的學者把甲骨文“斤”(斧子)誤釋為男性陽具,有理有據,沒有深厚的甲骨文學、古文字學的修養是做不到的。沒有豐厚的理論思維,《興的源起》、《先秦神話思想史論》等著作也沒法寫。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研究的最高峰,就一刻也離不開理論思維”,正是憑借理論思維,才使趙氏的研究具有前沿性和科學性的特征,才使趙氏成為當代《詩經》學的引路人。
(四)兩點反思
西方有句諺語:每個人都是上帝咬一口的蘋果。意思是每個人都有局限,不可能完美無缺。對于學術問題也應作如是觀。《思潮與詩經》采用的是開放型的建構模式,只能把每一個學術精英及其著作分屬于不同的專題,不可能像列傳式的建構模式那樣構筑一個人物譜系。梁啟超說:“我們讀《明儒學案》,每讀完一案,便覺得這個人的面目活現紙上”。(《中國三百年學術史》)這是開放型學術史建構模式難以達到的。由于該范型著重于《詩經》研究與時代學術文化思潮的對話,對以審美為中心的內部研究較為薄弱。這就提出一個能否把兩種模式結合起來的問題。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被譽為“開放型”建構模式的濫觴,但它既有學者的專論,又顧及文化思潮對學術研究的影響,可供借鑒。其次,《邶風·新臺》:“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詩中的“鴻”字,聞一多于1935年 7月,發表《詩新臺鴻字說》(《新華學報》1935年 7月)一文,釋“鴻”為“蟾蜍”,哄動一時。但聞一多先生后在《說魚》中用“仍以訓為鳥名為妥”加以修正。然而,夏傳才先生《詩經研究史概要》認為聞一多“自我否定并不正確”。趙氏在《思潮與詩經》中也對聞先生的新說給予高度評價:“聞一多對‘鴻’的訓釋更體現致密和周嚴的現代科學精神的突出例證。”那么,到底是聞一多的新釋對呢,還是他的修正對呢?對這一樁小小公案,我們認為還是聞一多的修正是正確的,因為詩中“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是種顛倒錯亂之象,比喻目的與效果的不一致。這種意象在《楚辭》中也常見。須知比喻只取一點不及其余,了解這個特征,聞先生的修正就好理解。何況聞先生也把“籧篨”、“戚施”的意象都釋為“蟾蜍”豈不重復?也不合《詩經》的詩例,因為一首短詩的一個意象不可能用三個異名。
[注 釋]
①杜書瀛在《文藝創作美學綱要》中指出;一位真正的杰出的作家“總是表現前所未有的‘第一次’的性質,是在這之前世界上從未出現過的,甚至連他的語言和表現手法也是未曾見過的。總之,這一切都是作家的精神創造物,是他第一次帶到這世界上來的,為這世界增加了新的精神因子”。(遼寧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 20頁)這里講的是創作,但也適合于學術研究,趙氏正是憑借許多學術成果的“第一次”,為現代《詩經》學增添了新的“精神因子”,并成為當代《詩經》學界主流學術的代表人物。
②中國學術史有一個特殊的規律;許多新的學說、新的思想產生于對經典的詮釋之中,從而使學術得以發展。趙先生通過對《詩經》的詮釋,提出許多新的思想,推動了《詩經》研究的發展,更可貴的是,他的研究已經形成一個學派,即“學術文化思潮派、”,這個學派濫觴于梁啟超,完成于趙沛霖。它以時代學術文化思潮為切入點,以現代的、開放的、世界意識為其主要學術特征,從而與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以夏傳才為首的“唯物史觀派”區別開來。它是《詩經》園地里,沐浴著改革開放春風而盛開的花朵。
[1]培根.論學術的進展[A].哈魯濱孫.新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2]趙沛霖.先秦神話思想史論[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