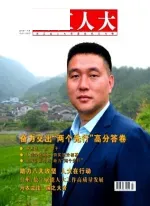尊嚴考量法治
■林 龍
尊嚴考量法治
■林 龍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尊嚴”,雖只有兩字,卻涉及億萬民眾,成為了此次全國人代會一個熱門的名詞。公民權利的保障,公民尊嚴的產生,除了公平正義的社會制度建構之外,還依賴于公權行使的規范和“以人為本”的歸位。圍繞這一話題,代表們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和討論。

“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當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前不久在新春團拜會上說出這句話后,其中的“尊嚴”旋即成為社會熱詞之一,激起人們內心深處強烈的情感波瀾。順理成章的是,相關表述同樣出現在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尊嚴不僅涉及“溫飽”的物質保障,更包含著“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的政治權利。毫無疑問的是,公民權利的保障、公民尊嚴的產生,除了公平正義的社會制度建構之外,還依賴于人大機關、政府機關、司法機關依法行使權力,裁定公民之間、公民與政府之間的權利糾紛。因此,尊嚴不但考驗著當下的社會制度,同時也對法治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政府行為與人民尊嚴
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和社會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利益訴求多元,社會矛盾交織,人民群眾對政府的執政能力、協調能力要求更高,對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期盼更加強烈。政府如果在執政過程中頻繁出現缺位、越位,甚至是亂作為的問題,人民的幸福感和尊嚴感將無從談起。
“政府的作為與人民的尊嚴感直接相關。”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的鄭玉歆代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人民政府既要謀求人民幸福,更要維護人民尊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的“努力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關鍵是服務什么人,怎么服務。
“政府如果追求增長至上,那么就會站在資本的立場,替資本說話服務。資本強勢,老百姓就會處于弱勢。”鄭玉歆表示,政府服務的角色歸位,其前提必須是觀念的轉變。財富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手段,不然政府就很容易錯位,陷入“與民爭利”的泥潭。
“我看現在有的地方,‘官場’像‘市場’,政府跑項目,跑資金。”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于輝達代表和記者談到,權力在配置市場資源時,很容易產生“特權利益”。“‘擴大民權、限制特權、規范公權’應該成為政府改革的重心。”

特權橫行讓曾任中紀委副書記的劉錫榮代表尤感憤慨。在全團審議時,劉錫榮代表怒斥,一些政府部門搞產品抽樣檢查,酒水一拿就是幾箱。曾有企業負責人向他反映,有關部門檢查皮衣質量,要拿上十幾件。“你不答應,它就用權力來弄你,讓你不得不為這種不合理檢查買單。”
當前,許多老百姓對拆遷問題怨聲載道,一些地方還出現了極不和諧的場面。“拆遷中的官民沖突發生,核心問題是對老百姓的利益補償沒能到位。房子拆了,安置的地段很差,資金補償少,老百姓能滿意嗎?”于輝達坦言。據悉,杭州市在拆遷工作上堅持兩條“硬杠”。因公共建設需要而進行的拆遷,以同地段房價作為補償標準;拆后建商品房的,則采取“原拆原遷”。
“政府的公權力如不受到約束,就會侵害公民的利益,尊嚴又何從談起?”鄭玉歆坦言,公權只有在陽光下運作,才會老老實實地為民服務。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政府要維護老百姓物質利益,更要尊重和保障公民依法享受的政治權利。”鄭玉歆表示,人民有渠道分享民主、監督政府,事關當家作主的尊嚴。“只有人民有效地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目前的問題是,讓人民批評政府是很容易做到的,關鍵是怎么回應?群眾監督,最終的落腳點還是看監督有沒有取得效果。”
富潤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趙林中代表建議,應建立群眾批評、監督政府的反饋機制。群眾的哪些批評、意見被吸納了,哪些工作改進了,哪些正在改進,還有哪些因為客觀原因,一時還不能解決的,應逐一向公眾及時通報。知道自己的批評、監督受到政府的重視,群眾的積極性自然會提高。
舟山市華鷹遠洋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李科平代表則認為:“現在,人民群眾批評監督的門檻依然較高,拓寬監督渠道很有必要。”他表示,應擴大網絡批評的監督平臺,方便群眾對政府工作進行批評、監督。
權力對政府來說是“雙刃劍”,用好了是正本清源的利器,用歪了是損害公信的“元兇”。可以想見的是,當政府權力被運用于保障公民權利,當權力運行更加透明,當公民的權利不被剝奪之時,一個更加文明、更加公正、更加和諧的社會也將隨之來臨。
走出信“訪”不信“法”的誤區
法律本是維護公平、正義的最有力的武器,然而目前卻有越來越多的群眾在受到不法侵害時,不是通過正常的法律途徑解決,而是一趟接著一趟,不厭其煩地踏上上訪之路。
封建社會,攔轎告狀常為草民伸冤之途,“青天大老爺”也因此每每被傳為佳話。人治時代的這種“信老爺不信王法”傳統,一直流傳至今。“現實中,群眾信‘訪’不信‘法’,不僅擾亂了政府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影響了社會穩定,同時也有損法律的權威,架空了司法程序。”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齊奇代表在全團審議發言中直指信“訪”不信“法”的病癥。
齊奇表示,由于信訪不受任何事實證據、期限、步驟、方式等確定性要求的限制,在個別時間和個別案件中又能夠“一步到位”甚至“突破法律底線”解決問題,成為越來越多當事人的首選。其結果是,原本通過書信反映情況的陳情制度日益轉化為越級走訪、鬧訪、纏訪。領導出于維穩的需要個別批示、法外解決,誤導了廣大信訪人,導致千軍萬馬齊涌黨委、政府尋求“直通車”,加劇了信訪潮。在小組審議中,升華集團董事長夏士林代表也認為,地方政府“花錢買安定”的處事方式,使得一些不合理的訴求,也在上訪中得到了不符法律的解決,這就會誤導民眾,以為“訪”比“法”更有效。
“信訪不能成為利益博弈的主渠道,必須要以事實、證據為主,通過司法渠道來解決糾紛。”齊奇言語堅定。
在全團審議發言中,寧波市政協副主席范誼代表建議,讓信訪體制和司法體制相分離,把受理信訪范圍嚴格限定在司法事務之外,凡涉法事務皆在司法框架內,通過司法渠道解決。“讓信訪體制逐漸淡出我國的司法協調和處置系統,才能真正把法制建設的注意力投放到司法體制、機制、隊伍建設中。要比重視信訪更加重視法檢建設。”范誼說。
對司法不公、違法亂紀等司法行為,范誼認為,對誤判、錯判案件的糾正,應在法律框架內通過司法手段和救濟渠道解決。凡違法違紀司法行為的查處,應通過紀檢系統解決。要把信訪和政府相分離,并歸到黨委紀檢系統,其職能限制在受理違紀投訴的范圍內,不再受理涉法信訪。
目前社會普遍關注的另一個熱點話題是“當司法遇到網絡”。鄧玉嬌案、許霆惡意取款案等等事件,在網絡上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有網民稱:“民意法官”、“全民法官”的時代來臨了。
“網絡發展很快,個案能迅速放大,網民參與進來,有關部門要傾聽這些聲音,但關鍵還是要堅持好司法獨立。”齊奇表示,有些案件,網民出于同情心,往往帶著一些個人的情緒化色彩。甚至在一些案件中,還存在網絡“掮客”,故弄玄虛,制造點擊率,炒作網上輿論,以達到某些不正當的目的。“網絡聲音不等于民意。法官不要有網絡恐懼癥,而要冷靜地用法律思維來考慮案件。”齊奇說。
“網絡熱炒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法院應該有所回應。”在審議中,范誼表示,這幾年我國社會生活中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社會影響很大,卻很少看到“兩院”報告給予指導。比如三鹿奶粉案、山西垮壩案、毒豇豆事件、最高法院副院長腐敗案等,都聽不到“兩院”的聲音。因此他建議“兩院”報告內容不一定面面俱到,可以更加具體些,深入些,用典型案例說明問題,這是一個很好的普法過程,有利于指導司法實踐。
目前“網絡反腐”現象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齊奇表示,“我們要肯定網絡輿論的積極作用,但要注意規范。”他坦言,當前對于網絡的管理和法律規范還不太完善,如果過了頭,也會誤傷好人,也會被一些人用來蓄意陷害他人,如果造成嚴重后果的話,就可以按照誣告陷害來治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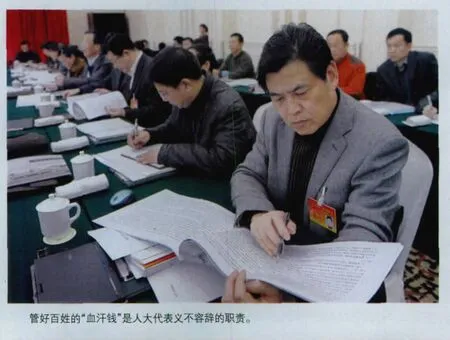
激活人大“休眠”的權力
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指出,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黨的十五大提出的新時期立法工作的總目標。如期實現這一目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是今年立法工作的首要任務,也是今年人大工作的重中之重。
要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其中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適應新的形勢需要進行法律的清理和修改。有專家指出,今后中國將進入全面“修法”的時代。圍繞這一話題,與會代表提出了許多意見和建議。
“轉型時期,法律的修改和清理工作十分重要。”于輝達代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原來的立法模式往往是部門拉出一個初稿,然后人大來審,中間存在許多的“部門利益”。有利相爭,無利推諉,因此,出現了一些領域“多頭管理”,而一些領域“管理真空”的亂象。于輝達建議,修法的重點,一方面要針對一些不合時宜的條款,另一方面則更要注重去除“部門利益”,真正實現法律的公平和正義。
“形成中國特色法律體系的目標已定,但我們一定要避免‘大干快上’,應該在立法的質量上多下功夫。”在小組審議時,不少代表表示,立法工作目前已進入“深水區”,要對一些重要領域、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進行及時研究。例如,官員財產公開法,提了那么多年,老百姓呼聲強烈,但就是“千呼萬喚不出來”。行政開支就像是彈簧一樣,“三公”開支過大,應該加緊做好稅收和財政方面的立法工作。
“無法可依是可悲的,而有法不依則是可怕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錫榮代表認為,相對于立法而言,現在執法和普法相對薄弱,人大要加強對政府執法行為的監督。
管好“錢袋子”,涉及億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是人大的一項重要職責。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政府預算報告跟以往相比有一個很大的亮點:央企紅利和包含賣地收入在內的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被首次寫入。而在此之前,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雖然納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管理,但長期游離于國家賬本之外,使得占地方政府收入約1/5的土地出讓金,始終得不到應有的監督。
“如果不管好納稅人的錢,糊里糊涂而不是精打細算的話,那就不是一個合格的當家人。”溫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小同代表直言。
在采訪中,溫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笑華代表告訴記者,溫州市人大常委會近些年來加大了對預算外資金的管理,重點監督土地出讓金。溫州市人大常委會在調研中發現,房地產商將地圈走后,遲遲未能在規定時間里交清出讓金。“30多個億資金不交,一個月光算算利息,都是一個很大的數字。”政府為什么收不上來?有政府不作為的原因,也有工作方式不當的問題。因此,溫州市人大將此問題提上監督的議事日程,督促政府限期解決。通過多方的努力,最終收回了71%的資金。
“針對存在的問題,人大必須要動真格,不動真格,很難推動。”陳笑華說。
“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依法開展專題詢問和質詢,將選擇代表普遍關心的問題聽取國務院有關部門專題匯報,根據有關法律的規定,要請國務院有關部門主要負責同志到會聽取意見、回答詢問、答復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高調重申“質詢權”,引起了代表們的廣泛討論。
雖然憲法和監督法對質詢都有明確規定,但是多年以來,質詢權卻一直處于“沉睡狀態”,不僅在全國人大層面上罕見質詢案,而且在地方各級人大中,“質詢案”也是鳳毛麟角。
范誼認為,質詢這種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形式是世界各國議會經常采用的一種形式,雖然國情、政體不同,但這樣的監督作為政府和民意溝通的渠道,其效果已被證明是非常好的。臺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薛少仙代表則認為,“質詢權”的激活,對于政府來說,將大大增強執法壓力,更加注意依法行政;而對于人大本身來說,質詢權的啟用和常態化,也將是人大監督工作的一個有力推手。
“質詢后怎么辦?這里就有一個需要探索下去的問題。”薛少仙表示,如果多次質詢都不滿意,應不應該采取更加嚴厲和剛性的手段,直至罷免。“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地方各級人大可以進行積極的探索,激活人大更多的權力,釋放更多監督的能量。”
“人大就是人民利益最大。人大應該成為民生民利的維護者,守護好人民的幸福和尊嚴。”鄭杰民代表的“人大新論”,道出了人大新的內涵和職責。我們期望,在保障民權、維護民利上,人大能有更多、更好的作為。這是代表的呼聲,更是億萬人民的心聲。